摘要:20世纪30年代以来,游泳在上海成为一种“时髦”活动,不仅游泳场聚满女性,女性游泳也成为媒体热衷的话题。作为近代都市新兴公共空间,游泳场给予了“观者”一个特殊场域,使“观者”不再遮掩凝视的目光,“被观者”也可以在这个空间展示裸露的身体,二者交织使私密性的身体成为公众化谈资,使近代游泳场中的女性身体成为富有张力的复杂符码。文章从1930年代上海以游泳为主题的报刊资料入手,以近代以来对女性身体态度的转变(身体发现—身体观看—身体展演)为线索,通过分析情色、健美与摩登等矛盾概念在游泳场中的女性身体上达到和谐状态,认为女性身体在三个层面呈现张力:一是对身体美的认知,在情色化与健康美的碰撞下,得以脱离男性话语规训从而建立自主选择的审美;二是在观看身体的态度上,在他者凝视的目光缝隙中进行女性主体建构;三是对身体的掌握,在媒体引领的肉体狂欢消费中彰显主动展演。
作者简介:高婉婷(2000—),山东临沂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视觉文化、中西美学与艺术史。
引文格式:高婉婷.情色、健美与摩登:1930年代上海游泳场中的女性身体图像[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5,42(4):45-56.
游泳运动自1920年代在中国兴起,便在上海受到热烈追捧,女性身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尤其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首次把女子游泳列入比赛项目,进一步催化了女性游泳热潮的形成,游泳运动迅速发展成最受欢迎的、话题度最高的运动项目之一。1930年代,欧美国家盛行裸体运动,高呼“回返自然”,并认为裸体运动有益于健康,中国的游泳运动一定程度上对标了西方的裸体运动[1]。然而,在没有裸体传统的中国,在公共空间裸露身体的游泳运动尤其是女性游泳能够在近代被广泛接受,具有其发展的特殊性。西方裸体观进入中国的历程是坎坷的,从“有伤风化”到“刘海粟人体模特儿风波”,传统礼教下的中国是没有公开的裸露历史的,但近代以来,在女性身体解放及救亡图存的口号中女性游泳运动成为一朵盛放的“奇葩”。随着游泳运动的发展,游泳场中的女性身体似乎合理化了公共空间中的身体裸露,呈现一场女性身体消费的狂欢。游泳场为“观者”的凝视与“被观者”的展示提供了一个特殊空间,使女性身体成为融合矛盾的复杂符号。
关于近代女性游泳的研究,鲜有将目光聚焦公共空间中的女性游泳身体,且多从他者的角度观看女性游泳现象,重在探究游泳场中的女性是如何被国家、社会、媒体等单向建构的,而女性的主体性则被漠视,女性的身体被遮蔽,女性的地位也被忽视。但值得注意的是,身体是客观存在的,并非一味地作为社会产品被建构,个人意志是无法被忽视的,身体是可以完成自我建构的,女性游泳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受到追捧,与女性自身对待游泳身体的主动建构密不可分。苏全有认为,舆论界的倡导与影艺界的引领合力铸就了我国女性游泳在民国时期的发展。[2]李雅琪从身体媒介与转译的视角出发,考察了作为 “媒介”的女性游泳身体是如何在政治、运动、时尚话语的转译中传播实践的。[3]李楠、孙淑慧梳理了“健美”这一西式话语在中国的转译与传播,注意到女性的身体并不是被动接受改造,女性解放思潮也使女性主张身体的自我掌控,但最后又将其归于个人的发展无法摆脱时代洪流的裹挟,认为这是国家民族的发展投射在女性身体上的结果。[4]游鉴明在《运动场内外: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一书中论及近代运动女性形象塑造时虽然关注到女性自身潜在的力量,但对“游泳场”这个更加特殊的空间没有展开更多论述。[5]在此基础上,本文从1930年代上海以游泳为主题的报刊图像入手,以近代以来对女性身体态度的转变(身体发现—身体观看—身体展演)为线索,通过分析情色、健美与摩登等矛盾概念如何在游泳场中的女性身体上达到和谐,认为女性身体在三个层面呈现张力:一是对身体美的认知,在情色化与健康美的碰撞下,得以脱离男性话语规训从而建立自主选择的审美;二是在观看身体的态度上,在他者凝视的目光缝隙中进行女性主体建构;三是对身体的掌握,在媒体引领的肉体消费狂欢中主动展演。
一、游泳场中的女性身体:合法的“裸体”狂欢
弗朗索瓦·于连曾在《本质或裸体》一书中给中国定下了一个裸体之“不可能”的结论。事实上,祼体在只有春宫图传统的中国举步维艰,但对标西方的裸体运动,相当于“裸浴”的游泳运动却发展成近代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在近代游泳观念的传播中,女性身体扮演了关键角色。女子游泳是在近代游泳观念传入中国后才逐渐普及的,在此之前,女性在公共空间中下水是不可想象的,游鉴明曾在对邵梦兰的访问中得知“她在上海读书时,会陪同女同学到海边游泳,但她回忆在浙江淳安老家河边游泳的,都是男人,没有女人”[6]。然而近代游泳观念一经传入,仅仅过了几十年,游泳场中的景象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上海,游泳成为“时髦”活动,女子游泳已成风气。游泳时节一到,不仅游泳池畔、河岸、海边聚集成群女性,报刊版面也被女运动员、女明星或名媛穿泳衣戏水的画面占据,女性更是成为游泳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以至于提到“游泳”,首先浮现在脑海中的便是身材姣好、穿着时髦泳衣的摩登女郎形象。可见,在游泳场中女性占据了主体地位,正如陈建华所言:“女子主宰了现代性公共空间,不只是’半爿天’。”[7]227如1939年第3期《上海》的封面图《水浴图》(见图1),身材姣好、穿着泳衣的女性正在跳水,几乎占据整个画面,而右下角有一个惊慌失措的极小的男性游泳者,两者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女性在游泳场中的地位可见一斑。这种空间意象图示也打破了传统图像中“男主—女次”的空间隐喻格局。
图1 《水浴图》
陈建华在《摩登图释》中详细介绍了“游泳”一词是如何进入近代中国的,并认为最终“游泳”取代了“泅水”。[7]236这不仅是语词能指上的更迭,更是游泳活动作为运动进入公共视野的转变,“游泳”一词从诞生起便包含着公共意味,将“水浴”这种私密行为搬到了公共话语中。在“体育强国”的政治倡导下,游泳运动中的裸露成为特殊现象,似乎合理化了公共场所的身体裸露现象,呈现一场女性身体消费的狂欢。《良友》刊登了大量泳装女子图片,但绝无“裸体”之嫌。在颇受争议的裸体写生领域,游泳身体成为特例,1946年《见闻》曾刊载表达此意的裸女写生图《美术:死后成名》(见图2),并配文:“只有游泳家的肌肉才可以合法的裸写。”1940年《小姐》中刊载的漫画《女人的诱惑力》(见图3)也有着类似的意思,漫画中呈现一位身着旗袍的女性,她用手撩起旗袍露出大腿,并配文:“在游泳池里全身赤裸裸倒也没有什么刺激,而在不意中瞧着点儿,管教你有点儿麻上来呢。”可见,游泳场中的女性身体已经被抹去了私密性,公开于公共视野中,过去只能通过偷窥或遐想的女性身体,现在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被大方地观看、拍摄,女性半裸露的身体甚至成为公共话题被讨论与批评。在游泳场这个特殊的空间中开启了对女性身体的狂欢消费,一场针对女子身体的吊诡事件正在上演,在一对对矛盾概念的和谐中,女性身体呈现独有的张力。
图3 《女人的诱惑力》
二、身体发现:情色化与健康美
在福柯看来,权力对身体具有规训作用,使其“温顺”“有纪律”,并认为“性属于身体的规训”,身体内在的性也会成为权力影响身体的工具。[8]在男权话语体系下,女性身体通常被限制于某个“规范”之内以符合男性期待,因此女性身体总是被动的、温顺的、柔弱的,这是由父权制社会的审美标准所建构的,并非身体的“自然”状态。因而,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女性身体是被严格包裹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夫为妻纲”的传统礼教之下,女性身体被异化,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所有物而存在。在男性话语体系中,女性的身体被分为两类:一是在男性规训下的礼法化身体,二是为满足男性欲望而被妖魔化、情色化的身体。前者造就了缠足、束胸,林黛玉式的“以弱为美”的畸形身体观;后者则表现为淫邪的、魅惑的“妓女”“情妇”形象。此外,女子身体美的标准一直被男性所掌控,女性身体在古代男性书写中一直遭受着不公待遇,不仅要符合男性审美标准,还要承受污名化与荡妇羞辱,成为被侮辱的、被损害的存在。这种传统语境中男性霸权话语下的身体审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关于“女子美”的讨论,“健美”观的出现为长期被妖魔化的女性身体提供了一个自我掌控的契机。
“健美”概念源自西方,最开始“健美”一词是政府和知识分子“为了鼓励女性对运动的兴趣”而创造的,由“健康”和“美丽”这两个概念组合而成,在1920—1940年代广为流行。[9]西方健美体育观传入中国后,在“保国强种”“国民之母”的口号中,被赋予了尚武精神、救国责任的健美体育观迅速走红。1930年的第四届全运会是中国女性第一次在全国性运动会上正式登场,《申报》的编辑在该报“全国运动大会特刊”的引言中描述道:
我国女子素以娇小文秀为美观、不出远道为习尚、而今一般肌肉丰满短衣露腿矫健美丽之女子、雄赳赳驰骋于运动场上、虽东北西南两隅、亦不嫌路途之跋涉、均来比赛、可见我国体育已普及于女子。[10]
“肌肉”“丰满”“矫健”“驰骋”等词显示一种颠覆以往的全新审美已然来袭。正如罗薇所言:“世界上的人一致的承认,最美的女人的体态是丰腴而不失其婀娜的姿态……现在像林黛玉似的病态的美人,已不能在现代的社会上受人的欢迎了!”[11]而相关宣传中达到健康美的最佳途径便是游泳,游泳活动与“健美”有着紧密的联系。《时报》刊登的相关宣传中国产影片《健美运动》的广告中明确提到,这部伟大的国产影片要“告诉女性们健美底必要,指示女性们怎能够健美”,最重要的就是“现代健美女性的太阳浴”及“现代女性的游泳运动”。[12]裸露的身体虽具有情色意味,但在游泳运动的作用下,健康美渗透其中,两者交织并形成张力。
虽然成为近代女性游泳身体的标志性审美的“健美”仍无法摆脱“国民之母”的“政治正确”,但它确实塑造了新的社会审美,激起了女性的主体性关注,她们既反对传统的病弱审美,也不认同政府期许下的只健不美,而是有着自己的思考与选择,尝试掌握自己身体的控制权。她们一方面不再回避“情色”的游泳身体,努力摆脱长久以来“女子裸露身体引起男性邪念”的有罪论,打破男性书写下“情色水妖”的污名化。舒如云在《拥护裸足运动》中写道:
如果看见女子肉体外露,便会引起邪念,那么除非把女子的面孔双手,身体一切外露部分,都用厚帛包裹了,才不至有问题发生,不然只把双足包着了是没有用的。但是,我以为假使男子是这样神经过敏,把身子包了也不会有什么功效,因为他们会无中生有想入非非呢。最好的法子,还是把男子的眼睛永远用手帕遮蔽了罢![13]
另一方面,在身体解放的潮流下,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有了双重要求,不仅要美观还要健康,由此“柔弱美”的身体观被彻底剔除。在西方太阳浴、晒乳的影响下,代表健康的小麦色肌肤成为新的审美追求,1934年《图画时报》就刊载了一张这年上海高桥海边的照片(见图4),配文“上海小姐也染上好莱坞风气以褐色皮肤为美穿上一件露背游泳衣坐于高桥海边”。以健康为主体的新的身体审美观—“健美”—的出现实际上是女性自我发现的标志、自爱的体现及主体性的觉醒。游泳场中的女子们摆脱了病态审美,闪耀着生命的光辉。
图4 《1934年上海高桥海边》
然而这种新型身体观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女子游泳运动盛行的时代,仍有不甘寂寞的“男权文化势力”试图打着“健康”的幌子插手女子游泳,并对其进行异化解读。一方面刊发文章讨论“运动是否会影响女性形象”,认为运动会造成女性“男子气”,甚至会使女性不孕;另一方面认为游泳女性穿着暴露,有情色嫌疑,会带来不良的社会风气。《女性的哀鸣》指出,虽然游泳运动向女性开放,但报纸上有关游泳的报道充斥着对女性的侮辱,常去游泳的女性被称作“星”,偶然一试的多数人则被称作“观音兵”,还有人有意无意地碰撞游泳中的女性,想入非非,这一女性高尚的运动却被说成“心邪行不正”。[14] 1933年《华安》就刊载过表达此含义的漫画《游泳女选手之副作用》(见图5),画面上为三本杂志,杂志封面刊登的是有“美人鱼”之称的游泳明星杨秀琼,并配文“游泳女选手之副作用”。可见大众对女性身体这一隐私问题的公开批评与讨论屡见不鲜。
图5 《游泳女选手之副作用》
此时期,围绕“健美”身体对女性的意义的问题争议颇多,认为它虽然使身体美的标准从“柔弱美”转向“健康美”,但仍摆脱不了它是新的社会环境中权力话语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如《各国女青年的健身运动》中所言:“以柔弱娟媚之姿,取容于男子,而她们的地位终亦不过沦为男子的附属物。但今日来的妇女,却大大不同了……”[15]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的女性渴望公共空间的表达,即使男性主导下的社会留给她们的空间只是基于所谓的强国保种、社会进步的需要,她们仍渴望争取哪怕一点点的话语权。在女性的努力下,“女子体格将渐渐变得强健”“女子将来不至再居被动地位”“从体格的锻炼中,将要造成新女性的典型”等内容见刊,健康美给性别界限带来了强有力的挑战。小麦色肌肤、健壮肌肉都是健康的表现,对健康的追求实际上是身体主体性的回归,是对身体的爱护与珍视,这是一种从女性主体出发而不再以取悦男性为出发点的身体观。故而虽然健康美仍带有身体政治符号载体的意味,但它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脱离男性凝视的女性审美观特质,是女性第一次站出来为自己发声的尝试,是一次对自己身体美的伟大发现。
三、身体观看:他者凝视与主体建构
女性身体一直被认为是男性视线凝视的客体,近代游泳场的特殊性合法化了游泳女性裸露的身体,不仅对女性身体解放“暗送秋波”,也给了男性光明正大观看的机会。1930年代游泳运动异常火爆,这种火爆不仅表现在游泳者的兴趣上,更表现在观众的目光中。游泳场经常挤满观众,他们多是冲着女性游泳者而来,《大晚报》记者曾发现,一到夏季,游泳池便出现男男女女,妙龄女郎的身体曲线常成为男性目光的焦点,岸上观看的男人排列成墙。[16]有女性参与的游泳活动总能吸引大批围观群众,即使不是正式比赛也是万头攒动,观看游泳的人远多于游泳的人。1935年《时代漫画》就刊载了男子赛场观众席空荡无人而女子赛场万头攒动的漫画《网球赛》(见图6),虽然画面表现的是网球赛,但当时观众的兴趣点可见一斑。1937年《中国学生》刊载的一则漫画《学生生活》(见图7)描绘了两个身着运动服、手持网球拍的男学生正准备去打网球,但与一位身着泳衣、身材丰腴曼妙、准备下泳池的女性擦肩而过后改变了主意,其中一位男学生对其同伴说道:“喂!还是游泳去吧。”漫画揭露了男性热衷前往泳池的原因。
图6 《网球赛》
图7 《学生生活》
在观者交错的视线中,他者凝视与主体建构共同作用于女性游泳身体,形成了一股张力。为观看女性游泳蜂拥而来的观众多以有色眼光对女性身体进行他者凝视,1935年《吴县日报》曾刊登了游泳比赛开赛前两位男选手看女选手下水时的对话:“看呵!大姑娘光屁股,太好看了”,“这家伙,这还了得,大姑娘、大小子,她们不害羞”。[17]猥亵的语言透露了观者对女性游泳身体的轻蔑态度。近代女性游泳作为公共事件,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来自公众的视线,事实上女性游泳身体也确实一直被男性视线侵犯。漫画家们更是用极尽讽刺的方式呈现男性观众对女运动员的凝视。1938年《滑稽世界》“夏季游泳”专辑中插入的一则漫画(见图8)将无处不在的窥视表现得淋漓尽致,画面被一个高台分为两部分,左侧为数名身着露背泳衣、打扮时髦的女性在海边沙滩上嬉戏,右侧高台上则是一个穿戴绅士的男性拿着望远镜向海滩窥探,并配文:“老妇:’我的丈夫是海岸缉私员,所以每天出去必须带望远镜。’”
图8 《滑稽世界》“夏季游泳”专辑漫画
游鉴明认为这种无处不在的有色偷窥视线与“在禁欲主义的旧礼教的环境中生长的男子,多少总有点色情狂”[5]249脱不了干系。然而面对这些不友善的视线,作为客体的女性不再遮掩回避、默默承受,她们或渴望被看、享受其中,或主动出击、直接痛斥,又或反客为主、选择“看”回去,无一不上演着女性对于身体观看的主体性生成。
对于海边的凝望视线,若仅从男性心理出发就简单地判断是不公平的,女性渴望被看的心态也不容忽视,“看”或“被看”的权力并非男性独有,而是掌握在双方手上。一位游泳爱好者曾这样描述1935年的虹口游泳池:
在虹口游泳池里,女人真是不少吓!但伊们之中,会游水的却是不多,因为身上虽是十九穿着一九三五式羊毛泳衣,而深水的地方,再没有人敢去的。一位朋友感慨系之的对我说:“女人在游泳池里,无非装样,会游水的究竟不多!”[18]
1933年《礼拜六》曾刊载过这样一则漫画(见图9),水中两位男子露头仰望岸边一位身着新式泳衣的摩登女性,并讨论道:“您瞧她没下过水?”“是的,不然她的游泳衣怎么会那样光洁。”这些穿着时髦泳衣却不下水的女性在近代以来的游泳场中并非稀奇现象,是漫画家最喜欢表现的题材之一。女性的生存空间一直以来处于被压榨的境地,游泳场终于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渴望被观看的心态使她们在面对男性目光时态度乐观、享受其中。
图9 《礼拜六》漫画
有人以乐观的态度享受男性的观看,也有人感觉受到了侵犯而不愿意被观看,这时她们会直接痛斥有色目光,维护自己的身体。1936年《中国漫画》刊载的漫画《游泳时节:漫画三则》其二(见图10)中,一男子在水中抬头仰望跳板上身穿泳装正准备跳水的女子,女子的视线则看向她的同伴,一段有趣的对话在她们之间展开:“哈!不要跳下去!”“为什么?”“下面有人在看你的大腿。”“唔!早已瞧见了,正要跳下去踏扁他的鼻子呢!”这幅漫画中的女性还只是言语上的痛斥,1938年《电声》刊载的漫画《吃了耳光》(见图11)则已经付诸行动,并配文:“游泳池里,豆腐吃不着,倒吃了耳光!”
图10 《游泳时节:漫画三则》其二
图11 《吃了耳光》
面对来自男性的视线,一些游泳女性在展示身体的同时还选择“看”回去,女性不全然是被观看的客体,有时她们还掌握了观看的权力。约翰·伯格提出了“男性凝视—女性被看”的观看传统[19]63,有学者指出,女性也同样在“看”,她们不仅是“被看”的客体,也是凝视的主体。柏霖的《奏着狂骚曲的游泳池》中这样描写当时的沙滩境况:
有久立在岸上的男子,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目的不是游泳,而是鉴赏女性美。也有专坐在草坪上的女子,她们的目的也不是游泳,而是在欣赏男性美。[20]
与此同时,1935年《大晚报》刊载的漫画《上海小姐:游泳(十五)》(见图12)也叙述了类似的故事:“上海小姐天一热便到游泳池,早上半天在游泳池旁找男友、喝可口可乐、弹曼陀林,或是看着男女泳客往池中跳,而她的泳衣却始终是干的。她们只是把游泳作为一种摩登玩意儿,来到游泳池只为了展示自己、出风头,寻觅异性。”无论在“奏着狂骚曲的”游泳池畔欣赏男性美,还是为寻觅异性而来,她们不再单纯地作为视线的客体存在,而是颠覆了传统看与被看的关系,向男性社会发出挑战。约翰·伯格曾颇具大男子主义地对女性展示自己身体的现象进行定义:“她身体的姿势,是摆给赏画的男人看的。为的是激起他的性欲,而同她的性欲毫不相干。”[19]56-57他认为主动展示身体的女性仅仅是把自己作为客体的“景观”。然而,值得关注的是视觉具有“交互性质”,我们能观看,也就意味着别人也能观看我们,男性凝视女性身体的时候,女性实际上也同样在凝视男性。故而这种展示实际上是女性对关系的主动追求,是把自己作为一段关系的主体而开展的有目的的行动,行动权掌握在女性自己手中。
图12 《上海小姐:游泳(十五)》
在他者凝视的环境中,女性游泳者或大胆痛斥观看者,或作为观者主动观看,又或主动展示身体给别人看,无论何种态度,都是她们自己的选择,她们不再是被迫承受的客体,而拥有了作为主体作出反应的权力。这些对于身体观看的态度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进了女性形象在游泳场中的主体建构。
四、身体展演:媒体消费与主动曝光
1930年代的上海离不开对女性身体的日常消费,如陈建华所言:“媒体不等于女体,但没有女体就失去动感和活力。”媒体的报道使原本已经暴露于公共领域的女性身体被进一步公共化。一方面媒体利用女性身体增加话题度,另一方面女性也积极配合甚至主动寻求媒体的曝光进行身体展演。
梳理1930年代媒体对运动场百态的报道,可以发现女运动员出现的频率比男运动员多得多,而其中媒体最喜欢报道的又是女性游泳运动员。杨秀琼在第五届全运会包揽游泳各项冠军,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些有影响力的画报无不刊登几张她的照片,然而多数媒体的关注点并不在她的游泳技巧上,而是对她靓丽的游泳身体更感兴趣。第六届全运会中杨秀琼穿了一身比基尼泳装,当她穿着这件新款泳衣下水时,有人竟以为是“乳罩”而引起公众讨论,对此,正如《杨秀琼的乳罩》中批评的那样:“作此语者,只顾出其没有见识,且不注意杨之技术,而注意其乳罩,着眼点也实在太坏了。”[21]在媒体消费领域,商品广告更是抓住这个热点无所不用其极地消费着游泳女性。1936年《时报》刊载的“明星花露香水”广告(见图13)就利用了杨秀琼的知名度,画面中视觉主体是一位正跃入水中的女游泳者和一瓶花露香水,使观者极易将二者形象勾连,并配文“世界女子游泳赛 杨秀琼各方面瞩目”“杨女士每于泳罢,必以’明星花露香水’涂擦全身,施行皮肤清洁,故其肌肉发达健全,肤色甚美。是以’明星花露香水’,各界仕女欲达健美目的,当常备一瓶,不仅泳罢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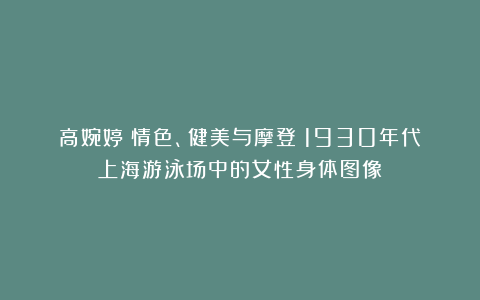
图13 “明星花露香水”广告
对于女性游泳身体的消费并不仅限于游泳运动员,身着泳衣的女明星也是媒体吸引读者的惯用手段。1939年《新华画报》刊载了女演员童月娟在游泳池试新游泳装的照片(见图14),并配文:“游泳季节一到,女明星赛过活神仙!”同年,《中国艺坛画报》“影人私生活”栏目刊载了女演员陆露明的漫画形象(见图15),并以游泳作为噱头:“一,论健美,黎灼灼后,一人而已,走起路来,一扭一扭,全部外国女人的风头。二,她爱游泳,什么蛙式蛇式,件件皆能,你在游泳池里,常有旁观芳泽的机会。”可见,媒体惯常利用女性游泳身体,并以偷窥的心态加以渲染,以满足读者的窥探欲望,进行商业牟利。女性游泳形象成为媒体的消费工具、读者的性欲对象,私人身体问题被放入公共领域批评讨论。
图14 《童月娟在大陆游泳池试新游泳装》
图15 《影人私生活:陆露明》
无论报刊上女性游泳运动员的报道,还是画报上穿泳装的女明星形象,之所以能有如此多篇幅的报道,除却媒体消费外,还应注意这其实也是女性主动参与的结果。对于女性游泳运动员来说,运动会是一种公开活动,为赢得观众好感,她们不仅向观众展示运动技巧,也讲究外观,甚至以摩登、新派的装束引领风骚,使媒体得以借题发挥。如上文提到的杨秀琼引人遐想的比基尼泳装,正是利用游泳身体引领风骚,凸显与自炫自我形象。且1930年代的游泳不仅是一项健身运动,也是一项时尚娱乐活动,《此所谓摩登女子也》中描述的几件时髦事儿为“与秘书长游泳、委员长跳舞、外长打牌、部长兜风、次长喝酒、公子哥儿上夜花园”,并定义“此所谓摩登女子也”。游泳与摩登的关系可见一斑。对于大众来说,游泳是一种“摩登”玩意儿,不会游泳的人也非常乐意参与其中,自由、个性、时尚成为游泳的代名词。陈建华认为在当时的上海,受好莱坞女星的影响,女子穿泳衣已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了。[7]237-244身着时髦泳衣的都市女性主动关注并展演着时尚的身体,利用媒体曝光提升知名度,受到赞美与追捧,成为偶像明星。拍摄泳装照片一时成为潮流,很多不会游泳的女性都沉浸其中。1940年《青青电影》刊载的漫画《电影漫画:游泳》(见图16)描述了一位女明星拍摄泳装照片的场景,其中一段对话如下,甲:“时代真进步得快,中国的电影女明星,现在全都会游泳了。”乙:“那里,他们不过在水里浸浸罢了。”丙:“下水浸一浸倒好了,有许多不过是借游泳做了个照相的背景罢了。”拍泳装照片甚至成了比游泳更重要的环节,泳装的时尚功能超越了运动价值。这种热衷拍泳装照的现象不仅在女明星中流行,也深受普通都市女子喜爱。1936年《中国漫画》刊载的漫画《游泳时节:漫画三则》其三(见图17)中,两名男子指着一张年轻女性身穿泳衣的照片展开如下对话:“这是小女的照片。”“穿游泳衣的吗?那她一定游泳得很好了!”“不!这是春天时装表演穿了游泳装照的,她还没下过一次水呢!”
图16 《电影漫画:游泳》
图17 《游泳时节:漫画三则》其三
泳装照的拍摄之所以如此盛行,其本身代表的摩登符号是重要影响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女性渴望被关注而主动曝光的心理。1938年《滑稽世界》“夏季游泳”专辑中刊载了一幅这样的漫画(见图18),三位身穿比基尼泳装的女性在沙滩上摆出曼妙姿势,右侧有一个手拿相机的男子,双方展开对话:女:“请问你拍我们的照片登在什么报纸上?”男:“并不登报,是我自己私人收藏的!”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男性窥视的合法化,他们可以在公共空间光明正大地拍摄泳装女性,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察觉被拍摄后的态度,她们并没有立刻制止,反而怀着想要被刊载在报纸上的心理配合展示,主动曝光。
图18 《滑稽世界》“夏季游泳”专辑漫画
当我们关注媒体是如何消费女性游泳身体的同时,被消费者其实也在为自己的曝光创造机会。媒体的曝光对女性来说是难得的在公共领域露面的机会,它为女性身体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展演平台,为其提供了一个表达自我身体的机会。长久以来被限制在家庭内部空间中的女性,不仅得以进入公共空间中活动,还利用媒体主动参与制造舆论活动,扩大影响力。
五、余论
在“性别化的空间”的划分下,长久以来女性被“男主外,女主内”的空间意识限制在家庭空间内部,公共空间则是男性活动展演的专属领地,女性成为“’看不见’的隐身人”[22],“与男性向外扩展的竞技场相反,女性的职责在锅灶和织机上。她的定位是向内的,在个性、外表和行动上,她都应是内敛的”[23]。此外,传统图像中的空间隐喻也形成固定的“外—内”“公—私”格局。近代以来,女性在五四运动的裹挟下得以逐步进入公共空间活动,尤其1930年代的上海,电影院、城市公园、游泳场、百货公司等新兴都市公共空间都发展成熟,女性的身影充盈其中。然而,“一旦出门在外置身于公共空间中,妇女必须谨慎”[24],女性在进入公共空间后不可避免地要承受来自他者的视线,女性身体成为被凝视的主要客体,面对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女性身体”作为视觉对象,总是承受着被想象、被凝视、被消费的压力,但1930年代上海报刊中有关“游泳”的图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水世界”:近代游泳场作为一种全新的公共空间,为女性活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一步步影响着从身体发现、身体观看到身体展演的全过程。女性身体在这个特殊场域可以被合法地“观看”,而“被观者”也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展演,同时又作为“观者”颠覆传统主客视线,在“观者”与“被观者”之间产生张力与纠结。正如伊沛霞所言:“最好的妇女史不仅仅告诉我们历史上的女人;妇女史挑动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历史和历史进程的理解。”[25]对于近代游泳场中女性身体的研究,我们不仅想要还原当时的女性游泳现象,窥探她们是如何在公共领域和大众视线中活动的,更想通过游泳场这个特殊空间映射“性别化的空间”等问题。被时代要求推上风口浪尖的女性不再沉默,而是抓住展演机会努力发声,在与周围环境的对抗中进行主体建构,力求打破二元固化,这一时期的“女性身体”形象不再单薄,反而充满迷人的张力。
参考文献:
[1] 影丝.裸浴与健美[J].玲珑,1936,6(28):2151-2153.
[2] 苏全有.民国时期女性游泳运动缘何兴起[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3,39(8):53-57.
[3] 李雅琪.游动的“媒介”:游泳运动场域中女性身体的转译及传播实践(1927—1937)[J].未来传播,2023,30(5):90-98.
[4] 李楠,孙淑慧.从“柔弱美”走向“健美”:20世纪30年代中国女性身体观的文化嬗变[J].体育与科学,2024,45(3):45-53.
[5] 游鉴明.运动场内外: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6] 游鉴明,黄铭明,等.春蚕到死丝方尽:邵梦兰女士访问记录[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5:65-66.
[7] 陈建华.摩登图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
[8] 福柯.性经验史:第1卷 认知的意识[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121.
[9] 游鉴明.无声之声Ⅱ:近代中国的妇女与社会:1600—1950 [M].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142.
[10] 崇淦.“全国运动大会特刊”引言[N].申报,1930-04-01(11).
[11] 罗薇.谈女人的美[J].北洋画报,1936,30(总1453):1.
[12] 佚名.健美运动[N].时报,1934-11-16(7).
[13] 舒如云.拥护裸足运动[J].玲珑,1933,3(104):1210-1211.
[14] 集熙.女性的哀鸣[N].大晚报,1933-08-18(6).
[15] 黎德明女士.各国女青年的健身运动[J].玲珑,1937(294):2088-2092.
[16] 佚名.夏季绿波中开始浮动红男与绿女[N].大晚报,1934-05-19(5).
[17] 王淑贞.女选手宿舍写生[N].吴县日报,1935-10-18(8).
[18] 黄影呆.游泳碎锦[N].申报,1935-08-24(18).
[19] 伯格.观看之道[M].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0] 柏霖.奏着狂骚曲的游泳池[N].大晚报,1935-06-19(7).
[21] 佚名.杨秀琼的乳罩[J].娱乐周报,1935,1(15):369.
[22] 洪镰德.女性主义在国际关系学说中的挑战与定位[J].国际研究季刊,2011,7(2):93-128.
[23]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5.
[24] 戈特迪纳,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M].黄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48.
[25] 伊沛霞.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M].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39.
本期编辑/张眉
图源/网络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