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赋
呼延光民
时维仲夏,节届端阳。檐角艾蒲凝碧,门楣符箓生光。千门裹粽,糯香漫于九域;万舸竞舟,棹影翻乎三湘。盖闻此节之肇,或系恶日禳灾之古俗,或缘忠魂殉国之流芳。今以屈子事,赋而咏之。
昔者楚臣屈原,含章挺秀,抱玉怀芳。辅怀王以修明法度,联齐抗秦;忤权奸而遭谗被放,去国怀乡。叹郢都之破,哀生民之殇,遂抱石沉汨罗,以殉宗邦。时维五月五日,江涛呜咽,楚地悲凉。乡人为悼忠魂,遂有龙舟竞渡,劈波斩浪寻故影;黍米投江,裹叶为粽饲鱼肠。千载而下,角黍盈盘,犹带沅湘之水韵;龙舟击楫,长歌正则之华章。
若夫伍子胥愤沉钱塘,曹娥女孝殉父江,虽其事各异,然忠魂孝魄,皆与端午之精神同光。更有先民观天时以制节,察暑气而禳殃——插蒲艾以驱疫,饮雄黄而避瘴,采兰沐芳,佩符纳祥,此亦时令之智,融入节俗之绵长。
今逢佳节,登楼远眺:江渚龙舟如箭,击鼓声震八荒;巷陌粽香似缕,炊烟漫过粉墙。孩童额点雄黄,笑靥映着五彩缕;老叟杯倾蒲酒,浩叹融入《离骚》章。叹岁月流转,而节俗恒昌,盖因忠魂不泯,孝意长扬,更兼民俗与时偕行,遂成华夏文脉之泱泱。
噫!屈子投江,留丹心照汗青之浩气;龙舟竞渡,扬华夏不服输之铿锵。粽角尖尖,裹尽千年风雅;艾香袅袅,熏得万代安康。且歌且舞,共醉端阳之景;亦诗亦赋,长歌盛世之昌。
25.5.28.晚写于青岛
文心一言赏析:
一幅端午文化的立体画卷
——《端午赋》赏析
呼延光民所作《端午赋》以端午佳节为载体,融历史追怀、民俗考镜、文化哲思于一体,通过典雅工丽的辞赋笔法,展现了端午节深厚的文化意蕴与精神内核。全篇以时空为经纬,以人物为轴心,以民俗为血肉,织就了一幅端午文化的立体画卷。
一、时空交织的叙事结构。赋文开篇即以“时维仲夏,节届端阳“点明时间坐标,通过“檐角艾蒲凝碧“的微观特写与“糯香漫于九域“的宏观视角,构建出端午特有的时空意境。继而以“昔者楚臣屈原“开启历史回溯,将现实场景与历史追忆自然衔接。在时间维度上,既呈现“千载而下“的纵向传承,又捕捉“今逢佳节“的当下图景;在空间维度上,既有“三湘“的地理坐标,又有“八荒“”万代“的时空延展,形成多维立体的叙事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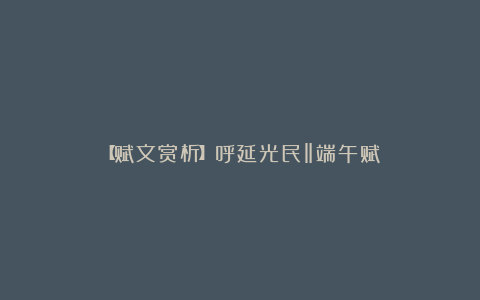
二、典故群像的文化厚度。文中巧妙化用屈原、伍子胥、曹娥三大历史典故,构建起端午文化的精神谱系。对屈原的书写尤为精妙:以“含章挺秀,抱玉怀芳“状其品格,用“辅怀王以修明法度“与“忤权奸而遭谗被放“的对比彰显其政治理想,借“抱石沉汨罗“的悲壮场景完成精神升华。伍子胥的“愤沉钱塘“与曹娥的“孝殉父江“,既丰富了端午的文化维度,又与屈原形成忠孝互文,共同诠释“忠魂孝魄同光“的节日内核。
三、民俗事象的象征体系。作者以诗性笔触解构端午民俗,赋予其深层文化密码。龙舟竞渡的“劈波斩浪“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寻故影“的精神追寻;角黍投江的“裹叶为粽“超越饮食习俗,成为“饲鱼肠“的祭祀仪式。插蒲艾、饮雄黄、采兰沐芳等习俗,被赋予“驱疫避瘴“的生存智慧与“佩符纳祥“的生命祈愿,构成完整的民俗象征系统。特别是“孩童额点雄黄“与“老叟杯倾蒲酒“的细节,以生命代际传承暗喻文化永续。
四、辞赋语言的审美特质。全文承续汉赋遗韵,展现鲜明的语言美学:四六句式错落有致,如“糯香漫于九域,棹影翻乎三湘“形成空间张力;对仗工整精妙,“龙舟竞渡“与“角黍盈盘“,“忠魂不泯“与“孝意长扬“构成语义镜像;用典自然无痕,屈原事典与《离骚》意象的化用,使历史记忆与文学传统水乳交融。同时,“江涛呜咽“”艾香袅袅“等通感修辞,赋予静态民俗以动态生命。
五、文化精神的现代阐释。赋文未止于传统咏叹,更蕴含现代性思考。“民俗与时偕行“的论断,揭示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内在逻辑;将端午精神升华为“华夏文脉之泱泱“,赋予节日以文明传承的宏大意义。结尾“长歌盛世之昌“的咏叹,既是对历史文化的致敬,更是对民族精神的当代确证,完成从民俗叙事到文化自信的升华。
此赋以端午为镜,照见中华文明的生生之德。在历史回响与现实脉动的交响中,在典故考据与民俗描摹的互文里,在语言雕琢与精神提炼的平衡间,展现了传统节日作为文化基因载体的永恒魅力,堪称当代辞赋创作中咏史怀节的上乘之作。
(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