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1)内森身上的正义感,一方面源于他的本性,一方面可以说被利用了。后者正如那些将年轻人、甚至普通人作为代价所利用的力量一样,他们宣扬一种遥不可及的主义、理念、乌托邦,以此欺骗我们为了那个未来,忍受当下所有那些不可忍受的东西。艾拉利用了内森,将正义感转化到了一个与思辨、内省观念截然不同的道路上,这条道路的迷幻性在于:身处其中的人可能高度亢奋、高度反叛、六亲不认、不容反驳与质疑,相信自己如果不是救世主,至少也是救世主的有力助手,相信必须要有颠覆和牺牲,革命,必须要有革命。
作为必须付出的代价,内森以为首先就要背叛父亲,主题是应该反对还是赞成脱离民主党的进步党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每晚在厨房吃晚饭,我都劝父亲投票支持亨利·华莱士和恢复新政,父亲则尽力要让我明白在这类选举中妥协的必要性。然而我是以托马斯·潘恩这位美国历史上最不妥协的爱国者为英雄的,单是听到’妥协’这词的第一个音节,我就会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对着他,和十岁的弟弟说,以后只要父亲在,我就绝不在这张饭桌前吃饭。”
令人心生敬意的是,作为足科医生的父亲继续寻求努力——正如每一对父母,无论子女怎样,都从未放弃让他们摆脱成长的泥沼——“他认为他作为父母有责任跟我探讨,我还不能生气”。当内森得意洋洋于将成为艾拉的嘉宾、去参加华莱士的聚会的时候,父亲说“他不会拦着我,但希望我起码听完他的话之后再做最终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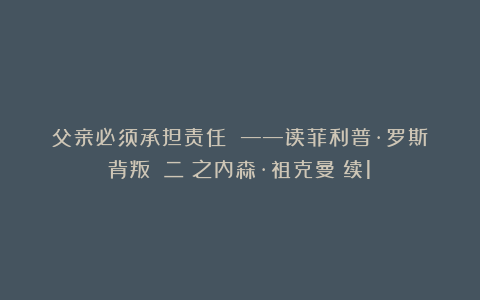
“父亲对我很认真,这点和林戈尔德兄弟一样,但是父亲没有艾拉那种政治上的无畏,没有默里的文采,最主要的是父亲做不到像他们那样不关心我举止是否得体、会不会长成个好孩子。林戈尔德兄弟好比拳赛中快拳左右开攻,把我引入大赛,引我探知何为真正广泛意义上的人。他们推动我进行严谨缜密的思维,现时的我回顾当年,对此也很认同。他们不在意我会不会做个好孩子。只在意我的信念。他们对我是没有做父亲的责任的,父亲的责任是引导儿子规避各类潜在危险。这些事父亲是要操心的,老师则不用。父亲要操心儿子的行为,操心怎么让自己的小汤姆·潘恩适应社会生活。可是一旦小汤姆·潘恩已经为成人圈子所接纳,他父亲却仍当他是个小男孩来教育,这父亲就没指望了。没错,父亲要担心可能出现的危险陷阱,他不担心就不对了。但无论如何,父亲还是没指望了。小汤姆·潘恩只能将父亲甩在一边,背叛父亲,义无反顾跨向人生第一个陷阱。然后独自一人,这样才达成人生真正的统一,从人生一个陷阱迈向下一个陷阱,直至墓穴。若无意外,这总归是他落入的最后一个坑吧。”
父亲只要求他要掌握全部真相,“没有事实真相,你没法做出明智决定”。他提出自己的理由——“尊敬的总统遗孀罗斯福夫人后来何以不再支持享利·华莱士转而反对他呢?哈罗德·伊基斯是罗斯福信任的忠诚的内政部长,当之无愧的伟人,他何以不支持享利·华莱士转而反对他呢?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有抱负的产业工会联合会又何以撤回了对亨利·华莱士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呢?是因为共产党势力渗透进了亨利·华菜士的竞选活动。”“父亲不想让我去集会,是因为共产党几乎完全控制了进步党。父亲说亨利·华莱士不是太天真,毫不知情,就是太狡诈,不肯承认——不幸的是,后者更有可能。但是共产党人,尤其是来自为共产党所控制的工会,已经被产业工会联合会开除的那些——”
儿子的反应是所有视父亲为阻碍他成为一个男人的愤怒少年的典型反应——“’你这个反共分子!’我吼道,随后离家,坐14路车去了集会。”(未完)
评价: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