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家最早能在中国生存下来,还是依靠道家。
前面讲佛像顺着丝绸之路,叮叮当当地传到了中国。说佛是一个神,大家能理解。
但是佛学思想,当时的人一听,直接就懵了。
比如佛学讲“空”,讲“无我”,说世界万物,包括你自己,本质上都是虚的,空的,像做梦一样,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
当时的人只会觉得,“扯淡!我这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我住的房子,我吃的饭,怎么就空了?我这么拼命干活,难道是为了一个“空”吗?”
你看,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维度的对话。
这文化差异,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
当时的人理解佛教,就好像你现在回到古代,给一个教书先生解释什么叫“元宇宙”。
你怎么解释?你说这里面有另一个世界,他能理解吗?理解不了。
那怎么办呢?
聪明僧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叫“格义”。
“格义”是啥?
“格”,就是格量、比对。“义”,就是义理、概念。
说白了,就是“连连看”。用大家已经滚瓜烂熟的概念,去比附、去解释佛学里那些陌生的概念。
简单粗暴,但有效。
你看,这招“格义”,就是花最小的理解成本,去够一个陌生的思想。
这个“格义”,就好像你跟那个古代教书先生解释“元宇宙”,你不能直接讲,你得打比方。
你说:“老先生,您读过《西游记》吧?孙悟空拔根猴毛,能变出无数小猴子,这就是一种’虚拟分身’。”
“您读过《庄子》吧?庄周梦蝶,分不清哪个是真实,元宇宙也有点这个意思。”
先生一听,虽然还是半懂不懂,但他至少能“哦”一声,觉得这玩意儿好像跟我们家的东西有点关系,不是纯粹的天外来物。他有了一个可以理解的“抓手”。
早期的僧人们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发现,老子、庄子的“玄学”思想,跟佛学“般若”,特别好配对。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地“格义”运动就开始了:
佛教讲“空”,说万物没有实体。这太难懂了。怎么办?好办!老子不是说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吗?行,那佛教的“空”,就约等于我们道家的“无”吧!用“无”来解释“空”,大家一下就感觉亲切多了。
佛教讲“涅槃”,说是一种寂灭的、最终的解脱状态。这也很玄。怎么办?也好办!老子不是讲“无为”吗?追求一种顺应自然、不强求的状态。行,那“涅槃”就跟“无为”差不多!
佛教讲“菩提”,是觉悟、智慧的意思。这个也好理解!咱们道家有“道”啊!得道成仙,得道开悟。那“菩提”就是“大道”!
佛教讲“真如”,是宇宙万法的真实本体。这个更简单了!道家有“本无”,认为“无”是宇宙的本源。那“真如”就是“本无”!
你看,经过这么一番“本土化编译”,虽然有点怪,但至少,能跟我们中国人正常交流了。
那么问题来了?
“格义”这事儿,到底是好是坏?
答案是:它既是引领精英入门的“蜜糖”,也是遮蔽佛学真义的“毒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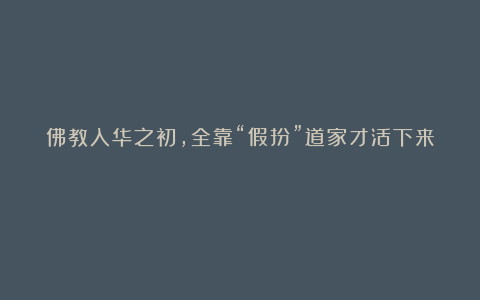
首先,它是蜜糖,是救命的蜜糖。
在刚来的几百年里,“格义”是唯一可行且最高效的文化“破冰”工具。
它最大的功绩,在于成功地将佛教带入了当时中国社会最有影响力的阶层——门阀士族。
高僧道安就曾说,早期般若类经典之所以能够广泛流行,正是因为它们所谈论的“空、无”等思想,与当时盛行的老庄玄学有相似之处。没有这帮人“带货”,佛教很可能就跟其他民间信仰一样,拜一拜,求个福报,然后就没然后了。
佛学正是搭上了玄学这趟“思想快车”,才能够一跃成为能够与本土最精深哲学对话的高级思想体系。
但是,任何快捷方式,都是有代价的。它也是慢性毒药。
“格义”这种“连连看”式的理解,说白了,是一种“模糊匹配”,它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更不是“精确”。
这就出问题了。
道家的“无”,真的是佛教的“空”吗?
完全不是一回事!
道家的“无”,是跟“有”相对的,是“有”的来源,它是一种“本体论”上的“无”,但它能“生”万物。
而佛教的“空”呢?它不是说“没有”,而是说万事万物都是由各种条件组合而成的,本身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独立存在的“自性”。它是一种“认识论”上的“空”,是“缘起性空”。“空”本身,什么也“生”不出来。
你看,这差别,大了去了。
这就好比,你跟一个只见过马车的人解释汽车。你说:“汽车,就是不用马拉的车。” 他听懂了吗?懂了,大概知道是个车。但他真的懂汽车吗?他不知道发动机,不知道变速箱,不知道这车怎么开起来。他理解的,只是一个“马车的平替”而已。
用道家的“无”去理解佛教的“空”,就是这种情况。中国人理解的,是一个“道家化”了的佛教。大家觉得,佛教嘛,不就是印度版的《老子》《庄子》嘛。
这种理解,不能说全错,但肯定不精确。
这种“误会”,导致早期的佛学研究,走了不少弯路。当时的佛学流派,有所谓的“六家七宗”,但他们争论来争论去,很多时候,争的都不是纯正的佛学思想,而是在用道家的思想,去解读佛经时产生的各种分歧。
这就像一群人,拿着不同版本的《哈姆雷特》,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言去翻译和理解,然后互相争论哪个翻译版本更正宗。他们吵得天翻地覆,但可能,他们离莎士比亚的原意,都还很远。
所以“格义”,是佛学在面对中华文明时,一次充满智慧、却又无可奈何的“自救”。
它是一剂为了“活下去”而服下的猛药,虽然保住了命,也留下了长期的、棘手的后遗症。
时间久了,问题就暴露了。
中国的修行者和思想家们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他们发现,“格义”这种方法,作为入门的“拐杖”,可以。
但是,你不能拄一辈子啊!你得扔掉拐杖,自己学会走路啊!
很多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修行上的关键点,根本就说不通。佛说的,和道说的,终究不是一回事儿。
一种强烈的渴望,像暗流一样,逐步蔓延开来:
我们不要“替身”了!我们要看“原版”!
我们不要“像佛的”思想,我们要原汁原味的、“佛的思想”!
这股巨大的渴望,像是在积蓄力量,呼唤着一位真正的大神降临。一位能够彻底砸碎“格义”这座华丽但限制人的桥,带领所有人渡过湍急的文化河流,直达彼岸的伟大翻译家。
整个中国的佛教界,乃至整个东亚的文化圈,都在为这位大师的登场,做着漫长而焦灼的铺垫。
他,就是即将以一人之力,扭转整个时代思想航向的——鸠摩罗什。
从此以后,“格义”这种方法,就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的佛学研究,也从一个“模仿”和“比附”的阶段,进入到了一个“消化”和“创新”的新阶段。
关于这位“翻译之神”如何凭一己之力,让佛祖说上标准“中国话”的故事,咱们下次再聊。
我是亿文,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