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先生的字,像他笔下的小孩儿,圆头圆脑的透着欢喜气。笔画不讲究锥画沙,倒似用秃铅笔在粗纸上画画,线条毛茸茸的,还带着点儿稚拙的歪斜。写“佛”字不显宝相庄严,倒像邻家阿婆抱着胖孙儿在日头底下打盹儿,松垮垮地透着暖意。
细看那些字,结体是松松的。竖笔不争着站笔直,倒像柳条儿让风吹弯了腰;横画也不绷着劲儿,倒似晒衣绳坠着半干的蓝布衫,自然地下垂着。转折处尤其好看,圆融融不见棱角,像把玩久的玉石边角,温吞吞地裹着一层包浆。这般字,不是供在檀木架上的摆件,倒是炕桌上盛绿豆汤的粗瓷碗,拙得可亲。
墨色也随和。浓时不过砚底余沥,淡处倒像涮笔水洒的痕,枯笔飞白像初雪落在草垛上,星星点点地透着亮。最妙是行气,字和字挨挨挤挤,像弄堂里乘凉的人,竹椅碰着竹椅,蒲扇叠着蒲扇。这个“人”字往左让半步,那个“心”字往右挪一寸,倒让出些穿堂风似的空当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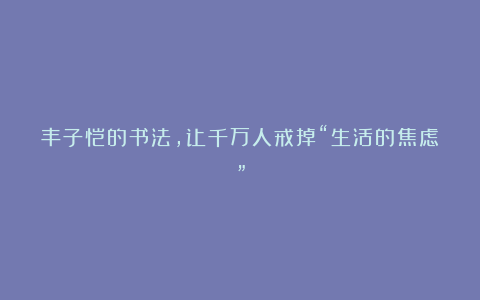
残墨处藏着真慈悲。页脚洇开的水渍像娃娃的尿片子,皱巴巴地蜷着;秃笔岔开的飞白,恍若老猫蹭在棉袍上的绒毛。这般不讲究处,偏叫人想起他画里那些护生的心思——断腿的蜻蜓,落水的蚂蚁,原都值得疼惜。笔墨里的缺憾,倒成了菩萨低眉时的那声轻叹。
题画字尤见赤子心。山水间忽题“阿宝放学早”,五个字圆鼓鼓地挤在山坳里,像草丛突然蹦出只野兔;给女儿的信笺上写“软软勿哭”,墨痕还湿着,倒似刚用手指头抹过泪痕。这般字,原不是要人供在案头临摹的,倒像灶台上温着的姜糖水,专为寒夜里暖手暖心。
丰先生的墨痕,是写在人间烟火里的偈语。当我们摩挲那些毛边的纸页,仿佛触到他握过炭笔的手温,听见童谣混着木鱼声穿过弄堂。这般字的好,不在笔法森严处,而在那份对众生温柔的懂得——就像他画里总给油灯添根新棉线,好让光多暖半寸寒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