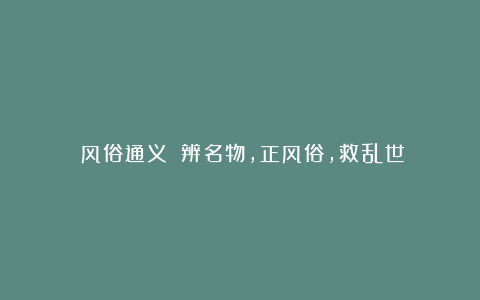|
东汉末年,帝国大厦将倾,社会陷入深重的失序与迷惘。连绵的政治腐败与天灾,侵蚀了儒学的正统光环,取而代之的是谶纬玄学的盛行与民间信仰的芜杂交织。在这个“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混乱年代,流言蜚语如同野草般疯长:传说汉武帝封禅时抽到了预示长寿的神奇筹策;汉文帝入京即位因故迟到,太阳竟为之重新回到正午……
这些光怪陆离的传闻,不仅在市井乡野口耳相传,被民众奉为真理,甚至许多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也深信不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位具有深刻文化自觉的学者——应劭,决心以笔为剑,为这个迷茫的时代重新勘定知识的边界与价值的尺度。
应劭,字仲远,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出身于累世通经的官宦世家。他本人博学多识,历任泰山太守、议郎等职,不仅熟谙典章制度(著有《汉官仪》),更深切关注现实社会的精神状况。
促使他提笔撰写《风俗通义》的直接动因,正是弥漫于朝野上下的虚妄之风。在自序中,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莫能原察。”他担心这些“积非成是”的流俗会误导后世,使人们“益以迷昧”。
因此,他著书的核心宗旨非常明确:“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即要通过辨正流俗中的荒谬之处,使其最终合乎儒家经典的义理准则。
这绝非单纯的学术考辨,其背后是深沉的时代忧患与士大夫的政治担当。面对“仁义陵迟,礼乐崩坏”的末世图景,应劭相信,混乱始于人心,救世必先正俗。他试图通过文化上的“拨乱反正”,为社会重建一套基于儒家伦理的认知与行为规范,从而呼应“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秩序理想。尽管原书三十卷在后世散佚严重,仅存十卷,但现存《皇霸》《正失》《愆礼》《怪神》等篇目,仍清晰构成了一个从考辨历史、批判虚妄到确立规范的完整思想体系。
《风俗通义》最醒目的贡献,在于其充满理性精神的系统性“辟谣”。应劭如同一位严谨的侦探,对当时流行的各类虚妄言论进行了分类侦查与有力辩驳,其范围之广,方法之缜密,令人叹服。
在《怪神》篇中,应劭深入剖析了民间神灵的“制造”过程,展现了惊人的社会洞察力。其中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鲍君神”的诞生:有乡人设网捕得獐子,暂存于泽中。路过商旅见状,恶作剧般将随带的腌鱼(鲍鱼)放入网中离去。乡人归来,不见獐子而见鲍鱼,惊以为神。此事传开,“转相告语,治病求福”,竟发展至为这块腌鱼建起祠庙,巫祝纷至,“钟鼓不绝”,借机敛财。应劭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类“神灵”纯属人们道听途说,随便立神祠的产物,其盛行背后是巫祝“赋敛受谢”的经济驱动。
对于史书与传闻中的奇谈怪论,应劭展现了卓越的考据功夫与逻辑思辨能力。《正失》篇是其主战场。
针对“燕太子丹感动天神”说:他依据《史记》等典籍,指出太子丹是怕死而逃回罢了,自己被父亲所杀,身首异处,他怎么可能招致天降粟米这类的祥瑞呢?之所以有这样的传闻,是因为太子丹喜爱结交宾客,礼贤下士,毫不吝啬,所以民间就夸饰成这类传闻了。用常识逻辑否定了其可能性。
在“孝文帝”一节中,应劭依据史实,认为休养生息的汉文帝比不上“孝宣中兴”的汉宣帝,他引用刘向之言,明确指出后代对汉文帝的溢美之词,完全是谏官编造出来的。
对《尚书》中“夔一足”的记载,他引用孔子之言澄清,其本意是“有夔这样的人一个就足够了”,而非指夔是独脚怪物,纠正了望文生义的误解。
针对名臣袁贺乃其父居丧期间所生,取字“元服”以掩过的诽谤性流言,他考证出“贺”名源于其出生时正逢汉安帝行冠礼(元服),百官庆贺,故以“贺”为名,字“元服”以纪瑞。一桩污名化传闻,就此得以洗清。
在《声音》《山泽》等篇中,应劭对乐器、山川之名进行了客观的考释。例如释“笙”时,他援引《世本》“随作笙”之说,进而阐明其形制“像凤之身”,其音律象征“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谓之笙”。这一解释既追溯了人文起源,又揭示了自然物候的象征意义,整体上保持了平实考辨的风格,全无怪力乱神之色彩。
“辨风”旨在破妄,“正俗”志在立范。应劭的终极目的,是依据儒家经典重建社会价值与行为规范,以期拯救世道人心。
《愆礼》《过誉》两篇直指士大夫阶层的行为扭曲。他严厉批评那些为博取孝名而过度哀毁、逾越丧礼的行为,认为其违背人性,非真孝道。同时,他痛斥士人之间互相吹捧、名不副实的“过誉”之风,认为这导致“善善恶恶”的标准混乱,使真正的美德黯然失色。在《十反》《穷通》中,他通过对比不同人物在面对功名利禄、穷达逆顺时的抉择与态度,彰显其境界高下,为世人树立符合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道德标尺。
面对民间“淫祀”泛滥,冲击官方意识形态,应劭在《祀典》篇中系统性地确立了国家正统祭祀的谱系。他引经据典,强调只有“天地、祖宗、山川、先农,有功于民众及前哲令德之人”才配享祭祀”。而其他无稽的杂祠崇拜,则属于“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这实质是从国家礼制层面,与民间信仰争夺文化领导权,力图将民众的精神世界重新收束于儒家礼治的框架之内。
全书开篇《皇霸》,即追溯“三皇、五帝、三王、五伯”等名号的由来与正统序列,旗帜鲜明地表明其“考信于六艺”的根本原则。这为全书的“辨”与“正”奠定了不可动摇的学术基石。他深信“为政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将风俗的良窳视为政治成败的关键,体现了儒家“教化治国”的思想精髓。
《风俗通义》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一部普通的“辟谣”笔记或风俗资料汇编。
首先,它是研究汉代社会的“活化石”。书中保存了大量正史不载的一手社会史料:如“女娲抟黄土作人”“李冰斗蛟”等著名神话的最早文献出处之一;散佚的《姓氏》篇通过辑佚,保留了珍贵的汉代姓氏源流观(“姓者,生也”);而《祀典》《愆礼》中对祭祀礼仪和士人行为的记录,更是深入了解汉代礼制实践与社会心态的窗口。
其次,它开创了“辨风正俗”的学术传统。其融合考据、批判与经世诉求的独特体例,区别于《白虎通义》的经学教条和《论衡》的哲学泛论,形成了立足现实、考辨结合的务实学风,对后世《荆楚岁时记》《东京梦华录》等民俗学者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尤为有趣的是,其文学价值使之被后世视为“小说之别祖”(龚自珍语)。《怪神》篇叙述灵异故事,如“鲍君神”“张辽杀怪”等,情节曲折,描写细致,氛围营造出色,多篇被干宝《搜神记》几乎全文收录,堪称魏晋志怪小说的先声。《十反》《愆礼》等篇品评人物,往往三言两语即神情毕肖,开《世说新语》类志人小说清谈隽永之风。
《风俗通义》是应劭面对当时社会迷信盛行、真假难辨的现状,以儒家义理为依据展开的一次文化反思与匡正。这部著作也为我们今天带来启示:在信息纷杂的时代如何保持清醒,在价值多元的社会如何守护底线,在文明传承中如何既有坚守又有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