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日收拾行囊时,从箱底摸出一张泛黄的车票。票根上印着“K528次”,墨迹被汗水洇得模糊,边角蜷曲如枯叶。指尖摩挲过“终点站:五里镇”的字样,恍惚又见那年夏天——父亲扛着蛇皮袋站在月台,灰衬衫被汗浸透,背影像块腌过头的酱菜。
车厢里挤满相似的面孔:扛着编织袋的农民工、攥着保温杯的妇人、蜷在座位下补鞋的老汉。他们的呼吸混着泡面味,在铁轨的震颤中发酵成粘稠的胶质。我缩在角落,看窗外风景如褪色的胶片掠过:稻田、坟茔、电线杆上歪斜的麻雀窝……直到暮色漫过车窗,才惊觉自己攥着那张车票,竟攥出了汗碱。
到村口时,月亮正悬在祠堂的飞檐上。青石板路缝里钻出几茎野草,被露水打蔫。远远望见老屋轮廓,门环上的铜绿又厚了几分,像凝固的血痂。抬手叩门,三声闷响惊飞了檐下的家燕。
门缝里漏出昏黄的灯,母亲举着煤油灯来迎。她鬓角的白发在风里飘,像极了灶膛里飞出的火星。“怎不提前说?”她嗔怪着,却将我冻僵的手塞进她袄兜。兜里暖烘烘的,有刚蒸的糍粑,有晒干的艾草,还有那件我儿时尿湿的棉袄——如今裹着樟脑丸的苦香。
柴火噼啪炸开火星,母亲在灶台边转悠。铁锅里的腊肉滋滋冒油,油星子溅在补丁围裙上,烫出细小的洞。我望着她佝偻的脊背,忽地想起二十年前:那时她能一手抱着我,一手往灶膛添柴,火光映得她脸庞通红,像熟透的红柿子。
“尝尝这个。”她端来一碗酒酿圆子,米酒混着桂花香。我舀起一勺,甜味在舌尖化开,却尝出满嘴的涩。窗外的月光淌进来,把我们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土墙上。她的影子单薄如纸,我的却重重叠叠。原来漂泊半生,归来竟比离家时更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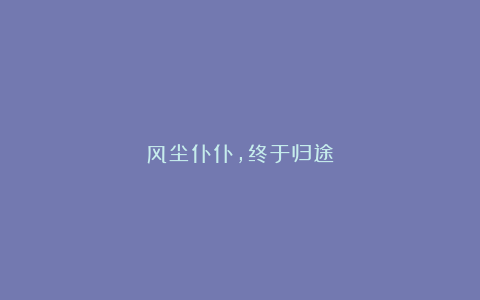
次日清晨,我独自去寻儿时的晒谷场。野草已没过膝盖,稻田里竖着“商品房预售”的广告牌。几个戴安全帽的人蹲在田埂上抽烟,烟头明灭间,惊醒了沉睡的稗草。
风掠过荒芜的田垄,送来断续的蛙鸣。那声音像是从旧磁带里抖落的,沙沙的,带着杂音。我蹲下身,拨开一丛野蒿,竟见半截残破的蛙哨——漆面剥落,竹管裂了缝。恍惚又见父亲教我吹哨的模样:他鼓起腮帮,哨声清亮如裂帛,惊起满田的绿翅膀。
离乡那日,我又去石桥上坐了坐。桥墩上爬满青苔,缝隙里嵌着碎瓦片和烟蒂。桥下溪水瘦成一线,载着几片枯叶,慢悠悠地往东漂。
头班车进站时,桥身微微震颤。司机探出头喊:“小哥,走不走?”我攥紧装满腌菜的帆布包,看车尾的红灯渐行渐远。红灯熄灭的刹那,桥下的溪水突然发出呜咽,像极了那年送我远行的汽笛。
归途的车票终究要重新攥皱。此刻我蜷在异乡的出租屋里,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忽觉行囊里沉甸甸的——装着母亲塞的艾草香囊,装着石桥缝里的碎瓦,装着晒谷场荒草间的蛙鸣。
这些零碎的物什,在钢筋水泥的缝隙里发酵,竟酿出比酒更烈的乡愁。而那风尘仆仆的归途,原是场永无止境的轮回:我们带着故乡的碎片上路,又在异乡的站台上,把自己碾成新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