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意打扮好去见拉康。是穿粗花的呢,天鹅绒的,还是羊绒服。为了增加我的魅力,我甚至带着一瘸一拐的小伤痛,那是练法式踢打时被踢伤导致的。我坚持准时到达他约我见面的时间。他也做到分秒不差,不让我多等一秒。配合得天衣无缝。
Gloria 刚为我打开前厅的门,他办公室的门扇便随之开启。我们彼此报以灿烂的微笑。
很显然,尽管我刚才在等候室看见了其他病人,但他只在等我。诊室的门在我们身后关上。他把椅子摆在与书桌平行的位置。我在自己的椅子上坐下。
面对面。
从昨天到今天,我已经有时间布置好防御。我带着一种带点调侃的好奇凝视着他,翘起二郎腿,点燃一支烟——不,他一点也不介意,还递给我一个烟灰缸——我用几句克制的词句,像在叙述中随手撒落那些对我而言司空见惯却饱含分量的名字,向他描绘了一个聪慧散漫的业余者的光鲜形象,来到他面前——虽然我没有明说,但话语里已隐含——几乎是出于机缘与智性好奇的交织。
他似乎完全明白。他很欣赏。我也是。当我谈到自己在供职报社的工作时,他问我是否认识也在那儿工作的 Z 女士。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便如实告诉他。
他突然问我是否喝酒。我愣住了。不,我不喝酒。和所有人一样喝点葡萄酒,但若说专门为了喝酒而喝酒,那不。我是个运动员,怎么可能喝呢?他欣然同意了我的说法。
我一支接一支地点烟,他总是递给我烟灰缸。然后,他带着最后的微笑站起身来,谈话结束了。过去了多久?一小时?也许更久。我问他我该付多少钱。虽然没人告诉过我,但他报出的数字,我早已心中有数。我料定这笔费用会高得惊人。
果然如此。正好与我昨天向两位和我一样身无分文的朋友借到的数目一致。我便毫不意外地把那三张钞票递给他,它们立刻消失在他裤子的口袋里。他笑容满面地和我握手,说:“明天见。”
我告诉他,遗憾的是明天不行,因为我没有钱支付。他依旧握着我的手,我正思忖怎样抽回而不至于冒犯他。他像没听见似的开门,又重复一遍“明天见”。
我回到街上,喉咙发紧,心想这段微妙的关系会不会因为缺钱而在起步时就被扼杀。
我该去哪里筹钱?
我在心里盘算着所有可能借钱给我的关系。之前的经历已经让我明白,无论在爱情里多么热烈,哪怕曾给予或得到过极大的欢愉,一旦碰到金钱这个敏感的问题,一切都会戛然而止。前些日子,我因为一笔紧急债务需要短期过桥资金。那笔借款我说好只借四十八小时,并且在把支票交给对方作担保时,明确表明到期便可兑现。我那天找了三个人借钱,一个女人,两个男人。
这位女人很有名。她是歌手,也是歌舞秀的领班。每周日下午,我都会去她的化妆间找她。那里总是放着装满鱼子酱的水晶碗,还有冰镇香槟和伏特加。我坐着的地方能听见观众席的掌声和欢呼。她像一颗炸弹般闯进这间闪烁着亮片的闺房化妆间,热烈地亲吻我,解开我的衬衫。为了不被打扰,她的同性恋发型师像地狱犬般守在天鹅绒帘幕后。每当她的双眼迷离恍惚时,总会有人猛敲门,将她从我怀里拽走,投入观众的怀抱。
整场表演期间,这样的来回上演了好几次。她从沙发跃上舞台,又从舞台扑回沙发。间隙里,我便以鱼子酱慰藉自己。
我觉得,这样的亲密足以让我向她开口谈钱,就像她对我谈情时毫不掩饰一样。让我吃惊的是,尽管她很有钱,她却说我们俩都运气不好。就在那天早上,她不得不缴纳一笔巨额税款,几乎被掏空。我自己的钱两天后才能到账。我问她是否需要我帮忙。她热情地向我道谢,但拒绝了,说她能自己应付。
我那两个朋友里的第一个是歌手,现在依然很有名,他的歌到处都能听到。他那种迷失孩童般的气质,让我在他抑郁时总想照顾他——他的抑郁发作频繁。我偶尔会带他去多维尔,甚至体贴到为他安排一个女人。有时凌晨三点,他会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重新构建世界。我对他的喜欢足以让我开口求他帮这个忙。
出乎意料的是,他那天早上刚刚被税务局找上。我挂断电话,替他难过。半小时后,他又打来。他想到一个办法。如果说明是帮我,他只要找我们十个共同的朋友,各借所需金额的十分之一,就能帮我渡过难关。
我千恩万谢地拒绝了他的慷慨提议。
我的第二个朋友不是歌手。他比我年长许多,让别人唱歌的人,掌控着夜总会的帝国,在圈内被称作“和平法官”,也就是被同行推举出来,在边缘世界里调解纷争的智者和正直之人。
但这次也不走运:同样是因为税务。
他是唯一一个对我说了实话的人。几天前,他刚把一大笔钱借给了另一个朋友,那个朋友甚至不是他最亲近的人。
无论他们拒绝的理由是真是假,我都觉得这是种背叛,并在心里发誓,就算因此丧命,也绝不再让任何人有机会用这种回避来伤害我。
那晚以及之后的日子,我是怎么做到遵守这个誓言的?我真的遵守了吗?我已经忘了。
每次结束分析,Lacan 总是不容置喙地说一句“明天见”,这句话让我带着满手的冷汗,重新走进里尔街灰色的街道。第二天,我再次出现在他的诊室里,口袋里攥着好不容易才在前一天凑到的钱——这种每天的奇迹,我还能坚持多久呢?
他依旧保持着那种无比优雅的礼貌。香烟。大约下午五点,Gloria 会端来一只瓷碟,上面放着一杯茶和两颗枣子。他的语气如此友好,我几乎不觉得意外,若他开口请我与他分享。
除了品茶,他似乎也在细细品味我的言辞。
确认他不会认错人,这一点至关重要。我不动声色地巧妙展示自己的优点,既不显张扬,又渐渐深入到那些荒诞无聊的领域,在那里,驴子为了获得糠麸的声音——此处指他的声音——会变得比孔雀还要骄矜。
第三天,Gloria 并没有直接带我进他的办公室,而是先领我到后面的小图书室,把我和其他病人一起留了五分钟。我偷眼打量他们:他们是谁?为什么在这里?难道他们不知道 Lacan 正在等我?
一进门,我便向他提起他的“迟到”。
他立刻向我道歉,非常客气地解释了原因,最后一句话却说:“不是我的责任。”这句话让我彻底茫然。
第五次会面结束时,他像往常一样在收下我的钞票后,握住我的手,突然说道:
“我决定给你在分析中留个位置。”
我愣愣地看着他,不明所以。
“可我以为我们已经开始了?”
他只是站起身来,说:“周一见。”
周日那天,我发现任何与即将到来的见面无关的事情都让我心烦。
奇怪的是,之前的几次见面我从未向任何人提起。除了我深爱的女人——不过我也是五六年后才告诉她的——更何况,我当时几乎与外界隔绝。早已厌倦了那种快速的、多重的、表面化且无疾而终的交往,那是某种新闻行业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交往曾让我反胃到极点,如果要我想象地狱,那必定是一个社交场景:灯火辉煌的宴会厅,宾客云集。而我被困在正中央,一只手里夹着烟,一只手端着满杯,女主人不停把一个个我再也不会见到的人带到我面前介绍。
我同样无法忍受与人相遇带来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些虚假的关心与追问。于是我决定换个城区,在城市中隐没。我没想到这会如此简单。那些被我们误以为属于自己的大都市,只因在某些地方会有人喊出我们的名字,但其实,它们完全允许人无声消失。事实上,在时间与空间中,在我们彻底隐形之前,我们的活动范围不过是那条重复的轨迹:几个朋友,三家餐馆,缴费的生活设施,工作场所,夜晚出没的地方。曾经是微型世界国王的人,一旦忘记了这些落脚点,便会在陌生人中变得匿名无名。
一切联系切断,也就是“去–异化”,我只服从于把自己置于括号中的紧迫需要,漂流在一条中性的轨道上,在那里,我不再能“命名”,因为我已忘了指称事物的词,忘了指向面孔的名字,忘了那些将我指向自己的面孔——那意味着几乎虚无——我对所有流言突然变得冷漠,对气味充耳不闻,对奔忙充满抗拒。我唯一的计划就是活在当下。除了我正在进行的工作,我对明天毫不关心,就像不在意自己空空的口袋一样,也许隐约意识到,如果我再次回到那片丰沃的牧场啃食青草,将会失去成为我自己的最后机会。
我们就是我们所渴望的。
但我们对自己的渴望一无所知。而这种渴望,虽然我们不了解它的本质,却以最独特的方式打击着我们的“自我”,没有任何一个人选择了让它栖居于我们体内。它是“被书写”的。它先于我们而存在。我们通过语言进入它的领域。
甚至在出生之前,我们就已注定,无论幸福还是不幸,总有一天要成为它的管理者。
这便是裂隙的来源。
因为这个构造我们的渴望并不属于我们。它通过话语,是大他者的渴望,是一个渴望着的大他者的渴望。
因此,作为渴望之存在者,我们的命运便是只能通向“存在的欠缺”。
五岁时,我画画。十四岁时,我渴望变老。老年对我来说会是温柔的。每流逝一天,都让我更接近那种完全的掌握,接近那一刻的谜团,在那里,天才的创造者终于触及纯粹色彩的强度,在死亡的边缘,抵达他们颤动的绝对核心。
二十八岁那年,十一月的某个夜晚,在电话呼叫的喧嚣声、Remington 打字机的急促声和香烟缭绕的雾气中,我突然感到一种闪电般的分裂,成为自己的旁观者,“看见”自己,嘴里叼着烟头,桌上堆满可怕的文件,两只耳朵各夹着一个电话,听着那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声音却一句也听不进去。一个问题刺穿了我:我在哪里?
在一家日报的办公室里。做什么?写那些所谓的“巴黎专栏”。
这太荒谬了,我是个画家。那么?
无意识并不是直线书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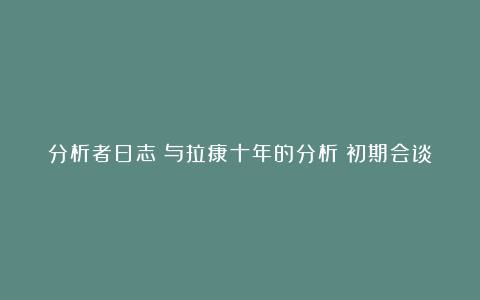
父亲为了丰富他所谓的我的“行囊”(那种一旦移动便会让人寸步难行的负担),梦想我拥有普遍的知识。
某天早晨,他说出一句奇怪的话:
“你也许该学学速记。”
“为什么?我是画家啊。”
“谁知道呢。万一有天你想去搞新闻……”
我记得自己就是读到这个。若当时有人把我的头放在断头台上,我也会发誓,自己确实看到了这段对话,并将它转化为一个攸关生死的拷问:“如果有人剥夺了你的绘画,你会死吗?”
令我羞愧的是,我的回答也是:不会。
于是我立刻断言,自己不配做画家:我的色彩便化作词语。
我的画笔,变成了一台史密斯·科罗纳打字机。
二十年后,我重读《给青年诗人的信》,却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我当年记忆中的那句话。在里尔克这部假托书信体的作品里——那些回应假想提问的回答——我曾经为自己想象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对话。
这正是无意识领域中错误的功能:为了活出大他者的话语,我甚至为自己编造了一个遮蔽自身渴望的虚假理由。
第一次去里尔街探访三周后,我在游泳池又见到了那个胖子。我那时太专注,以至于几乎忘了他的存在。自从他告诉我 Clavreul-Perrier-Lacan 这三个人的名字后,就没再联络过。
“你去哪了?”
“我开始做分析了。”
“跟谁?”
“Lacan。”
他满脸难以置信地盯着我看。
“他收你了?”
“这有什么稀奇的?”
他困惑地摇摇头。
“我以为他不再接新病人了。”
“你这话说得好笑!是谁给我的电话的?”
他的惊讶让我感到意外。倒不是我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特殊待遇——我们的会面费用足够高,这或许也算不上什么恩惠——而是我始终认为,任何医生都会接受所有求诊者。Lacan 的声名对我而言依旧没有任何实感,就像我没意识到他的时间有限。我迫不及待地想把我们最初的几次面谈告诉胖子。
可我立刻感觉到他的抗拒。他为什么要转移话题?我们曾无数次讨论过精神分析,现在,当他将我引到这核心之地,却突然装作不感兴趣。没等我开口追问,他就借口有急事,嘟囔了几句道歉,转身离去。
而就在那天早些时候,我又去见了 Lacan,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出现了难以言喻的变化。当下,我无法说清具体是什么变化,说实话,我也并不想深究。Lacan 依然和蔼、专注、热情。或许只是他沉默的时间更长?不知不觉间,他的沉默把我们的对话变成了我的独白:我不停地讲。被自己语言的快感迷醉,我说得越来越快,生怕他插话打断。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如何倾听。
后来,我不得不去乞求他一个眼神的默许,或是一丝嘴角的微妙不满。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我忙于倾听自己的声音,根本不可能真正听见自己,但他的某些话语却铭刻在我的记忆里。人们对鹦鹉的大脑研究甚少,只知道它们能够复制能指,换句话说,它们可以“重复”声音。我与它们共享这种声学天赋。但和它们一样,我也没有凭借声音抵达所指,也就是意义的特权。
我才做了不到十次分析,Lacan 就奢侈地丢下一句我无法理解的话,恰恰因为他知道我不可能懂。像往常一样,我一定又在进行一大段形而上学的长篇独白,突然停在一个问题上,这个问题的提出更是对我自己而非对他说的,因此刚一说出口,我便陷入沉默:
“灵魂存在吗?”
我本以为他会回以微笑。
结果他回答了:
“灵魂是条裂痕,而这裂痕,是我们作为说话存在者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当时的我,对算法、转喻、数论命题都毫无概念——算法?数论命题?转喻?——但我模糊地感觉到,这句表述背后隐藏着某个谜。
可惜,我缺乏解答它的钥匙。
他所说的裂痕指的是什么?进贡与语言之间有何关联?为什么作为“说话的存在者”,就必然要支付“贡品”?为了偿还什么?什么债?又或者,什么罪?
我怀疑地在心里反复琢磨这句话,却没特意去记住它。
但如果我今天还能一字不差地将它引用出来,那是因为我也许隐约预感到它所蕴含的意义的深度,并且确信,当我有能力破译它时,这个意义终将向我显现——这便是对“被认为知道之人”的信任,将人牢牢系住的原因。
实际上,这句话包含了拉康理论建构的几条重要主线:那条永远分隔能指与所指的横杠,这种分裂与“无意识的结构如同语言”之间的关系,主体因寻求超越而再度分裂,他为了抵御死亡的虚无而树立神祇的雕像,并为自己发明出一个灵魂。
人们往往不愿提及这些裂隙。
但我怎能略去自己在分析初期的“天真”呢?
要知道,字母表有二十六个字母。但要知道这一点,首先得意识到字母表的存在。
尽管我并未真正了解它,我却已经感受到它的最初影响,那是一种巨大的、陌生的阴影——字母“A”的阴影。
事实如此,何不坦言?
我后来明白,进入任何一个知识领域之前,首先都需要艰难地承认自身的匮乏。
“明天见。”Lacan 说。
“我不能。”
他挑了挑眉头。
“可我没钱了。”我补充道。
“那明天见。”他重复一遍,同时为我打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