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书案上有一方砚台,是父亲传给我的。父亲是位地地道道的农民。高小毕业,会写毛笔字,每年春节前,他都会为三里五庄的乡邻们写春联,所以父亲在我们当地小有名气。记忆中,父亲的砚台总是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那是一方黄石砚,出自家乡的黄石山。砚台有个小墨池,墨池里常常积着厚厚的墨垢,边缘处磨得发亮。每天清晨,我还在睡梦中,就能听见父亲研墨的声音,沙沙的,像春蚕啃食桑叶。
父亲研墨时总是微微低着头,花白的头发在晨光中泛着银光。他的动作很轻,仿佛是怕惊扰了砚台里沉睡的墨魂。醒来的我常常躲在门后偷看,看他如何将一支秃笔在砚台上轻轻舔过,如何在纸上落下第一个字。那时的我总觉得,父亲写字时的神情,像是在和某个看不见的人交流。
“玉杰,来。”父亲偶尔会叫我过去。我便踮着脚尖,凑到他身边。他粗糙的大手包裹着我的小手,教我握笔的姿势。“写字要像做人一样,横平竖直,堂堂正正。”他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刚过五岁,我就成了父亲写春联的助手。父亲在书桌前从早到晚不厌其烦地写着,我站在对面拉着纸,静静地看着不知疲倦的父亲和那方砚台。
记得十岁那年,我偷偷把父亲的砚台拿去学校。同学们好奇地围观,我掂起砚台不停地炫耀,谁知一不小心,砚台掉在地上,被磕掉了一个角。我吓得不敢回家,躲在村口的麦秸垛后面。天快黑时,父亲找到了我。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轻拍了拍我身上的草屑,牵着我的手往家走。
月光下,我偷偷看着父亲的背影,突然发现他的头发比以往稀疏了不少。后来我到离家二十里外的高中读书,每月回家,总能在堂屋的八仙桌上看到那方缺角的砚台。父亲依然每天写字,只是动作越来越迟缓。
有时我站在旁边,看着他写字时颤抖的手腕,看着他因为眼睛老花而不得不将纸拿得很远的样子,内心总是隐隐作痛。我劝他别写了,可他抬头朝我笑笑,仍继续写,仿佛要将一生的故事都写进这些字里。
上高一时,我的母亲不幸去世,父亲后来一直孤身30多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父亲学会了拉胡琴,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小公园里与朋友唱和。他在自行车的后座外侧挂了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一个小马扎和那方被包裹着的砚台。“爹说要将那方砚台传给你,所以后来一直带在身边,怕弄坏了弄丢了。”哥哥告诉我。
2014年3月30日,我的个人书法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父亲当时病重,没能来参加开幕式,但我知道,他肯定躺在老家的病床上牵挂着。20天后,父亲突发急病,当我从千里之外匆忙赶回老家时,父亲已经走了。哥哥说父亲临终前想亲手将那方砚台交给我。整理父亲的遗物时,我在他床下发现了一沓发黄的手札和一摞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诗词格律和名言警句。
“写书法要懂国学,会诗词是基本功。”那些字符从一开始的工整有力,到后来的歪歪扭扭,记录着父亲日渐衰弱的身体,也记录着一个父亲对儿子最深沉的思念与期待。弹指一挥间,匆匆逾十年。现在,那方缺角的砚台从老家搬到了我的书案上。每当夜深人静,我研墨写字时,仿佛能听见父亲的声音在耳边回响,“写字要像做人一样,横平竖直,堂堂正正。”
窗外的月光洒在砚台上,那个缺角处泛着温润的光。恍惚间,我仿佛又看到父亲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微微低着头,专注研墨的样子。我明白,父亲留给我的不仅是一方砚台,更是一生的教诲与牵挂。那些他写下的诗词警句,那些他教给我的道理,早已融入我的血脉,伴我从警近三十年。
去年12月,我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二次书法展,开幕式上我含泪感谢了父亲。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父亲写字时执着的神态,那是在和心中的书圣对话。正如我为此次书法展创作的主题曲《你看着我的眼》歌词中所写的那样:天地之间一根线,点与点紧紧相连,摇曳生姿,亦浓亦淡,方寸之间让生命一眼千年。
古往今来万千面,黑与白忽隐忽现,扑面而来,亦迷亦幻,心连心将情感之火点燃……如今,父亲虽然离开了,但砚台我仍在用,给群众写春联、为英雄写赞歌,墨池里的色彩依然,紫色泛黛。
方玉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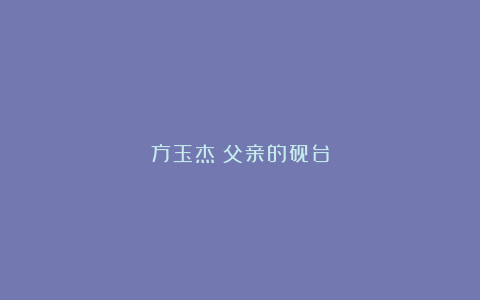
全国首届书法专业艺术硕士( MFA ),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职业道德与行风建设委员会委员、全国公安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书法展览并获奖,多次担任全国书法展赛评委、监委,出版《中国书法丛论》《历代书法经典:张旭、怀素》《致敬警嫂》等著作,在中国美术馆等地多次举办个人书法展。书法作品被中央档案馆、中国美术馆、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单位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