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教中南十二年
范忠信
(一)
中南政法是国内法学教育重镇之一,我与她的缘分始于她复校前后。1984年春节过后某一天,西南政法学院原副院长、刚出任中南政法复建筹备组长的王嘉惠老师来到我们314宿舍斜对门的80级年级办公室,跟年级办廖国钧、赵一兵、庞宗华等老师们一起,言辞恳切地动员我们应届毕业生加盟中南政法。报考政法大学研究生刚笔试完等候结果的我只能默默将到中南当作备选项,同届同学屈刚、刘黎明、周嘉玲、徐桂菊、熊正刚、张远煌、匡萍他们则由此情定中南。据说那时中南政法学院还在图纸上,司法部领导在武昌南湖边茶山刘村地界“画了一个圈”还没多久。此前一年多,78级齐文远、刘迪,79级江山、孟令智等学长已加盟中南,正在“学大寨”般做重建工作。85年暑假自京回乡途径武汉时,我曾到设在丁字桥“三招”的中南教工宿舍访晤江山师兄,也曾造访广埠屯假肢厂的中南教工宿舍。所见所闻尽是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栉风沐雨故事,那就是中南政法给我的最早印象。
1986年10月,怀揣着司法部给的两百元毕业论文调研费,我从北京南下武汉、广州、深圳,假调研之名旅游并找工作。10月31日下午,经鲁巷坐59路公汽到了遥远的茶山刘,我首次踏进总共不过七八栋楼、站大门口南望一览无遗的中南校园。在新建的塔楼教工宿舍访晤屈刚、黄茜夫妇并享用他们的厨艺后,又参观了江山的书房,还在行政主楼一楼与刘黎明、周嘉玲叙谈良久。由此对中南工作条件环境有所了解,因而打算求职中南。11月7日,自深圳、广州考察归来再经武汉,次日上午我到紫阳路中南财大教工宿舍拜访张梦梅先生,持张晋藩先生推荐信觍颜自荐。后因中南无法保证较短时间帮我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只好悻悻放弃。
大约同时,研究生同窗徐国栋兄毕业获中南教职又考上社科院博士生,中南为挽留人才主动承担“委托培养”费用,条件是国栋毕业后必须回校工作。中南这份惜才之忱让人颇有好感。87至92年在社科院工作期间,国栋兄又多次从北京东郊西八间房或武汉茶山刘村来西郊机场北边门二号看我,跟我聊及中南政法的更多创业故事,特别是中南给他的礼遇和待遇,不免引我羡慕。但因相信国栋兄受礼遇主要是因有博士帽,所以没有博士学位的我暂不敢再问津中南了。
1998年夏人民大学博士毕业前夕,我加盟中南事再次提起。起初,因李龙先生力荐,王明元先生力邀,我正拟到武汉大学工作,已提交成果材料并经武大特聘委员会审定具聘任正高资格。时在中央党校进修的中南政法学院新任院长吴汉东兄,大约从舒国滢兄处听说此事,6月2日打电话邀我到中央党校,在校门口某餐馆请客(陈小君、曹义孙亦在场),告知已成功延揽童之伟兄加盟,又说还有一位长辈法理名家即将加盟,诚邀我选择中南共图大业。在他的安排下,6月8日我(韩国同学李井杓同行)专程到中南考察,李汉昌、覃有土、萧伯符、童之伟、陈小君、齐文远、刘茂林诸师友都被安排出来参与集体邀劝。这阵仗,对一个不满四十没见过大场面的小教员而言,实在有些受宠若惊。6月10日,汉昌、茂林还专门安排外事办范敏和吕品购买了鲜花水果,由吕品陪我到武汉大学向王明元书记等说明情况并郑重道歉,如此虑事细微、关怀备至十分难得。此后四五个月间,汉东兄几乎每月给我打电话两三次,暑假回乡他竟电话追寻到英山,细述中南发展蓝图以显恳邀之意,并告以中南住房更大更利迎养父母,我深为感动。我与汉东兄,此前仅互知其名,素未谋面。作为知名学者,作为年长八岁之兄侪,又以校长日理百机之身,汉东兄不惮烦累恳切邀聘,比之古时伯乐明公未遑多让,使我顿生士遇知己之感。
(二)
自1998年8月25日至11月3日,近三个月间我和妻子在苏州、武汉、北京三地间来回穿梭,办理调动、毕业、搬家一系列繁琐手续,忙得天旋地转。这一期间,汉东兄三天两头过问,副院长李汉昌兄亲任“接待员”。他先安排我和儿子(其时妻子暂留苏州办手续)于“外招”客房暂住,一个月后又安排到47-15-102过渡居住,后来又安排我们正式入住52-101(两年后又入住号称“小中南海”的21栋)。其间各种部门手续繁琐不堪,清理、装修、搬家烦累异常,都是汉昌兄亲自安排督促完成的,汉东兄也常向汉昌电话追问进展。搬进47栋暂住时,因我不欲购置简易家具,汉昌兄亲自帮我到校产科办理学校公用桌椅、床柜、书架借用手续,还亲蹬三轮车帮我搬运家具,帮我扛背家具进屋安放,若陌生人定会以为他是搬家工。至于安排校工会吴振华主席陪我到华工附中办理儿子入学手续,安排人事处和保卫处干部陪我到省人事厅和洪山公安分局办户口迁入手续,安排我特急加入中南98年度职称评审流程,安排我的韩国同学李井杓(外专)君职岗聘任,落实我中学老师之子录取中南本科事,都是汉昌兄亲自安排甚或汉东兄亲自督办的结果。10月5日中秋节夜晚,汉昌兄亲送月饼到外招与我父子共赏圆月;入住47栋临时房时,汉昌兄、伯符兄、黎明兄分别从各自家里拿来煤气罐、煤气灶、水桶、菜刀、菜板、碗筷、炒锅、杯盘、脸盆、枕头、被套、床单等,共同倾力帮我父子搭起了一个温馨的临时简易居家。整个9月,因为我们三地奔波无暇照顾儿子,国栋兄夫妇主动担负起我儿子“代理双亲”之责,管吃住照料并检查作业,其子铁英与我儿依畴同床起居携手上学。
2001年8月5日,范忠信携子依畴在杨景凡先生寓所与俞荣根老师、喻玲师母合影。此照体现了中国法律史学人四代传承关系。
其间感人事情很多,有件记忆特别深。因我人不在汉,时任校办主任的萧伯符兄曾亲自带车带人到武昌北站帮我签字领回从北京托运过来的一整集装箱书籍,直接充任搬运工帮我扛几十箱书。其间因火车站说领取托运书籍须出具新闻出版局的认定证明(证明这批书不是非法出版物),经萧兄又三番五次交涉或恳求,最后勉强获准以中南政法学院官方证明替代。这批书籍运至中南校园后先临时存放于60栋的2-101室,不料因大雨渗水打湿了底层书箱,伯符兄又亲率校办临时工小范及几个研究生帮我将全部书籍搬到百米外的外招二楼圆形会议厅,打开所有包装将上千本书一一摊开在几十张课桌上晾干。路过外招的张继成兄有点好奇,以为是谁要做贩旧书生意,问知原委后欣然加入搬书劳动。我从苏州回来后听人说起这一切,感动得差点落泪。至于那段时间特别温馨的饭局连续不断,我和家人被汉东、汉昌、国栋、之伟、小君、茂林、伯符、文远、黎明等同仁轮流坐庄宴请(国栋、之伟为设家宴专门坐公汽几十公里到汉口买烧鸡等),几十天内隔三差五(有时甚至天天)觥筹交错、微醺微醉、欢声笑语,使我大有从苏州软语呢喃之乡初进水泊梁山聚义厅天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快感。
我花较大篇幅细述初入中南前后的亲历和感觉,当然不止是人之将老其言也烦,而是出于两个特别理由。其一,当年正是这种聚义厅氛围或语境吸引我投身中南,初入之时大有相聚恨晚之感。这种感觉使我连续十年里倾心倾力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虽苦累非凡全无怨悔。其二,二十年过后特别是离别中南八年过后记得最清楚的仍是这种氛围和感觉,格外珍惜。这种氛围感觉,这种公义私谊的特别存续方式,当时没特别当回事,今天看来实乃稀罕之物。一个重情重义的古式书生,比别的人更加珍惜这种氛围。今日翻开日记,往事历历在目,多少有些凄然。2010年秋,正因为感到那种氛围已显著淡化,我才艰难选择了离开。此乃后话,暂且不表。
(三)
我在中南期间的教学,就老实教书而已,没什么明显业绩。十二年间没有申报过一次教学成果奖,也没有承担过一个教学研究课题,也没有参加一次教学竞赛,所以连总结教学业绩的指标都没有。
我十二年中南教学生涯,分本科生、研究生、对外教学三个部分来回忆。
本科生教学,自1998年秋入校至2010年春夏,我一直给本科生授课。98年秋最初课堂是武乾师弟临时让给我的,因评职称需要课时。在这个课堂上,我和武乾曾安排97级法史研究生登台试讲,四五个研究生每人讲二至四节课,此乃模仿我的母校政法大学,作为研究生教学实习。1999年3月起,我给法学三个系本科生开讲台港澳法概论,是选修课,在北教楼403阶梯教室,选课者110人左右。2000年10月27日开始,我又从武乾手里接过99级本科课堂,学生有250多人,讲授中国法制史,在文潭楼一楼阶梯大教室(后来在我建议下命名为“邓析堂”),这是我讲中法史的最早课堂。此后每学年都要给本科生开设中法史必修课,或者开设中西法律文化比较选修课,选课生常达三百人(有人告诉我有时曾达五六百人)。因教室规模限制及课时平衡考量,教务处限定每个课堂不得超过二百人,但因为有补考生加入而每每超过几十人。在授课中,有两件事值得特别重温。
第一是查收批注学生课堂笔记。在授课中,我特别要求学生在笔记本页边批注“联想和质疑”。我要求学生将笔记本页面折叠,留出三分之一,专用来批注听课时的联想和质疑。为了检查效果,我经常不定期收取全体同学笔记本,加以批阅。每个课堂,收笔记两次,每次收到两百多本,好几大袋子,学生帮我扛回办公室,我花一周零星时间批阅,下次上课发还。几乎每本笔记都留下了我的批语和评分。一学期下来,在笔记本上批注意见五百条(次)左右,听说还有一些同学至今仍保留着我的批注。查收笔记,一来为了逼学生认真听课,防止课堂走神;二来为了培养学生质疑批判精神,养成良好思考习惯和思辨能力;三来是为了教学相长,从学生的联想或质疑中,我常常获得很多启发。此外还有查“到课率”的考量,因为常常猝不及防地收回笔记本,内容有没有记到当堂课一看便知,使谁想代交或代记几乎不可能。这点小伎俩,我曾沾沾自喜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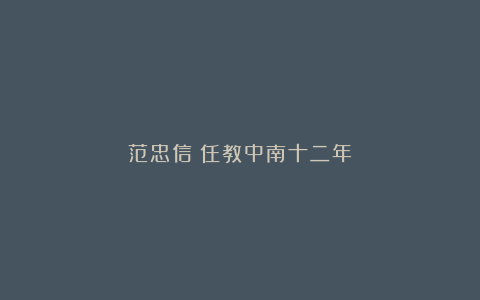
第二是鼓励学生就历史与现实关联撰文思考。在授课中,每个课堂,我都要以“我们身边的法律传统”、“古时恶法的产生存续理由是什么”、“同样问题中西为何制法不同”、“同一问题今法对于古法最关键变了什么”等为题,要求每个同学交小论文一两篇。这些论文,与课堂笔记查阅结果一起,成为评定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每学期评阅这类小论文二至四百篇,虽累有乐。记得2001年11月到2002年6月,在课外小论文考查基础上,我主持发起了“我们生活中的中华法律传统”征文竞赛,收到论文三百多篇,评出一二三等奖论文五十多篇。吴丹红、尤陈俊、陈俊涛、吴玲等四人获一等奖,周林飞、李宗辉、宋东来、蔡东丽等十三人获二等奖,陈升华、罗媛、刘永、戴建华等三十五人获三等奖。6月3日于邓析堂举行颁奖典礼,吴汉东校长、陈小君副校长及法学院齐文远院长、萧伯符书记等出席助势,他们与我和陈景良兄一起为学生颁发奖证奖金,并致辞勉励,场面感人。《中西法律传统》第二卷(法大出版社2002年10月版)曾报道此事。
研究生教学,我最早授课,是为97级研究生汪庆红、黄德新、李济涛、张丽霞、李夏珩、邹道军等讲授中国法律思想史。此后每学年,我都要给法史和法理研究生讲中国法律思想史,或中西法律文化比较,或中国行政法制史,或法律史史料学,每学期讲一二门课。此外,00年上半年开始,法理学科点负责人童之伟兄还安排我给法理研究生讲西方法理学,大约为两届学生讲过。后一届有陈柏峰、陈云中等同学。在研究生课堂上,我常组织课堂讨论或专题试讲,汪庆红、李济涛、尤陈俊、何鹏、汪雄涛、翟文喆、崔兰琴、陈柏峰、李栋、张锋、时亮、陈兵、吴欢等同学在其时展现了相当的理论兴趣、思辨能力和表达能力。此间先后常与我商量论文选题或征求论文修改意见的有尤陈俊、翟文喆、陈柏峰、侯猛、王亦白、罗鑫、吴欢、徐会超、孙晋坤、张福坤等同学。还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初,我还组织2002级研究生八人到我小学时的母校与小学生们“结对帮扶”,安排每人给一个班讲一堂课。那应算是研究生社会实践的形式之一。
从2004年开始,中南法史开始了博士招生教学。2004年至2010年的七年间,我先后招收了陈会林、黄东海、张国安、易江波、李可、罗鑫、刘华政、乔飞、李永伟、龚先砦、黄晓平、范晓东、汤建华、李志明、陈敬涛、陈秀平、阿荣等十七名博士生。博士生们与我,实际上是“互相教学”。在授课、合作课题或论文写作磋商中,我鼓励他们解放思想、革新思维,不受传统法史选题及话语格局限制,没有将他们引入死胡同。他们以各类民间社会的纠纷解决模式、传统国宪制度或惯例、家法人模式和制度等为博士论文选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在指导过程中,他们教给我的不一定比我教给他们的少。为配合博士生、硕士生教学,我们发起了“洪范学术论坛”,博士生们是这个论坛的主力。每期一人主讲,二三人辅讲,老师即席评议。这一论坛据说现在已经办到五十多期了,效果极好。与此相关,在曾宪义先生的支持下,我们发起组织“法律文化全国博士论坛”,2007年第一届即在中南举行,全国各地博士生及导师们数十人,还有本校研究生共近百人与会讨论,这成为博士生教学的最佳模式之一。十年过后,2017年的第十届博士论坛,又回到中南举办(景良兄主持),亦为历史佳话。以中南法史博士硕士生论文为基础的“历史的法学”文丛,由我和景良兄主编,在李传敢兄、张越兄协助下,自2009开始由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出版十种(本)。以学术丛书方式单独保存并展示一个学科点的博士培养成果,在国内各大法史学科阵地中应该是第一家。
我的中南教学生涯,特别值得回忆的,还有对外教学。所谓对外教学,是指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之外的教学活动,主要有三者。一是法官培训班,由最高法院和福特基金会安排,由中南政法承办,对南方各省法官进行系列培训,为期八年左右。从98年秋冬起,我为这个系列培训班讲授过好几年课程,讲题包括法治与德治的关系、两岸法律冲突与司法协助、权利理论与人权保障等问题,为备课我逼着自己恶补了一些知识,受益不浅。这个系列培训先后邀请校外法学名家多人来校,除给法官班授课外,每次还给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做学术讲座。每逢此际,南湖校区进入学术嘉年华,讲座现场人满为患,盛况空前。不止是座无虚席,常常是足无虚位。二是在各地举办的法律硕士课程班。00至05年间,我先后在武汉、长沙、广州、佛山、信阳、南昌、西安、黄石、恩施等地为课程班讲授中国法制史,因而从政法实务界一些同仁那里获得了很多教益。三是在省湖北政法委、法学会的安排下为全省多个市县党政干部做“双百”学术讲座,先后主讲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西法制理念比较、基层自治和纠纷解决等专题,与各地干部有一些切磋,这也应算是一种校外教学活动,我对中国法律实务的认识也由此有所加深。
2009年,范忠信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讲《中西法律文化的十大相通》。
(四)
任教中南十二年,“学科建设”是一种最特别的经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关于各种学位授权点、重点学科、重点团队、重点平台、研究基地、培养基地、试验区、实验室之类名目的申报、竞争、评选、检查验收,成了高校建设的重中之重,被称之为“学科建设”,犹如企业界部优国优、金奖银奖、免检产品、国家品牌、老字号、文明企业竞牌运作一般。我的大学教育生涯自始就与这事儿联系在一起。1994年,在苏大的时候,我就参加了杨海坤先生主持的宪法行政法硕士点申报,并一举成功。1997年秋,我又参加了杨老师主持的宪法行政法博士点申报,协助填表并参与游说,又取得成功。
拉我加盟中南,就是当时中南申博布局之一。因为从前中南法史学术力量较强,1983年就建成了法制史硕士点,游绍尹、章若龙、张梦梅、吴传太、杨堪等先生在全国均有相当学术影响,这都是申博的基础。但1996年前后,因老先生们全部退休,法律史学科连个正高都没有,硕士点一度停办,要申博绝非易事。我一到岗,汉东兄就跟我说,要建博士点,必须到校外挖人才,于是我们同时想到了景良兄。98年底我们就开始电话联络景良,99年2月至5月间专邀景良兄来汉考察数次,99年6月26日-28日汉昌兄和我专程到河南大学商谈景良兄转会事。在景良兄实际到岗中南工作半年后,2001年1月16至18日(农历腊月廿二至廿五),汉昌、小君两位副校长和我一起,三人驱车专往河南大学,向河大领导商量恳请放行景良的户口和关系事。景良来汉后,因为梯队仍不完整,我们先是加盟方世荣、童之伟、刘茂林兄主持宪法行政法团队申报博士点,可惜未获成功。后来,我跟景良兄商量必须进一步引进人才,争取法律史独立申报。于是,景良兄推荐了山东师大的程汉大教授,他说程老师人品和学问均为上品。尽管从前素不相识,但首次贸然电话相邀,一见(谈)如故。与景良兄联名上书校长获有力支持后,2001年11月5日学校派人事处副处长袁翠凤与我同飞济南,与山东师大历史系和学校有关领导商谈。起初很不顺利,后经反复诚恳沟通协商,终于在2002年1月办完汉大兄正式加盟手续。当年秋,法律史学科正式向国务院学位办提出申请,景良兄、汉大兄和我分别成为中国法律传统、西方法律传统、中西法律文化比较三个方向的学科带头人。本来应在03年夏完成的评审,因抗“非典”拖至年底才完成。结果还不错,我们法律史学科,与宪法行政法学科一起,同时申报成功。这是中南法学学科建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其重要性仅次于00年民商法博士点申报成功。当时,全国法史博士点仅五六家,更没有一级博士点一说。同年,法律史学科入选湖北省重点学科,为全校最早入选省重点的三个学科之一。2004年以民商法、法律史、宪法行政法三个博士点为基础,经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中南建成了法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及博士后流动站;次年又建成了知识产权国家人文社科基地,再过一年又建成了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这些在当时都是全国不到十家大学才有的资格或殊荣。那几年,在汉东兄的宏观安排下,中南法学学科建设取得了空前的成绩。
就官方指标而言,中南法律史学科那几年是有成绩的。这些成绩,除了三位学科带头人的努力,也与郑祝君、萧伯符、武乾、李艳华、春杨、屈永华、滕毅、李培峰、孙丽娟等同仁的积极参与襄助分不开。这一期间,形式要件的建设很多,如2000年创办法律史研究所,2001年创办《中西法律传统》年刊,2001年创办“法律史学术网”,2006年创办湖北省法律文化研究会,2007年创办法律文化研究院,2007年建成中国法制史省级精品课程,2008年创办“中国法制史教学网”,2009年建成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并申报省级优秀团队,2010年建成中国法制史国家级精品课程,这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郑祝君、李艳华两位同仁积极支持配合我的硕士点管理和博士点申报方案并动员教研室全体积极配合硕士点博士点事务,武乾师弟在研究院建设上事无巨细倾力亲为任劳任怨,还有培峰、会林、李栋三位学术新进在网站年刊编辑、各类评审表格填报、多次办会劳务上付出的辛勤劳动等等,对共同事业贡献不小。关于此间中南法史学科建设的前期历程,赵凌云兄主编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科学术发展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9月版)有详细记载。
因为有了这些牌子、帽子或指标,中南法史在江湖上有了名次。在2005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中,中南的法律史学科名列全国第五;在中国管理科学院2006年发布的全国研究生院评价报告中,中南法律史学科名列全国第四。作为一个已调离多年者,再絮絮叨叨回忆这些,心情是复杂的。幸而校庆筹备团队来函中明确要求我谈谈“我与中南学科发展”之事,要不然都忘记了。那些年,主要精力的确大多花在“学科建设”的无休止的填表、申报、迎评之上,要是不背明确安排谈一谈,我简直就不知道“时间去哪儿了”。人走了还谈这些,也许有朋友会问,既然引为自豪,那么何必调离?我的回答是,并没有怎么引为自豪,不过是为服务学校大局、自证“有为有位”不得不然。如果有一种不争这些形式要件,仅仅凭着个人讲课内容新颖、深刻、生动活泼、个性突出,以及学术论文写作全无禁区并且展现独立人格、科学精神、自由思想就能被视为“有成就或贡献”的正式氛围和机制,谁还愿意去整天做“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建设”工作呢?说实话,那种建设工作,就如有好多个“公公”“婆婆”“丈夫”在盯着一个新媳妇儿,他们整天要求媳妇儿在身材、体重、三围、ABC罩、发型、描眉、粉黛、口红、睫毛、服饰、香水味,甚至坐姿是否端正、举止是否轻浮、微笑是否露齿、嗓门是否粗细适当等等方面都要符合“公颁标准”、“婆颁标准”、“夫颁标准”(可怕的是他们的标准各异,且随时变化),要求媳妇儿天天仰人鼻息地悉心打扮(“迎评促建”)。这种评价模式,简直是一种梦魇。在那种机制下,还有“自然美丽”和“自然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精神、科学精神)可存吗?在那些年,几乎天天都有填表申报、求助拜票、迎接检查评估的紧迫事情要做,没完没了。每当刚评上一个,还没等你自豪并喘息几天,下一个评选又来了。刚评上了二级学位点,又马上要你去竞争一级学位点;刚评上了重点学科,马上又要你去竞争创新学科或特色学科;刚评上了重点基地,又要你去竞争重点实验区;刚评上精品课程,又要你去竞争特色课程或网络优质课程;刚评上重点平台团队,又马上要你去竞争卓越人才基地或双一流……,总之让老师们(特别是学科带头人们)整天穷于应付、疲于奔命。新名目出来,旧有名目很快淡化或作废;若不参与新竞争,你就连“成绩”“贡献”标志都没有了,也没有新学术资源的分配资格了,于是你只能无休止地参与这种竞争。因为对这种无休止竞争感到困倦,我选择了离开。来杭州这些年轻松了许多,种豆得豆、求仁得仁;临近退休,寄情山水,也算适得其所。
(五)
约稿函还要求我讲讲“对中南未来发展的期待”,有点不好谈。如果一定要说几句,那么将本文前几部分未及引申的企图引申出来,或许能表达我的期待。其实也就不过是下列三点希望。
第一是兄弟式、胞谊式学术江湖氛围很可贵,过于淡化乃至完全没有这种氛围不是好事。人从本性讲是包含江湖秉性的,谁也不愿意每日置身于谨小慎微、如履薄冰的氛围中。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淡薄尊卑,行无町畦,言无忌讳,是人际关系的好生态。大家活得惬意潇洒,而不是心机烦深,终日锱铢必较地萦回于道术,那是不利于健康的。大学多少保持一点这样的江湖氛围,减轻或降低官府行政式或豪门深宅式氛围,应该是一个集体更加健康的标志。中南未来如果能一定程度上再次形成这种人际氛围或场域,让年轻人觉得更有自在感、归属感和可信托感,实乃进一步发展之幸事。
第二是学术自主和争鸣氛围重建,真正以解放思想、质疑成说、开放争鸣、容许不同意见为大学之魂。中南以前在这方面是有优秀传统的。合校初那几年,“青年经济学论坛”(首义校区,宋清华、曾繁华、陈池波等学者主持)和“南湖法学论坛”(南湖校区,徐涤宇、高丽红等学者主持)等多个学术团队或平台,多年里他们坚持形式多样的学术活动,包括讲座、辩论、读书会、征文、课题研商、调研或实践汇报,使那几年学校的学术气氛非常活跃,成为武汉地区人气最旺的学术集市,连武大、华科、民大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也经常“赶集”般跑来“蹭讲座”,学校内外的经济学书店和法学书店常常出现学术书籍格外畅销盛况,也没有人整天“防闲”闺房般防范这些学术活动有“出轨”。我主持的科研处也尽力以校科研经费协助其活动。那时的学生以听讲座为荣,不会“抓壮丁”般拉凑听众人数。在老师们的影响下,学生社团也经常自发举行真有学术性质(而不是以娱乐或兴趣性质为主)的活动,很多学生毕业后回忆母校时都以在母校听讲座参与讨论为荣。啥时候这样的氛围重新发达起来,或比从前更加活跃了,中南就更像一所好大学了。
第三是将学科建设变成推进学术研究真正深化、学术问题真正解决的自主努力,而不是按照官定标准检查考核逼着人们应接不暇、心力交瘁的过程。这虽不是学校能单独解决的事,但学校是有一定努力空间的。简单地说,对教师个人以“三大件”(权威期刊、国家课题、国省奖项)论英雄,对团队集体以学位点、重点学科、重点基地等牌匾论英雄的评价机制,应该尽力有所改变或缓和,应该让教师们个人或集体不再受“不经常快出标志性成果就算失败”之魔咒的压迫,让教师们个人在进行学术课题研究时不必担忧考核不合格、评不上职称、职岗等级降低、滚出人才计划、丧失江河湖海山川学者名头,让学术团队进行学术合作时只考虑怎样才能真的合众力推进学术问题解决,不必整天为重点学科、优秀团队、重点基地、精品课程之类官定标准而生掰硬扯、巧妆打扮甚至弄虚作假,不必削足适履、买椟还珠地扼杀学术本真,不必蝇营狗苟地进行拜票公关,要形成一种不以牌匾或饰品论短长的氛围。要不然,长此以往坚持比级别、比数量、比科研积分式的学术考核机制和学科建设机制,多少有些逼良为娼地让我们整天沉迷于学术次品或垃圾生产而不可自拔,整天沉迷于自吹自擂的公关竞赛式学术牌匾竞逐而不可自拔,最后必然葬送学术或科学本身。
我在中南的最后几年,白天忙忙碌碌后常常静夜思考,年复一年填表申请无数,开会受动员无数,满足形式无数,迎受检查评估无数,真的一刻也没闲着,以至于身心俱疲,健康受损,似乎什么都忙了,就是没有时间真正静下心来全神贯注读几本学术名著,没有时间写一两篇真正针对前人遗留学术疑难问题或现实实践难解问题的真命题论文,甚至连真正静下心来根据最新理论进步和实践变化及时更新讲课大纲或ppt课件的时间也没有。随着老之将至,不免有些惶然。今天斗胆说出来,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为了引起“疗救的注意”。其实这种回忆也是一种个人反省。今天回过头看,因为个人修炼不到位,易于受环境和体制影响,未能真正心无旁骛地潜心于学术,以至于碌碌大半生没有什么真正成就,这是自己要负责任的,不能光赖体制。委过于人,开脱自己,君子不为。
2018年10月1日初稿
2025年2月5日改定
编辑:徐子越
审核:范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