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克栋
春生第一次见到火车时,才六岁。
那天他跟着爹去镇上换粮,远远就听见轰隆轰隆的声响,像闷雷滚过麦场。爹把肩上的布袋往地上一搁,扯着他往铁道边跑,粗糙的手掌捏得他胳膊生疼。铁轨泛着冷光,像两条永远望不到头的铁蛇,正趴在黄土地上喘气。
“来了来了!”爹的声音发颤。春生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黑烟从远处的地平线冒出来,越来越浓,带着一股煤渣味压过来。接着是巨大的铁家伙,轮子碾过铁轨的震动顺着脚底往上爬,震得他牙床发麻。车窗里晃过几张模糊的脸,有人朝他们挥着手,春生却吓得往爹身后缩——那铁家伙跑得太快了,快得像是要把这片土地都掀起来。
火车过去很久,爹还站在原地搓手。“春生你看,”他指着铁轨延伸的方向,“这铁家伙能跑千里地,能把咱这的麦子拉到天边去。”春生似懂非懂地点头,只觉得那铁轨印在地上的影子,比村口老槐树的影子还要长。
那时的黄土塬,日子像老牛拉破车,慢悠悠地晃。春生家的几亩地在塬上挂着,土是黄的,风是黄的,连人脸上的皱纹里都嵌着黄。每年开春撒下种子,就等天老爷赏雨,雨多了怕涝,雨少了怕旱,收多收少全看老天爷的脸色。娘总在灶台前念叨:“啥时候咱这地能像河边上那样,浇上水,旱涝保收,就不用求神拜佛了。”
春生十四岁那年,塬上来了一群穿蓝布褂子的人。他们背着仪器,拿着标尺,在地里插了好多小旗子。村长领着他们挨家挨户地走,说要在塬上修水渠,从三十里外的洛河引水上来。
“引水?”春生的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敲得鞋底邦邦响,“洛河在沟底,咱这塬比河高了百十米,水咋上来?莫不是哄人?”
穿蓝布褂子的年轻人听见了,蹲下来给他递了支纸烟:“大叔,咱用抽水机,一级一级往上抽,保证能浇到地里。”他说着从包里掏出张图纸,上面画着弯弯曲曲的线,像条银链子绕着黄土塬。
爹没接烟,只是一个劲地摇头。春生却凑过去看图纸,他认出那上面标着自家的地,旁边画着个小水闸。年轻人说:“等水渠修好了,你们种麦子、种棉花,啥都能浇上水,产量能翻一番。”
翻一番?春生的心猛地跳了一下。他想起去年麦收,全家起早贪黑割了三亩地,打下来的麦子还不够交公粮。要是真能翻一番,娘就不用总在夜里叹气了。
修水渠的工程开工那天,塬上像过年一样热闹。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来,履带压过土地的声音,比当年的火车还要响。春生跟着爹去工地帮忙,搬石头、挖土方,一天能挣两个工分。他看见那些蓝布褂子的人整天泡在工地上,晒得跟当地人一样黑,嗓子都喊哑了。有个戴眼镜的技术员,总蹲在渠边量来量去,眼镜片上沾着泥,他也不擦。
“小张技术员,歇会儿吧。”春生的娘给他们送水时,总会多递上一块玉米饼。小张接过去,三口两口就咽下去,抹抹嘴说:“大妈,得赶在汛期前把渠底夯实,不然水一冲就垮了。”
春生不懂什么叫汛期,但他看见小张的手磨出了血泡,缠着布条还在搬石头。夜里躺在炕上,他听见窗外的风里夹杂着机器的轰鸣,还有人喊号子的声音。那声音顺着黄土塬的沟壑传出去,像是大地在喘气。
水渠修到一半时,出了岔子。塬上的土是沙质的,挖渠时总塌方。那天春生正在渠底清土,突然听见头顶有人喊:“快跑!塌了!”他抬头一看,渠壁上的黄土正哗哗往下掉,像要把整个渠底填满。他慌忙往出口跑,刚爬上来,身后就“轰隆”一声,半面渠壁塌了下去,扬起的黄尘把太阳都遮了。
小张技术员冲过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手劲大得像铁钳:“没事吧?有没有伤着?”春生摇摇头,看着塌下去的渠壁,心里直发慌。爹跑过来,照着他后脑勺就是一巴掌:“作死啊!不知道躲远点?”
那天晚上,工地的灯亮到后半夜。春生看见小张和几个工人蹲在塌方的地方,用手刨着土,嘴里不停地说着什么。后来他才知道,他们是在研究怎么加固渠壁。第二天,来了辆卡车,拉来好多钢筋和水泥。小张说,要给渠壁打上钢筋混凝土,就像给水渠穿上铁衣裳。
水泥是个稀罕东西,摸上去凉冰冰的,掺上水就变得黏糊糊的。春生看着工人把混凝土抹在渠壁上,像给土地敷上了一层药膏。小张告诉他:“这水泥能让渠壁硬得像石头,再大的水也冲不垮。”
秋末的时候,水渠终于修通了。放水那天,全村人都跑到渠边等着。小张扳动闸门的那一刻,春生看见浑浊的河水顺着渠道流过来,像条黄龙在塬上蜿蜒。水流过的地方,干硬的土地发出“滋滋”的声响,像是在喝水。有个老人蹲在渠边,伸手掬起一捧水,眼泪“吧嗒吧嗒”掉进水里。
“活了一辈子,没想到能看见洛河水淌到塬上来。”老人抹着眼泪说。春生的娘也红了眼眶,拉着春生的手说:“以后咱家的地再也不用靠天吃饭了。”
那年冬天,春生家的地里种上了冬小麦。水渠里的水慢慢渗进土壤,冻硬的土地变得松软。春生踩着刚浇过的地,脚下的黄土不再是呛人的粉末,而是带着潮气的泥块。他想起爹说过的话,这土地就像人,得有水才能活。
转年开春,冬小麦返青的时候,塬上的景象变了。往年这个时候,地里还是一片枯黄,今年却铺着一层嫩绿色,像给黄土塬盖上了块绿毯子。春生跟着爹去地里锄草,看着麦苗一节节往上长,心里像揣着个暖炉。
麦收时,脱粒机在打麦场上转得飞快,金黄的麦粒堆成了小山。爹拿着木锨,把麦粒扬得高高的,阳光从麦粒的缝隙里漏下来,闪得人睁不开眼。“春生你看,”爹的声音里带着笑,“这一亩产了四百斤,真翻了一番!”
春生看着那些麦粒,突然想起了当年的火车。他觉得这水渠就像另一条铁轨,只不过跑在上面的不是火车,是水,是能让土地活过来的水。这水流过的声音,和火车的轰鸣一样,都是大地在响。
后来,春生娶了媳妇,生了娃。他不再像爹那样只会种地,跟着村里的人去县城学了农业技术。回来后,他在自家地里搞起了大棚,种反季节蔬菜。水渠里的水通过管道引进大棚,滴灌、喷灌,用得精打细算。
有一年,小张技术员又来了。他头发白了不少,眼镜片也厚了,但看见春生的大棚时,眼睛亮得像星星。“春生,你这搞得不错啊,比我们当年想的还周到。”
春生给小张递上一筐刚摘的西红柿,红得像玛瑙。“张叔,这都是托水渠的福。”他指着远处的水渠,现在那里已经修了观光步道,城里人来旅游,都要去看看这条“地上河”。
小张站在塬上,望着远处的洛河,又看看脚下的田野,叹了口气:“当年修渠的时候,有人说这是瞎折腾,黄土塬哪能留住水。现在看来,只要人肯下功夫,大地总会给回应的。”
春生点点头。他听见风吹过麦田的声音,沙沙沙,像在说话;听见水渠里的水潺潺流动,哗啦啦,像在唱歌;还听见远处的公路上,汽车驶过的声音,和当年的火车一样,带着这片土地往前跑。
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就是大地的回响。它告诉人们,只要你对土地好,土地就会对你好;只要你肯努力,日子就会像渠里的水,越流越旺。
春生的儿子今年六岁了,和他当年一样大。有一天,儿子指着水渠问他:“爹,这水是从哪来的?”
春生抱着儿子,指着洛河的方向:“从很远的地方来,流到咱这塬上,让咱家的地长出麦子、长出菜,让咱能吃饱饭。”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头,伸手去够渠里的水。春生抓住他的手,就像当年爹抓住他的手一样。他知道,这大地的回响,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就像这渠里的水,永远不会干涸。
傍晚的时候,夕阳把黄土塬染成了金红色。水渠里的水映着晚霞,像条铺满了宝石的带子。春生站在地头,看着自家的大棚,看着远处的村庄,心里踏实得很。他知道,这片土地还会有更多的声音响起来,那些声音里,有希望,有日子,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念想。
而这所有的声音,都是大地在回应,回应着人们的汗水,回应着人们的期盼,回应着这片土地上永不停止的生长。
春生的大棚在村里出了名,不少乡亲跑来学经验。他不藏私,把滴灌的窍门、控温的法子一股脑儿教给大家。没过两年,塬上的大棚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白花花的塑料膜在太阳底下反光,把黄土塬的一角衬得格外鲜亮。
村里的路也修宽了,能通卡车。收菜的时候,外地来的商贩直接把车开到大棚边,过秤、装车,现结钱。春生的媳妇拿着计算器,噼里啪啦算着账,脸上的笑就没断过。“当年嫁过来时,哪想过能过上这样的日子。”她给春生端来一碗凉茶,“你说,这往后还能更啥样?”
春生望着远处正在拓宽的水渠,那里来了新的施工队,说是要搞节水改造,还能用来发电。“会更好的。”他说,“大地不会亏待下力气的人。”
变故是从儿子小望上初中那年开始的。小望在县城读书,回来总说城里的新鲜事:超市里的蔬菜包装得整整齐齐,带着标签;有人用手机点点,就能买到乡下的菜。“爹,咱也开个网店呗,把咱家的西红柿、黄瓜卖到城里去。”
春生听着新鲜,却犯了难。他这辈子跟土地打交道,哪懂什么网店。“咱这菜从地里摘下来,运到城里就蔫了,咋卖?”
“可以冷链运输啊。”小望拿出手机给爹看,“你看人家这样包装,加冰袋,快递三天就到。”
春生凑过去看,屏幕上的图片花花绿绿,他看得眼晕。“这能行吗?”
“咋不行?”小望不服气,“张爷爷(当年的小张技术员,如今已是退休的老张)说,现在讲究’数字农业’,咱不能总守着老法子。”
老张确实常来村里,带着农业局的年轻人,教大家用手机看土壤湿度、测光照强度。春生学了好几次,还是记不住那些按钮。但他看着小望眼里的光,想起了自己当年看着水渠图纸时的样子——年轻人的想法,说不定就是土地明天的样子。
“行,咱试试。”春生咬了咬牙。
开网店比种大棚难多了。拍照、写介绍、跟买家聊天,春生啥都不会,全靠小望周末回家手把手教。头一个月,一单生意都没有。春生蹲在大棚边上抽烟,看着红彤彤的西红柿挂在藤上,心里发堵。“怕是真不行。”
小望却不气馁,拿着手机在村里跑,拉着其他种大棚的乡亲一起入伙。“多凑点品种,人家才愿意来买。”他还跟县城的快递点谈合作,把运费压了下来。第二个月,终于接到了第一单——上海的买家买了五斤圣女果。
打包那天,春生比收麦时还紧张。他跟着小望把圣女果一个个装进泡沫盒,放上冰袋,封得严严实实。看着快递员把盒子拿走,他心里像揣了只兔子,跳个不停。“这果子能平安到上海不?”
三天后,买家给了好评,说果子新鲜得像刚摘的。春生看着那行字,突然笑出声,笑得眼角的皱纹都挤到了一起。
生意慢慢好起来。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发两百多个包裹。春生雇了两个乡亲帮忙打包,自己则琢磨着怎么把菜种得更好。他听老张说,用有机肥种出来的菜更受欢迎,就拉着村里的养殖户,搞起了“种养循环”——猪粪、鸡粪发酵后当肥料,种出来的菜口感更清甜。
有回,一个北京的买家在网上留言:“你们的黄瓜有小时候的味道,带着土气。”春生看到“土气”两个字,非但不恼,反而觉得亲切。这土气,不就是土地的味道吗?
小望考上大学那年,选了农业工程专业。临走前,他跟春生说:“爹,等我毕业回来,咱建个智慧大棚,用电脑控制浇水施肥,让咱这的菜长得更好。”
春生送儿子到火车站,看着他背着包走进站台,突然想起自己六岁时第一次见火车的情景。当年那列火车带走的是他对远方的好奇,如今这列火车载着的,是儿子对土地的念想。
“到了学校好好学。”春生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爹在塬上等着,等你回来给这土地添点新动静。”
小望走后,春生的日子更忙了。他不仅要管着自家的大棚和网店,还成了村里的“领头人”,带着乡亲们搞起了合作社。他们统一育苗、统一施肥、统一销售,打出了“黄土塬”的品牌。有外地企业想来投资建加工厂,春生领着乡亲们去考察,一条一条看合同,生怕坏了土地的名声。
“咱这地能产好东西,靠的是实打实的力气。”他在合作社的会上说,“加工厂能建,但得保证咱的菜不变味,不能用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企业老板被他的倔劲打动,答应按照最高标准建厂房,还请了农业专家来指导。开工那天,推土机又一次开进了塬上,轰隆的声响跟当年修水渠时一样,震得春生脚底发麻。但这次,他心里踏实得很——这声音,是土地在迎接新的生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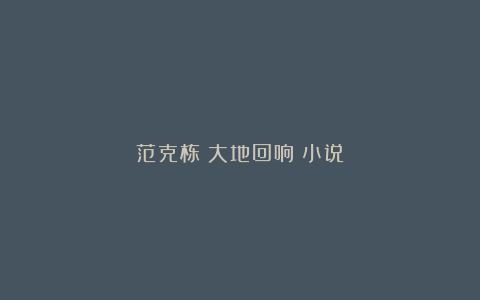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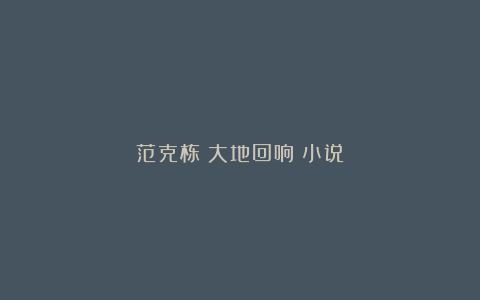
加工厂建成后,黄土塬的蔬菜有了新模样:脱水蔬菜、蔬菜脆片,装进印着“黄土塬”字样的包装袋,卖到了更远的地方。春生去县城的超市,看见货架上摆着自家种的菜,忍不住伸手摸了摸,像摸着刚从地里摘下来的一样。
老张来参观加工厂时,拄着拐杖,走得慢慢的。他看着流水线上的蔬菜被清洗、切割、烘干,感慨道:“当年修水渠,就想让大家能吃饱饭。现在啊,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好,能靠着土地发家致富,真是没想到。”
春生给老张递上一杯用自家黄瓜泡的水:“张叔,这都是您当年打下的底子。没有水渠,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老张摆摆手:“是土地本身有劲儿。你看这黄土塬,看着干巴巴的,其实底下全是宝。只要你对它用心,它就给你长东西,给你回应。”
那年秋天,塬上下了场罕见的大雨。雨下了三天三夜,春生心里揪着,怕水渠出问题,怕大棚被淹。他披着雨衣在地里转,看见水渠的堤坝被雨水冲刷着,却纹丝不动——当年打下的钢筋混凝土,真的像铁衣裳一样护住了它。大棚的排水系统也很通畅,雨水顺着管道流进蓄水池,还能用来浇地。
雨停后,太阳出来了,空气里全是泥土的腥气。春生蹲在地头,看见雨水滋润过的土壤里,冒出了新的嫩芽。他想起小时候,娘说土地像人,得有水才能活。现在他知道,土地不仅要水,还要人的心思、人的智慧,才能活得更旺。
小望放假回来,带了个女朋友,是同专业的同学。姑娘是城里长大的,第一次来黄土塬,看着漫山遍野的大棚和水渠,眼睛里满是好奇。“叔叔,这里的土地真神奇,能长出这么多东西。”
春生笑着给她摘了个圣女果:“尝尝,这是咱塬上的味道。”
姑娘咬了一口,酸甜的汁水在嘴里散开。“真好吃!”她看着小望,“我跟你说过,毕业后就来这儿,咱们一起搞智慧农业,好不好?”
小望看了看爹,春生朝他点了点头。儿子眼里的光,和他当年一样亮,和老张当年一样亮,和这片土地上所有用力生活的人一样亮。
那天晚上,春生坐在院子里,听着水渠里的水哗啦啦地流,听着远处加工厂晚班工人下班的笑声,听着风吹过大棚塑料膜的沙沙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比当年火车的轰鸣更响亮,比水渠刚通水时的流淌更绵长。
这是大地的回响,是土地对汗水的回应,对智慧的回应,对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与创造的回应。它告诉春生,告诉小望,告诉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只要根扎在土里,只要心里装着土地,日子就会像这黄土塬上的庄稼,一茬比一茬旺,一季比一季强。
春生站起身,望了望漆黑的田野。虽然看不见,但他知道,那些大棚里的蔬菜正在悄悄生长,那些埋在土里的种子正在积蓄力量,等待着下一个春天。而这片土地,会继续听着人们的脚步,回应着人们的期盼,把所有的声音都酿成丰收的歌,一年又一年,在黄土塬上久久回荡。
小望毕业那年,带着女朋友林溪回到了黄土塬。林溪是南方姑娘,细白的皮肤,说话带着吴侬软语的调子,站在黄土地上,像株刚移栽的兰草,怯生生的,却透着股韧劲。
“叔,婶,我们想试试无土栽培。”林溪把一叠图纸摊在桌上,上面画着整齐的栽培架,“不用土,用水和营养液,产量高,还干净,适合网上销售。”
春生的媳妇在灶上蒸着馒头,探出头来:“不用土?那还叫种地?”
林溪笑了,眼睛弯成月牙:“婶,还是在咱这塬上,只是换种方式。您看,这营养液里的成分,好多都是咱土地里有的,相当于给作物’定制’营养餐呢。”
小望在一旁补充:“现在都讲究绿色农业,无土栽培能精准控制病虫害,不用打那么多农药。”
春生摩挲着图纸,指腹划过那些细密的管线。他想起自己年轻时,连水渠都觉得是天方夜谭,如今要在没土的架子上种庄稼,心里又犯了嘀咕,却没像当年爹那样直接摇头。“得多少本钱?”
“我们申请了大学生创业补贴,再凑点,差不多够建个试点棚。”小望看着爹,“您要是觉得不靠谱,咱就先小范围试试。”
春生往烟锅里填了把烟,没点燃:“试。土地不就是让人试的?当年修水渠,不也是试出来的?”
试点棚建在合作社最边上,用的是新型材料,透光性更好,还装了传感器。林溪每天盯着电脑屏幕,上面跳动着湿度、温度、光照的数据,手指在键盘上敲得飞快。春生凑过去看,屏幕上的曲线像地里的田埂,弯弯曲曲,却有章法。
“这玩意能比土栽的强?”他还是不信。
“您等着看。”林溪信心满满。
第一批无土栽培的生菜成熟时,春生惊呆了。菜叶嫩得能掐出水,大小均匀,连根须都干干净净。林溪用清水冲了冲,直接递给他:“叔,尝尝,不用洗农药。”
春生咬了一口,清甜里带着点脆,比地里种的更爽口。“怪了,没沾着地,咋还有股土腥味?”
林溪笑了:“营养液里加了咱这的腐殖土提取物,特意保留的’塬上味道’。”
这“没沾土的菜”在网上火了。城里人就爱新鲜,订单像雪片似的飞来。有个美食博主专门来拍视频,镜头对着栽培架,惊叹:“黄土塬上竟然长出了’空中蔬菜’!”
春生看着打包好的生菜被装上冷链车,心里像揣了块热乎的馍。他总算明白,土地的味道,不一定非得靠根扎在土里。人把心思融进土地,哪怕隔着层架子,那味道也能透出来。
试点棚成功后,合作社扩大了规模。林溪又琢磨起“认养农业”——城里人网上下单,认养一块地或者一棚菜,他们负责种,定期发照片、视频,成熟了直接寄过去。
“就像城里人在咱这有块’远方的地’。”小望给春生解释,“他们能看着菜从种子长到成熟,吃着也踏实。”
春生觉得这主意新鲜,却也担心:“人家凭啥信咱?”
“凭咱这土地的名声。”林溪指着大棚外的牌子,“’黄土塬’三个字,就是保证。”
认养的人还真不少。有个上海的老太太,每周都要视频看她认养的西红柿,跟林溪念叨:“丫头,别浇太多水,我小时候种的西红柿,旱点才甜。”林溪就真的少浇点水,熟了摘下来,特意挑个带点沙斑的寄过去。老太太回信说:“就是这个味,跟我老家院子里的一样。”
春生听了,心里暖烘烘的。他想起娘当年总说,土地最实在,你对它啥样,它就对你啥样。现在,这实在劲儿,隔着千里地,也能传到人心坎里。
那年冬天,塬上通了高速。通车那天,春生跟着车队去了收费站。看着第一辆小轿车驶过来,栏杆抬起,他突然想起六岁时见过的那列火车。火车把土地的物产带向远方,高速路把远方的人带回土地。
“以后城里人来咱这更方便了。”小望说,“咱可以搞采摘园,搞农家乐,让他们不光能吃着咱的菜,还能踩着咱的土。”
说干就干。合作社把靠近高速口的几亩地改成采摘园,种了草莓、樱桃、小番茄。周末的时候,城里的车排着队来,大人孩子钻进棚里,摘着红的绿的果子,手上沾着汁水,笑声把棚顶都要掀起来。
有个小男孩摘了颗草莓,没洗就往嘴里塞,他妈妈想拦,春生摆摆手:“没事,咱这草莓没打药,土都是干净的。”
小男孩的妈妈笑了:“大哥,你们这地真让人放心。”
春生听了,直起腰,看着远处的黄土塬。冬天的土地光秃秃的,却藏着一股子劲,等开春一到,就会冒出新绿。他知道,这放心,是土地给的,也是一代代人用汗水攒下的。
老张去世那年,春天刚过。弥留之际,他让儿子把他送回黄土塬,说要再看看水渠。春生推着轮椅,把他带到渠边。渠水还在流,清亮亮的,映着天上的云。
“春生啊……”老张的声音很轻,“我这辈子……就干成这一件事……值了。”
春生握住他枯瘦的手,那手上的老茧,跟爹的、跟自己的,一模一样。“张叔,您干的这事,撑着咱这塬活了一辈子,还得撑下去。”
老张笑了,眼睛望着水渠尽头,像是看见了当年那些蓝布褂子的年轻人,看见了推土机扬起的黄尘,看见了水流进土地时,那“滋滋”的声响。他最后说的话,春生听得分明:“你听……大地还在响呢……”
老张葬在了水渠边,坟头朝着洛河的方向。春生在坟前种了棵柳树,说等树长大了,树荫能遮住渠水,就像当年老张他们,为这片土地遮风挡雨。
柳树发芽的时候,小望和林溪的孩子出生了,是个男孩。春生抱着大孙子,站在渠边,跟他说:“这水是从洛河来的,流到咱这塬上,养着麦子,养着菜,也养着咱一家人。”
孩子太小,啥也听不懂,只抓着春生的手指,咯咯地笑。春生看着他眉眼间像极了小望,像极了年轻时的自己,突然觉得,这笑声,也是大地的回响。
又过了些年,春生老了,背驼了,走路也慢了,但每天还是要去地里转一圈。大棚换成了更智能的,能自动调节光照,手机上就能开关闸,可他还是习惯用手摸摸土壤的湿度,用鼻子闻闻空气里的土腥味。
小望成了合作社的理事长,林溪成了远近闻名的农业专家。他们带着乡亲们搞起了“农旅融合”,修了民宿,开了农产品体验馆,黄土塬成了网红打卡地。有人来拍电影,镜头里的黄土塬不再是穷山恶水,而是充满生机的希望之地。
有回,春生在体验馆里,看见个年轻姑娘正在直播,手里举着个刚摘的苹果:“家人们看,这就是黄土塬的苹果,日照足,糖分高,咬一口,全是阳光的味道!”
春生凑过去,问她:“阳光有啥味道?”
姑娘笑着说:“就是土地的味道啊,爷爷。”
春生愣了愣,也笑了。他想起老张,想起爹,想起那些修水渠的人,想起自己这一辈子。阳光的味道,土地的味道,不就是日子的味道吗?
那天傍晚,春生坐在塬上最高的土坡上,看着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远处的高速路上,车灯像流动的星星;大棚的灯光亮起来,一片一片,像是撒在地上的银河;水渠里的水,映着晚霞,依旧哗哗地流。
他听见风从沟底钻上来,带着麦苗的清香;听见采摘园里传来游客的笑声;听见加工厂里机器的嗡鸣;还听见小望和林溪在讨论新的种植技术,声音里满是干劲。
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比火车的轰鸣更磅礴,比水渠的流淌更悠长。这是黄土塬的心跳,是大地的回响。它穿过岁月,越过沟壑,告诉每一个人:土地不会老,只要有人守着它,爱着它,它就永远年轻,永远会用最丰厚的回报,回应那些深深扎根的脚步。
春生慢慢闭上眼睛,嘴角带着笑。他知道,自己也会变成这大地的一部分,像渠边的柳树,像脚下的黄土,继续听着,继续回响着,陪着这片土地,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