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墉先生之写意花鸟,笔简而意丰,墨淡而趣长。观其作,不事雕琢,仅数笔勾勒,花鸟之神韵自出,如见生机跃然纸上。昔人谓其花能疗愈,先生欣然曰:“草木有生,或绽或舒,皆含向上之意。多识草木,少扰尘俗,心自清净。”又尝作瓶花,人赞其闹,先生暗忖:“子未见其孤也。”斯言也,道尽画中三昧。
先生之“简”,非疏懒之略,乃千锤百炼之取舍。绘牡丹,不逐富贵之态,以三五笔勾瓣,中锋藏骨,侧锋含逸,墨自浓而淡,如见花风里舒展之瞬。无刻意之艳,然令人忆盛放之烈——此生命本真之姿,不媚不俗,自有昂然之气。
其画瓶花尤见功。一粗陶瓶,数笔立纸,中插三五草花,或全开,或半绽,或含苞。线似随意,暗藏节奏:长线展茎之挺,短点显叶之灵,浓墨点蕊,如生命跃动之脉。人谓其“闹”,先生独感其“孤”。盖此孤者,乃生命内省之基。瓶花之闹,是向世之姿;其孤,是向内之根。如粗陶瓶,拙然托花,实与花相倚之默伴。闹与孤共生,恰如人生:一面于群中绽放,一面于独处沉淀。
笔下雀鸟更见意趣。一麻雀,往往两笔:侧锋一抹翅羽,中锋一点脑袋,复以焦墨勾喙与爪,跃然啄食之态立现。无细描之翎,然从倾体见啄米之欢,从侧首感周遭之警。此乃生命形态之精准捕捉——不必面面俱到,得其一瞬之“气”,便握生命之魂。
“人谓吾花能疗愈。”先生此言,道破创作初心。其画中,确有安人心之力。绘兰草,数叶披拂,不着浓墨,以淡墨勾叶之柔,叶尖微垂,却带向上之弧,如经风雨而犹舒展之生命。无孤高之态,反含亲近——仿佛此兰生邻家窗台,晨带露,晚迎风,与寻常岁月相融。
此治愈之感,源于对草木之敬。先生曰:“生命之态,皆在一花一草,绽放、热烈、向上。”故其笔为译生命之器。画菊,则见经霜不凋之倔,瓣虽瘦,笔笔含骨;画竹,不刻意求疏,反令叶密,枝桠交错间,藏“咬定青山不放松”之韧;画蒲公英,一茎挑绒球,墨极淡,然令人思风过时,种子载希望远飏之轻。此等草木,未被赋多义,唯以本真之姿存在,却令观者见己:那些绽放之时,那些挣扎之瞬,那些默默向上之日。
在其画中,草木非仅景物,实乃与人心相通之知己。“多识草木少识人,常守自信清净心。”先生此言,如钥解画中“闹与孤”之秘。其瓶花,闹为世之表,孤为内之真。粗陶瓶者,隔绝外扰之象也;瓶中花,于有限空间奋力绽放,恰是“守清净心”之写照——不被外评裹挟,唯专注己之生长节奏。
其画鸟雀,常绘双鸟立枝头,背景留白,然令人感天地暖请之阔。鸟态多静,或缩颈憩,或侧耳听,于喧嚣世中,守陪伴静心之醒,于草木静默里,寻内心之序。
画荷,荷叶以大笔泼墨,浓淡交织见光影,荷花却以淡墨轻勾,瓣边微晕,如蒙薄雾。无“出淤泥而不染”之刻意,唯静开水中,与叶相依……
先生之画,终指向生活本身。不绘奇花异草,唯画寻常草木:院边野菊,窗台绿萝,瓦罐多肉,乃至路边狗尾草。此等日日相见而常被忽略之生命,在其笔下有了温度。绘其绽放,亦绘其凋零;绘其热闹,亦绘其孤独;绘其坚韧,亦绘其脆弱——正如人生,有阳光灿烂,亦有风雨兼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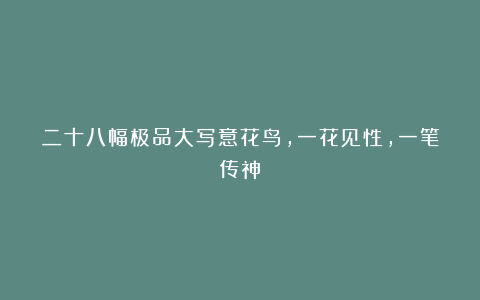
“多识草木少识人”,非真欲隔绝人际,乃警人于草木纯粹中,寻回被俗世掩盖之本心。草木从不因外评改其生长节奏:春发芽,夏开花,秋结果,冬休眠,皆顺自然,不疾不徐。此“顺”非消极之妥协,乃积极之坚守——守生命本然之貌,守内心之向。
观先生之画,常忆被忽略之日常:晨推窗,檐雀扑棱飞;午后晒阳,窗台吊兰抽新叶;傍晚散步,墙角野花正艳。此等瞬间,平凡而有力,如他之画,简笔而藏深意。于笔墨浓淡里,见者不仅是花鸟草木,更是己心之貌——那些需治愈之时,那些望清净之瞬。
合上先生画册,墨香仿佛犹在鼻尖。简笔勾勒之花鸟,早已跃出纸页,化入生活寻常景致。盖至美之艺,非高高在上之仰望,乃融入日常之陪伴——于一花一草见生命,于一笔一墨照本心,此周墉先生极简大写意花鸟最动人之处也。
画家|周墉
字號:筠溪、老溪、
筠廬半壺、九儛山人
職業畫者,獨立兿術創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