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歌德的自传《诗与真》和富兰克林自书的《富兰克林自传》中,这二位伟大的人物在叙述自己成长经历的时候,都有拔高、美化、有趣、实用和真诚的地方,而卢梭的《忏悔录》则有些自黑了,叙述梵·高的《渴望生活》则写出了梵·高的倔与痴,《乔布斯传》则延续了他的传奇,在读罗曼·罗兰的《名人传》之前,我想先看个俄国音乐家的小册子——英国音乐学家杰拉德·亚伯拉罕创作的《柴可夫斯基传》。
英国音乐家杰拉德·亚伯拉罕可是创作过音乐史的大学音乐教授,做过英国《每日电讯报》的音乐评论员,英国和音乐家的立场使《柴可夫斯基传》可读性更强,关键是较为客观些。这本字数不多的小册子没有关注柴可夫斯基的花边新闻和个人性取向,只是强调了他的音乐著作的创作过程,从一些书信上摘抄的内容也几乎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如果是想过度演绎的话,可以写写柴可夫斯基身边的3个女人——恋人黛西莉·阿尔托、妻子安东尼娅·伊凡诺夫娜、精神伴侣娜捷日达·冯·梅克,但是柴可夫斯基音乐作品的光芒已经遮住了所有的这些他人生中发生的令他伤感和不堪的事情。
对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的评价,我们就留给那些懂音乐的专业人士吧。毕竟每当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发表和演出的时候,他特别在意评论家们的意见,腼腆的他常常不敢面对。
柴可夫斯基(1840-1893)是个音乐天才,他对声音很敏感,学习音乐和语言都很快,“6岁时就能流畅地读法文和德文书籍,7岁,就可以用法文写诗。”成年后,为了读狄更斯,就学习了英语,家里没有人懂音乐,他这些爱好和灵感完全是天生的。他青少年时期师从多位老师,没有人认为他有音乐天资,在他学习赖以谋生的法律课程时,他的数学特别糟糕,哪方面也不出众。“俄国的文官中,他的工作效率是最低的一位。”这评价真是低啊!
他人生中出现了几位贵人。N·I·查良巴,这位波兰的音乐理论家将他带进了彼得堡音乐学院,院长犹太人安东·卢宾斯坦,是他少有的尊敬和佩服的人,对他的作曲学习要求的是相当地严格,他的任性几次把老师气的够呛,毕业后顺利得到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教书工作,院长尼古拉·卢宾斯坦,安东·卢宾斯坦的弟弟成为他终生的朋友。除了上课他最关心的就是自己创作的曲子能够出版、能够被选中表演、能够评论家们叫好,能够观众接受欢呼。
他身上的敏感、忧郁、多愁善感的艺术家性格非常明显。头几次担任指挥,走上指挥台前就已经紧张不已,似乎不用手托着,脑袋会掉下来。他只关心作曲,其他的事情很难上心,因此,一般都有人,特别是他的家人,陪伴他出游。他很能花钱,在梅克夫人替他偿还债务,资助他之前(梅克夫人的资助占他每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他很担心自己的生活费用,想想同时代的契科夫(1860-1904),靠白天做医生,晚上写小说挣钱,养活的是全家那大大小小的一大家子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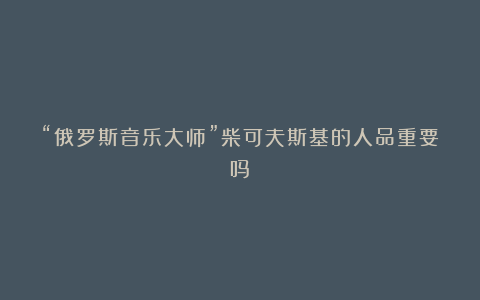
他是以作曲家巴拉基列夫为首的“强力集团”的盟友,不过有时莫名其妙地又攻击他们,为了作品获得竞赛的名次和表演的机会,他也做过手脚,贬损过其他的作曲家。他从不顾忌、张口就说谎话,又时常真诚地向别人道歉。或许他对塔涅夫、梅克夫人、巴拉基列夫说的有关《曼弗雷德》的话都是他思想的断片,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曼弗雷德(Manfred)。
他像是有劳碌命的人,有没有灵感都创作,要“像修鞋匠那样经常工作”。他始终认为:“不能像流星一样继续生活下去!”结果,他的努力和运气助他成了音乐天空中耀眼夺目的群星里的一个。
柴可夫斯基《天鹅湖组曲》
“在给朋友实际帮助方面,他是最无能的。”至于与梅克夫人的交往,从双方的通信来看,作者杰拉德·亚伯拉罕认为;“她是诚恳的,他不够十分诚恳。”对梅克夫人的断绝资助的信件中的:“不要忘记我,有时想想我”的话,柴可夫斯基非常气愤,他把梅克夫人的断资行为认为是对自己的伤害,把14年的资助认为是庸俗的,是富有的老太婆对他的耍弄,柴可夫斯基就是这样一个“心胸狭窄”的人,没有想到除了金钱,自己在精神上也非常依赖这个女人,他把别人的资助和精神陪伴当成了必须和永远,实际上光是《黑桃皇后》的版税收入就超过了那份年金,他在跟女赞助人的交往上,让读者情不自禁地会想起卢梭(1712-1778)与华伦夫人,哦!柴可夫斯基也非常喜欢阅读他的《忏悔录》,也许南非诺奖作家库切在其诺奖作品《耻》里说的对:“所有的忏悔最终都是自我辩护”。
柴可夫斯基《四季》
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是极富感情的,音色令人印象深刻,曲调优美明晰——体会一下《天鹅湖》的节奏吧,作者杰拉德·亚伯拉罕认为“隐藏在后面是作曲家自发的虚假性,他怪诞、自欺,而且自我折磨。”
但是无论如何,斯人已逝,作品永存。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