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条河,额尔古纳河,普通,又不普通。
说它普通,是因为它不是特别宽,最宽处也不足一华里;也不是特别长,全长1600公里左右;水深2-3米,掀不起惊涛骇浪,载不动万吨巨轮。
说它不普通,一是因为它是一条界河,中俄有上千公里国界以这条河划分;二是因为它的流向,它的上游自东向西流淌,中下游自南向北流淌,这在中国的万千河流中并不多见。
三是因为一本书。
一条北方隐秘的、静默的、平凡的河,因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火了一把。
2005年这本书一出版,我就读到了。当时对这条神秘的河,对这片神奇的土地感到震撼,并心生向往。
快二十年了,因为董宇辉的推介,这本书再次引起轰动。
如果你的故乡有一条河,那你就是幸运的。无论你走到哪里,那条河会始终在你的脑子里缠绕,你因此记忆会比别人丰富很多。比如我的故乡,有一条巴漏河,它全长只有一百多公里,却承载着几乎我所有的童年记忆,离开这条河,我的童年就是一片空白。
所以临河而居的人们,总是幸福而充实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人们,无论属于哪个民族,都是这样的。在这个相对广阔而富饶的流域里,生活着汉族、蒙古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不同民族的同胞,他们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和睦相处,融合发展。
蒙古帝国时代,额尔古纳河是我国的一条内陆河,《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成为中俄的界河。
《尼布楚条约》是在雅克萨之战大清胜利的情况下签订的,然而大清帝国却做出重大让步,把额尔古纳河左岸大片领土拱手让给沙俄,目的是以解当时噶尔丹占领喀尔喀之急,现在想想不禁令人扼腕!
额尔古纳河的上源是海拉尔河、呼伦湖,而它本身正是黑龙江的上源。
额尔古纳河左岸,是俄罗斯;右岸,属于我国的内蒙古自治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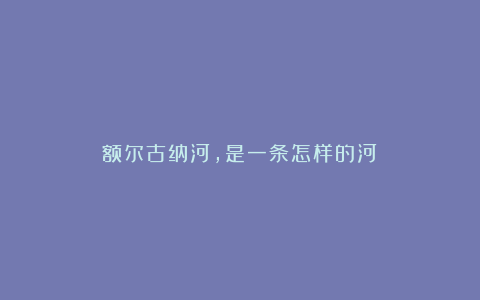
室韦、恩和是额尔古纳市的两个俄罗斯民族乡,室韦还曾被评为全国十大魅力小镇。这里的人长着欧洲面孔却能说一口地道的东北话,他们包饺子也烤列巴,人人会唱“喀秋莎”。他们住着传统的“木刻楞”木屋,保持着一些俄罗斯传统习俗,同时和汉族人融合度很高,汉语说得很好。
而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是传统的游牧民族,他们饲养驯鹿,在森林和草原上射猎,住帐篷,信奉自然主义和万物有灵观念的萨满教。
从迟子建的书中我们读到,鄂温克人绝不会亵渎自然的一草一木,他们不会在河里撒尿,不会对着火吐口水,不会对山说任何不敬的言语。
我们因《额尔古纳河右岸》而感动的,正是这种朴素的敬畏天地、山神、河神的纯自然主义观念。
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片土地,肥沃、茂盛、丰润、静谧、自由。不过这里有点偏远,再加上漫长冬季的酷寒和稀疏的居民,这里似乎与繁华、热闹、现代化缺乏缘分。
这就看你的性情了。很多人厌倦了都市的嘈杂与喧嚣,就去寻找自己的“瓦尔登湖”了,然后来到额尔古纳河右岸放逐自己。
实际上,迟子建书中所描述的鄂温克人的原始生活状态,在这里并没有完全消失。驯鹿还在,白桦林还在,苔藓还在,河神还在。飘荡在林间、河上的神秘气息还在。
至于萨满起舞的神秘向往,那是古老文化与现代灵魂的跨时空对话,每一跃一动间,都蕴含着对自然力量的崇敬与祈求;月夜下的银辉洒落,不仅照亮了大地,更照亮了人心深处的梦想与渴望,让人在无尽的遐想中,寻觅到心灵的归宿与宁静的彼岸。
额尔古纳河流域没有大城市,差不多都是县城和乡镇一级的,牙克石、呼伦贝尔、根河、额尔古纳、漠河,在中国只能算是小城市,但各具特色,旅游资源很丰富,如果不是追求热闹和繁华,不妨到这些地方走一走,感受一下北方辽阔、粗犷、静谧、安详的美。
同时,也可以领略到一丝异国情调。对面的俄罗斯村镇,视野之内一览无余。其实左岸广阔的土地,从贝加尔湖以东到整个外兴安岭,曾是我们的故土。美丽的额尔古纳河以及它所连接的更加宽广的黑龙江、乌苏里江,都曾是我们的内河。
迟子建出生在漠河,据说她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居住在漠河,寻访、读书、写作。故乡是一个作家写作最丰富的素材,甚至可以说,离开故乡这个话题,一个作家的作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贾平凹的棣花镇,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东北乡,刘震云的延津县,李娟的阿尔泰,迟子建的北极村……
我写这么散乱的一篇稿子,其实是想说:每个人心里,都应有一条自己的额尔古纳河。
额尔古纳河是一条什么样的河?
就是你心中的那条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