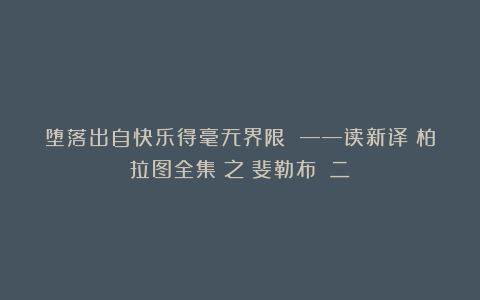|
第二阶段开始,依照苏格拉底的方法论,他们开始思想与快乐孰是孰非的论证,并对存在者存在的四种样式进行了分类。
论证要求回答的要点是:“它们每个怎么既是’一’又是’多’,且它们每个到底怎么不直接[变成]无限,而是在已经变成无限之前获得某个’数目’。”也就是要问:“快乐的样式是不是存在,而且它们有多少,且有什么属性。关于思想,也同样有这些[问题]。”
但既然要通过某种中介,好像就要找寻除了快乐与思想以外的东西。狡猾的苏格拉底就像他常常在对话的开头或结尾需要借助梦或神话来增强论证的力量一样——虽然我们明知道这些东西于论证而言毫无逻辑的、而只有修辞的价值,但因为我们就像美诺、卡利克勒斯或格劳孔那样被他电麻了,除了接受某些结论以外,根本无力提出质疑,或者宁愿那些质疑要比梦或神话更加可疑——在这里也借助一个梦作为开启论证的钥匙。
在梦里,“好像这两者[快乐与思想]都不是’本善’,而是某个其他东西,一个第三者,不同于它们,但比它们两者都更好。但如果这个[第三者]现在明显地向我们显现,那么,快乐就已经被排除在胜利之外了,因为’善’就变得不再等同于快乐了”。
本善必然是具足的。“所有认识它的东西都追求且渴望抓住它,且为了自身保持它而毫不思想其他任何东西,除了那些随着诸善一起完成的东西。”
因此,如果快乐是本善,它必定丝毫不额外需要任何东西,包括思想。但是,如果缺乏思想,我们就认识不到自己究竟欢喜或不欢喜;如果缺乏记忆,我们就不记得曾经欢喜过;如果不拥有真实的意见,就不会对欢喜发表意见,说出感受;如果没有推测能力,我们甚至没有能力推测未来会感到欢喜,“那么你就不会过着属人的生活,而是[过着]某种牡蛎或任何灵魂被关入贝壳身体里的海洋生物的[生活]”。
但我们也不会“选择过着拥有思想、本心、知识和关于整全的整全记忆[的生活]”,因为如果它就是本善,其中就既没有任何快乐,也没有任何痛苦,对所有这些东西完全无感受的生活是木头人的生活,没有人会喜欢。
上面两种生活,“既不具足,又不值得选择”,于是就剩下第三种生活,“两者(快乐与本心和思想)结合[的生活]”,“从两者的混合变成的共同[生活]”。苏格拉底说:“要是我们有人选择其他[生活],他就会是非自愿的,出于无知或某种不幸的必然,违反真正值得选择的东西的本性。”
一个合逻辑的疑问随即就要被提出:如果是混合的,快乐和思想哪个是主要的呢?“它们总有一个是原因。”
苏格拉底把本心放在第二位(第一名是二者混合的共同的生活),声称快乐“连第三名都够不上”,这让快乐主义的斐勒布和普罗塔尔科斯感到震惊和不解,仿佛遭受了某种耻辱,因为世人无一不会同意快乐的生活才是值得追求的,幸福的中心意旨莫不如此,苏格拉底偏偏要和世人作对,以哲学的名义。这也是我们痛恨哲学的原因,它说出我们不愿承认或不甚喜欢的真相。
关于“谁是第二名?”的论证紧紧围绕着那个会让斐勒布摆脱困扰的法门——“任何永远据说存在的东西都既出自一和多,又在它们自身内部具有自然的界限和无限”。这里或许是本篇对话论说的中心。
以上述法门为起点,存在者存在四种样式或种类:无限、界限、二者之混合、二者混合的原因。苏格拉底要考察它们各自到底怎么既是“一”又是“多”。
①无限
无限者就是多。“任何东西嘛,只要在我们看来能变得’更多与更少’并能接受’强烈与微弱’’过量’以及所有这类东西,所有这些东西就都必须归人’无限’的种类,就像归入’一’。”因为,当我们说更多或更热的时候,多和热永远都不存在一个确定的量,而是总要“更多”和“更热”,它们“永远前进而不等待”。这就像两个小孩子争相比较谁知道的数字最大,当一个小孩说出一个他以为的巨大数字时,另一个小孩永远只要在其上加一就实现了超越,因此他就总能说得更大。
②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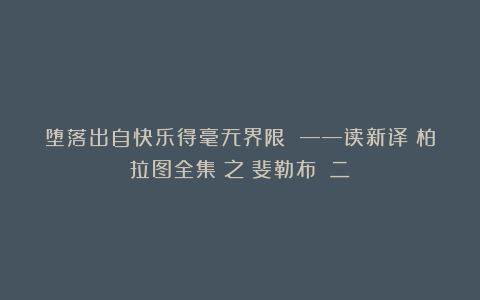
“首先[是]’相等和等式’,而在’相等’之后,[其次就是]’两倍’和所有’数目’之于’数目’或’尺度’之于’尺度’[的比例],⋯⋯”所有这些东西都可算入“界限”。
③二者之混合
无限和界限的整个生成物是“一”,二者之混合就是通过界限所要求的“尺度”从前两者进入存在的种类。正因为这种尺度,在高低快慢中合成了音乐,在无限有限的混合中产生了季节和所有美的东西,以及“灵魂里极多的其他极美的东西”。
“其实,恰恰这位女神(阿芙罗狄忒)自己,⋯⋯肯定看出狂妄和所有东西的整个堕落都出于快乐和满足而变得毫无界限,就在它们[快乐和满足]里面确立了拥有界限的’法律和秩序’。尽管你说她毁掉了她自己[快乐],但我说恰恰相反,她拯救了[她自己]。”
界限就是康德在他的哲学中百般告诫我们要遵守的东西。在理论理性那里就是先验的范畴只能运用在经验的领域,那个经验就是知识的界限。在实践理性那里就是自由同样不可认识,只可“行”出来,这个“行”就是道德的界限。界限提供的“尺度”对于无限来说,并非因此就奴役了无限,让它失却了无限的本性,相反,它让它重新焕发了生机。从前它只是“多”,如今它仿佛成了“一”。
这就像自由,作为无限的自由是“自由的任意”,它其实戕害了自由,因为任意往往带来混乱、伤害乃至毁灭,不但对他人,也对自己。而被尺度所规定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这个尺度在社会学那里就是法律,在康德那里就是纯粹理性。对于前者,有法律保障的自由才得以摆脱了丛林法则的混乱和弱肉强食,真正保障了每个人的自由,因为自由是“群己权界”,它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对于后者,自由就是意志为自己立法,而不是被欲望、情感等外在的东西所决定,一个是自律,一个是他律;这个自律就是依纯粹理性所认为的普遍有效的法则行事,唯有纯粹理性才是自由得以实现的唯一尺度。
因此就像“自由是戴着镣铐跳舞”一样,无限与界限的混合就是“无限戴着界限这个尺度跳舞”,它使这第三种形式成了最好的存在形式。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阿芙罗狄忒为什么在快乐当中确立了“法律和秩序”,苏格拉底说,她不是毁掉了、反而是拯救了快乐,因为她这样就避免了无限的快乐所可能带来的秩序的、思想的、人性的堕落。只有真正理解自由、法律、幸福这些概念之关系的人才会认同苏格拉底,这恰恰也印证了“人是城邦的动物”这句政治学的真理。
我们只要简单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就能理解其中的深意: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吹嘘自己极限穷游香港的经验。一方面寻找各种卖场的试吃摊位,在不同的时间反复前往,一方面冒充流浪汉到慈善组织那里领取免费食物,如此吃饭就不用花上一分钱。试想如果人们都如此这般,他们或许实现了极限穷游的无限快乐,但卖场的秩序和弱势群体的权益就全部失去了,它所伤害的是社会秩序,因此所引发的连锁效应最终会伤害到每个人,包括极限穷游的人。至少,香港不会欢迎不遵守秩序、侵害弱势群体利益的人,他们的所谓无限快乐从此将不会是无限的。这就像一个嗜酒如命的人,酒精和无度最终将损害他的肉体和精神,不但使他无力从酒精中获取快乐——因为肉体的器质性损害,而且让他的精神也没有能力在任何事上振作起来——因为堕落的一个特征就是将会一直下降,直到下降到毁灭的深渊。(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