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Tangle没用,注意力反而更分散,看来我不是ADHD。”
(图源网络,侵删)
这是小红书上的一句热门评论。
但我看到后,脑子里就一句话:“Tangle不是验孕棒,你不能靠它判断你是不是ADHD。”
现在是一个人人焦虑、人人“自我诊断”的年代,ADHD被塑造成了“逃离内卷”“反对职场疲劳”的精神出路,但真正的ADHD,从来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赛博确诊为何流行?
身处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我们的注意力似乎被三股力量同时撕扯:
-
多线程工作模式让大脑在任务间高速切换
-
短视频平台以15秒为单位刷新多巴胺阈值
-
慢性疲劳又持续稀释了本就稀薄的认知资源
当“注意力碎片化”成为现在大多数人的一种公共体验后,ADHD的诊断标签就不再只是临床工具,而成了一个被广泛借用的概念。
人们把“拖延、发呆、不想上班”这些日常困扰一股脑装进去,仿佛贴上标签就能获得解释与赦免。
也就是说,很多人不是在确诊ADHD,是在试图解释“我为什么不是主流成功模板”。
然而,临床意义上的ADHD是一组更复杂的神经发育特征,除了难以维持专注与冲动控制外,还包括时间管理混乱、情绪调节困难和中枢性疲劳等。
研究指出,ADHD群体的疲惫并非单纯懒散,而是与自主神经系统兴奋水平下降有关,属于“中枢性疲劳”范畴[1]。
(图源网络,侵删)
这意味着,当大众把ADHD简化为“拖延+爱发呆+不爱上班”时,既放大了诊断的娱乐化风险,也淡化了真正的ADHDer所面临的执行功能缺陷与神经化学差异。
换言之,标签带来了短暂的自我和解,却可能掩盖更深层的问题:
我们的工作环境、信息生态与休息方式正在系统性地损耗所有人的认知资源。
ADHD被娱乐化的那一刻,真正的ADHD人开始沉默了
当算法把“我是谁”拆成一连串可截图、可配乐、可二创的标签时,“ADHD”刚好满足了平台对“显性身份”的全部需求:
足够小众,又足够有梗;带点自嘲,还能引发大规模“我也是”。
过去人们羞于承认“我有病”,现在却害怕没有标签。
短短两年,小红书笔记里带#ADHD#的话题浏览量从几十万飙到5亿;抖音上关于“ADHD日常”的视频往往能够获得上万赞——镜头扫过满桌没拆封的书、三台同时播放的平板、最后定格在一张处方药盒,配文:“不是懒,是大脑开了37个后台程序。”
(图源网络,侵删)
在这种叙事里,ADHD被抽离了DSM-5里关于“功能受损”的临床标准,压缩成几组极易辨认的视觉符号:拖延、走神、冲动消费、一次性开20个浏览器标签。
Aidoo等人在2024年的一项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倾向于把心理障碍“可爱化”“浪漫化”,因为轻度化表述既降低观看者的心理门槛,也能让博主收获“脆弱性红利”[2]。
正如现如今注意力被碎片化的年代里,ADHD不是病,是一种文化现象的投影。
于是,ADHD不再是神经发育差异,而是一张自带柔光的滤镜:它让混乱显得俏皮,让迟到显得合理,让失败显得无害,真正的临床群体却在这场狂欢里被迫噤声。
早在2022年就有一项跟踪调查显示,当#ADHD话题在TikTok上暴涨时,线下门诊中自述“怀疑自己ADHD”的年轻人增加了82%,其中60%经系统评估后并不符合诊断标准;与此同时,确诊的平均等待评估的时间从3个月延长到9个月[3]。
涛哥后台也收到过这样一条私信:“当我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同事我真的有ADHD,对方回我:’哈哈,谁不是呢?’那一刻我知道,我说出口的不是病情,而是梗。”
文化理论家Lauren Berlant把这种现象称为“情感商品的扁平化”:当一种痛苦被切割成可消费的情绪碎片,它就失去了向社会结构追问的能力[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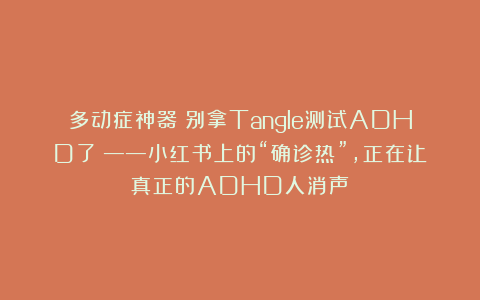
于是,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工作节奏必须依赖多线程?为什么休息也被算法切成15秒?——被轻巧地转译成一句“我大概有点ADHD”。
ADHD被娱乐化的那一刻,真正的ADHD人开始沉默了。
(图源网络,侵删)
心理困境不能靠’剁手’解决
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里,商品被赋予的不再是使用价值,而是“对问题的承诺”[5]。Tangle的流行,恰好再现了这一逻辑:
原本需要临床访谈、量表、神经心理评估才能完成的ADHD诊断,被压缩成一次“下单即治愈”的瞬时体验。
淘宝详情页用“转得越快,注意力越集中”把症状商品化,小红书博主用“转30秒不卡顿=没有ADHD”把诊断游戏化。
于是,心理困境被翻译成购物车里的SKU(stock-keeping unit,代表零售商库存中的一种商品),而平台算法则不断放大“买一个就能好”的幻觉。
然而,正如伊娃·伊鲁兹在《冷亲密》中提醒的:
“情绪的商品化并未带来真正的情感解放,反而让痛苦成为可流通的符号”。
当Tangle被包装成“测试ADHD的试纸”,它真正贩售的是一种可触、可晒、可丢弃的“疗愈感”,而非疗愈本身。
(图源网络,侵删)
这种伪疗愈的吊诡在于:
它把复杂的心理结构简化为“有没有转起来”的二元判断,再用物流包裹把焦虑暂时封存——直到下一次注意力涣散,消费者又回到同一个页面。
但是,心理困境不能靠’剁手’解决。
这句话涛哥真是深有体会,我用过最贵的“确诊工具”,是五年的人生卡顿、几百次自我怀疑。
卡顿的不是手指,而是时间;需要被诊断的不是注意力,而是被压缩到只剩KPI的人生。
涛哥说
总的来说,在现在的社交平台上,ADHD不再是一种障碍,而是一种被包装过的叙事方式。
小红书等内容平台把原本属于“神经差异”或“心理困扰”的特征,包装成了“个性标签”或“内容人设”,用于吸引注意力、获取流量和点赞,比如下面这些表达:
-
“我总是爱发呆,应该是ADHD吧~”
-
“我太讨厌上班了,社恐又拖延,是不是也算ADHD?”
-
“我不爱被管,感觉我根本适应不了职场。”
-
“我做事老跳跃、记性差、爱熬夜——ADHD没跑了!”
-
……
这些说法在平台算法下被频繁推送、点赞、转发,本质上不是为了“了解ADHD”,而是满足受众“终于有人跟我一样”的情绪共鸣,在提供一个轻松幽默的“自我认同标签”的同时形成一种“我也是特别的”的人设定位。
这让真ADHD人的混乱、崩溃、情绪暴走、羞耻、社交误解等困境反而不被看见。
ADHD从来都不应该成为网络热词,它是成千上万人真实挣扎过的路;它不是你逃离职场的出口,而是有人拼命想成为’普通人’的起点。
如果你对ADHD感兴趣,请先理解它的复杂、长期和结构性,而不是只看见它的“可爱与共鸣”。
(图源网络,侵删)
[1]Yamamoto T. (202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ntral fatigue and 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 of the inattentive type. Neurochemical research, 47(9), 2890–2898.
[2]Aidoo, E. A. K., Wood, S. F., & Mohammed, F. (2024). “Anxiety is not cute”: analysis of Twitter users’ discourses on romanticizing mental illness. BMC Psychiatry, 24, 221.
[3]Gilmore, R., Beezhold, J., Selwyn, V., Howard, R., Bartolome, I., & Henderson, N. (2022). Is TikTok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self-diagnoses of ADHD in young people? European Psychiatry, 65(S1), S571.
[4]Lauren Berlant, “Introduction: Compassion (and Withholding),” in Compassion: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an Emotion, ed. Lauren Berla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13.
[5]Baudrillard, J. (1998). 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C. Turner, Trans.). Sa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