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在镇江焦山西麓的陡峭崖壁上,一片历经江水千年冲刷的残损石刻,构成了中国书法史上最富传奇色彩、也最令人着迷的悬案——这便是被誉为“大字之祖”、“书家冠冕”的《瘗鹤铭》。它并非出自庙堂之上的帝王将相,也非书于纸绢之上的规整法帖,而是一篇为悼念死去的鹤而作的铭文,以其无与伦比的艺术感染力与身世之谜,吸引了无数文人书家为之倾倒、考证与膜拜。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瘗鹤铭》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其作者之谜。由于原文并未留下确切的纪年与署名,仅以“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等道家色彩浓厚的别号示人,千年来关于其作者的推测聚讼纷纭,成为一桩名副其实的“文字公案”。最主要的说法有以下几种:其一,六朝说,尤以梁代陶弘景所书最为后世所重。陶弘景是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医药学家,自号“华阳隐居”,其身份、行迹与文中的“华阳真逸”颇为契合,且其生活的梁代正是书法艺术自觉、楷隶交融的时期,与《瘗鹤铭》的书风时代特征相符。北宋大学士黄伯思即力主此说,论证详备,影响深远。其二,唐代说,其中以书圣王羲之或顾况所书最为动人。王羲之素有爱鹅之名,其转世为鹤、自撰铭文的故事虽属浪漫的附会,却反映了后世对其书法至高地位的认可。而唐代诗人顾况亦号“华阳真人”,使其成为另一可能的人选。其三,五代说,如南唐的王文秉等。这些争论,至今未有定论。然而,或许正是这种作者的不确定性,反而剥离了具体个人的光环,使得《瘗鹤铭》的艺术价值本身成为绝对的主角,任人沉浸于其纯粹的线条与意境之中,而不必受限于“名人效应”。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审视,《瘗鹤铭》是一部刻在摩崖上的“楷隶过渡教科书”。它的字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或者说,它是用深厚的隶书笔意来书写楷书的结体。观其用笔,圆笔藏锋,起收含蓄,线条饱满而富有篆籀气,如屋漏痕,如锥画沙,充满了内在的筋力。其结体则率真自然,因崖势而布,宽博舒放,中宫开阔,四肢伸展,仿佛不是人力刻意雕琢,而是自然生长于山石之上。章法布局更是妙趣天成,字的大小、疏密、正侧一任自然,行气连贯,如群鹤翔集,各具姿态又浑然一体。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这种艺术风格,被后世归纳为“金石气”与“逸气”的完美结合。所谓“金石气”,是指其历经风雨剥蚀所形成的苍茫、浑朴的线条质感,这不是笔墨在平滑纸绢上的流畅运行,而是凿子在粗砺岩石上的艰难推进与自然力千年打磨后的结果,一种残缺之美与永恒之力的交织。而“逸气”,则指其整体气韵中透出的超凡脱俗、逍遥物外的精神格调。它为一只鹤而作,主题本身已远离世俗功利;其书风不拘常法,天真烂漫,正合道家“法天贵真”的思想。黄庭坚对此推崇备至,其诗云“大字无过《瘗鹤铭》”,其本人雄肆开张、辐射状的书风,无疑从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瘗鹤铭》的命运与其身世一样坎坷。原石曾因雷轰崖崩而坠入江中,碎为数块,只有在冬季水枯时,才偶有残石露出水面,文人雅士方能冒险捶拓,故有“水拓本”传世,片纸千金。直至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才由镇江知府陈鹏年募工从江中捞起五块原石,移置焦山定慧寺壁间。至此,这千古瑰宝才结束了数百年的沉浮,得以重见天日。这段“水落石出”的经历,更为它增添了一层悲壮而神奇的色彩。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瘗鹤铭》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个无可替代的坐标,在于它集多重价值于一身:它是书法演变史上的活化石,见证了楷书脱胎于隶书的关键节点;它是意境美学的巅峰,将文字从实用功能提升至哲学与艺术的表达;它是一件“天工”与“人力”共同创造的艺术品,自然的风化与最初的书写共同完成了最终的杰作;它更是一个永恒的文化谜题,持续激发着后人的考据热情与审美想象。它不像庙堂碑刻那样庄严整饬,而是充满了山林野逸之气与生命的感伤。当我们站在焦山之下,凝视那些斑驳陆离的字迹时,所感受到的已不仅是一位书家的笔法技巧,而是一种穿越时空的生命咏叹——对羽化仙禽的哀悼,何尝不是对生命易逝、精神长存的沉思?这块冰冷的石头,因其文字的温度与艺术的不朽,获得了永恒的生命。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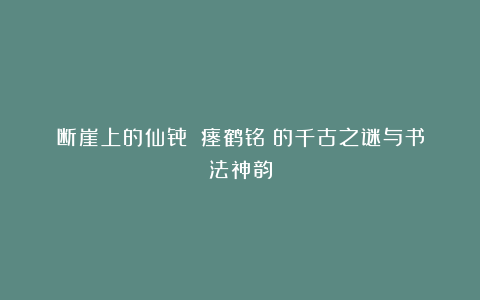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