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童谣从小听到大,可你知道吗?端午节的“身份证”至今还在“打架”。
有人说它是屈原的专属纪念日,有人却坚持它最早是为了祭祀伍子胥。
这场跨越千年的“姓氏之争”,背后藏着一部鲜活的中华文明交融史。
汨罗江边的纵身一跃
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郢都。
汨罗江边,一位身着素衣的老者将最后一口米酒洒向江面。
他是屈原,那个写下“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楚国大夫。
当《怀沙》的墨迹未干,他怀抱巨石沉入江底,溅起的水花惊醒了千年后的端午记忆。
据《史记》记载,屈原投江后,百姓们“争舸逐之”,
用竹筒装米投入江中喂鱼,这便是龙舟和粽子的雏形。
南朝《荆楚岁时记》更明确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
唐代时,竞渡之风从民间走进宫廷,
唐玄宗在《端午三殿宴群臣》中描绘的“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正是当时盛况的写照。
姑苏城下的涛神传说
在苏州胥门,每年端午都要举行一场特殊的祭祀。
人们将粽子投入胥江,船头的老者念念有词:“伍大夫,回家过节了。”
这里流传着另一个版本的起源,
春秋时期,伍子胥因忠言直谏被吴王夫差赐死,尸体装入皮革投江,这天正是五月初五。
苏州的端午习俗与别处大不同:
龙舟竞渡前要先拜伍子胥祠,粽子里要包进一枚咸蛋黄象征“子胥之目”,
连悬挂的菖蒲都要编成宝剑形状,寓意斩杀奸佞。
《清嘉录》记载,吴地百姓“以龙舟竞渡为伍子胥助威”,
这种信仰甚至影响到相邻的无锡,当地至今流传着“端午不祭屈,只念伍大夫”的说法。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独木舟和木桨。
这些远古遗物揭开了端午节更深层的密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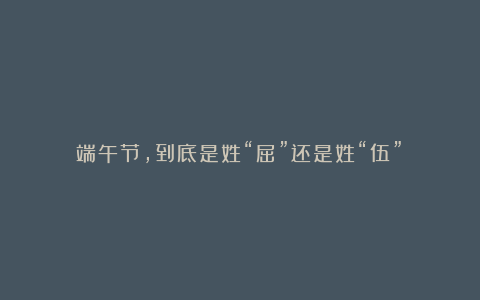
上古百越族的龙图腾崇拜。《淮南子》记载“越人便于舟”,
每年五月初五,他们会划着刻有龙纹的独木舟,将裹着树叶的饭团投入江中祭祀龙神。
这种原始信仰至今仍有遗存:
福建漳州的“旱龙舟”在陆地上模拟竞渡,
广西的“龙船歌”保留着古越语的韵律,就连粽子的锥形造型,
都与百越人祭祀用的“角黍”一脉相承。
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指出,
端午节的核心是“龙的节日”,屈原、伍子胥的传说不过是后来附着的文化层。
汉代以前,五月初五被视为“恶月恶日”。
《风俗通》记载,这天生的孩子“男害父,女害母”,
甚至“五月到官,至晚不迁”。为了辟邪,人们佩戴五色丝“长命缕”,
用兰汤沐浴,门前悬挂桃符和艾草。
这种禁忌观念在唐宋时期逐渐转变。
宋代《岁时广记》记载,端午节变成了“女儿节”,
家家户户给女孩簪上石榴花,出嫁女回娘家“躲午”。
苏州妇女还会用金银丝编织“健人”饰品,既有驱邪之意,又暗含“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
如今的端午节,早已超越了单一的起源传说。
在湖南汨罗,游客可以体验“祭屈大典”的庄严肃穆;
在苏州胥江,国际龙舟邀请赛吸引着各国健儿;而在北方,人们更注重插艾、挂钟馗像等驱邪习俗。
粽子的演变最能体现文化融合:
广东的裹蒸粽用柊叶包裹,个头堪比小枕头;嘉兴的鲜肉粽肥瘦相间,咸香入味
北京的小枣粽则延续着北方人对甜糯的偏爱。
端午节这场跨越千年的“姓氏之争”,本质上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
正如苏州端午习俗传承人所说:
“伍子胥教会我们忠勇,屈原教会我们爱国,龙舟教会我们团结,粽子教会我们分享。”
在这个粽香四溢的节日里,与其纠结“姓屈还是姓伍”,
不如剥开粽叶,品味那穿越时空的文化交融,这或许才是端午节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