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通常认为,一八七六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岛条约》,是朝鲜打开国门,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起点。作者梳理流入朝鲜的西洋布的历史后却发现,其实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洋布已广泛流通于朝鲜市场。西洋布在民间的流行,表明朝鲜已通过与清朝、日本的贸易,间接而广泛地参与了全球贸易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这为东亚地区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奠定了基础。
朝鲜半岛的西洋布与贸易全球化
一八六九年,朝鲜王宫数次出现盗窃案件。先是三月份,闵妃,即明成皇后宫中的内人盗取“蓝绵裳一,洋木青裳一,白洋木回粧赤古里二”等物,卖给了旧衣商人金化允。“蓝绵裳一”很好理解,即蓝绵衣裳一件,但“洋木”又是什么东西呢?
“洋木”即“洋布”,朝鲜语固有词称“布”为“mok”,用汉字借音标记为“木”。“洋木”“洋布”在当时都是指西洋布,所以上文中被盗物品是以西洋布制成的青裳一件,白色西洋布制成的加以其他色彩装饰的上衣两件。到了十月,又出现了大妃宫中的内人与守卫军士金尚哲合谋盗取“洋木女赤古里二,西洋纹裳一,洋木裳一”等物卖给衣廛商人李根源的事件。金尚哲等人不知收手,在十月二十日夜里潜入大妃宫中再次盗取“草绿绵回粧赤古里一,西洋木青裳一”等物品后,被其他守卫军士们抓获。被盗衣物中多次出现西洋布制成的服装,表明当时朝鲜王宫中存在为数不少的西洋织物。需要留意的是事件发生在一八六九年,距一八七六年朝鲜被迫与日本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岛条约》还有七年。通常认为该条约的签订标志朝鲜打开了国门,是朝鲜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起点,也有学者认为这是朝鲜近代史的开端。
描绘《江华岛条约》签订场景的日本画作(来源:wikipedia.org)
但从上文的盗窃事件来看,朝鲜王宫中早已充斥大量西洋布,王室成员就是西洋布的重要消费者。小偷将偷来的西洋布制品卖给民间商人,也证明朝鲜民间愿意接受这些物品,民间存在西洋布的销售渠道。可以推测,在《江华岛条约》签订之前,也就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朝鲜已然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以西洋布为代表的外国货物早已大举进入朝鲜。
这个假说是否成立呢?还得从西洋布流入朝鲜半岛的历史说起。《朝鲜王朝实录》中第一次出现有关西洋布的记录是在一四六八年。此前一年朝鲜世祖听从明朝的要求,派兵征讨建州女真,斩杀女真头领李满住等人,得到成化帝的嘉奖。《明实录》记载的赏赐物品中有“西洋布十匹”,《朝鲜王朝实录》中将此记为“白西洋布十匹”。此后的岁月里,明朝诸帝多次在册封朝鲜国王、王妃时赏赐西洋布,该习惯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前的十七世纪初期。获得明朝赏赐的朝鲜国王也会将西洋布赏给宠信的臣子,如朝鲜成宗曾在一四九三年“赐德源君曙、河城府院君郑显祖、西陵君韩致礼、领敦宁以上及六承旨、尚衣院提调各西洋布一匹”。成宗的兄长月山大君在《奉赓御制赐西洋布》诗中写道:“幸得西洋布,轻明与锦殊。眼看宣赐重,身被圣恩濡。”明朝灭亡百余年后,仍有朝鲜国王怀念与明朝亲密合作,明朝皇帝赐下西洋布等物的光辉岁月。如朝鲜纯祖(一八〇〇至一八三四年在位)的文集中收录了一篇《拟朝鲜国王谢赐彩缎白金纹锦西洋布以表平女真之功表》,文中怀念的还是成化年间的事情。
由此可知十五世纪至十七世纪前期流入朝鲜半岛的西洋布多是明朝皇帝的赏赐,数量不多,流通于朝鲜王室与贵族阶层,被认为是“圣恩”的象征。按王元林等学者的研究,该时期的西洋布应是贩自被东南亚国家称作“西洋”的印度洋一带地区的布料,由东南亚国家进贡给明朝。不过此时的西洋布只是富贵人家的猎奇之物,并未大量进入明朝的大众市场。
到了明末清初,产自欧洲的所谓“西洋布”被传教士介绍到中国。南怀仁在《西方要纪》中记录:“以利诺草为之,视绵更坚且洁。佳者一匹可十数金。所谓真西洋布是也。此布用坏又可捣烂为纸,莹洁而耐久。”一七七七年赴北京的朝鲜使臣李𡊠在《燕行记事》中记录了“西洋国”,提到该国:“以利诺草作布,则视绵更坚且洁,一疋或至十数金,此所谓西洋布。若坏弊则捣练为纸,莹洁耐久。”看起来李𡊠直接照搬了南怀仁的记录,但他不一定真见到了西洋布。一七九三年,朝鲜赍咨官洪宅福的手本记录通过义州府尹报至正祖,其中提到“咭唎国,居广东之南,为海外国”,其当年的贡品中就有“西洋布”。此处“咭唎国”大概指英国。一七九五年,朝鲜使臣记录了“距燕都九万八千里”的荷兰国的贡品,其中也有“西洋布十疋”。于是朝鲜朝廷开始意识到“西洋布”是来自这些遥远的西洋国家。
湖色印花纹洋布(光绪年间),故宫博物院藏
一八二八年赴华的朝鲜使团在使行途中见到了西洋布,按此行随员李在洽留下的《赴燕日记》的记载:“西洋木者即细绵木布也。广至二尺,价不甚高,而我东所未有者,可堪服之。”可见当时西洋布尚未在朝鲜市场流通开来。一八三二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胡夏米号”泊于朝鲜洪州附近海面,向朝鲜提出通商的要求。英国人希望可以“因公贸易设约,以洋布、大呢、羽毛绡、琉璃器、时辰表等,货买贵国金、银、铜、大黄等药材”。同时英国人还赠送了“洋布十四疋、千里镜二个、琉璃器六件”等礼物。朝鲜朝廷拒绝了通商要求,但留下了英国人赠送的礼物。
虽然英国人未能与朝鲜直接贸易,但作为西方工业制品的西洋布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迅速流通于朝鲜市场。朝鲜在商业上实施所谓的“市廛体制”,简单说来是官府在汉阳钟路一带建立市廛行廊,商人们向官府租赁行廊开设常设商铺——市廛,官府赋予这些市廛对特定商品的专卖权,但市廛需要承担向官府供应物资等义务。某种程度上来说,市廛商人是朝鲜时代的官许特权商人。但各家市廛只能销售登载在本廛市案上的商品,即在官府登记的销售目录上的商品。一八三七年,青布廛认为木廛售卖西洋布等物影响了自身利益,向官府提出“西洋布及大布三升之木廛卖买,一切禁断事也”的请求。官府认为:“西洋布、唐木既非市案现载之种,又非土产恒有之物,不须梗属一廛,只令随分互卖为宜。”也就是说西洋布与清朝布匹等新商品,此前既未登记在市案上,也不是朝鲜土产,其销售权不应属于某处市廛,各处市廛都可以自由售卖西洋布等物。这一决定史称“丁酉处决”。该决定的实施,实际上开启了西洋布得以在朝鲜市场自由售卖之路。
市场,金俊根绘
然而几处市廛仍为获得西洋布的专卖权而争诉不已。一八四三年银木廛向官府提出:“西洋木,近因木荒多有贸出者,而即是绵织,宜属矣廛。而乱卖居多,后弊无穷,自今私卖者,绳以乱廛之律事也。”进口西洋布的原因是朝鲜本土布匹供应不足,银木廛认为西洋布属于棉织品,其销售权应该属于本就销售棉织品的本廛,但现实中存在大量不遵守销售规定的“乱卖”行为,于是希望官府能以“乱廛之律”严加管制。在银木廛之外,还有帽子廛、廛也提出了类似请求,但朝鲜官府一律不予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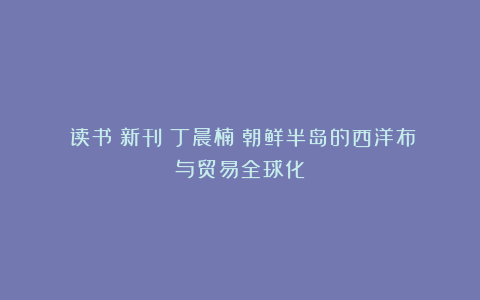
随着十八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市廛体制渐渐不能满足汉阳的物资供应需要,不属于市廛商人的私商群体开始活跃在汉阳的大街小巷之中。同时汉阳以外其他地区的商业也有较大发展,义州商人、开城商人、东莱商人等民间商人掌握了外国商品的进口权与流通渠道,逐步成为连接朝鲜外贸与内贸的大商人团体。按白木廛商人的说法:“洋木贸迁,岁加月增,闲杂之类,惟意卖买,故常产之木,市绝交易,实为失业之端。燕商贸来,一切防禁,而不然则系是绵织,即有所主,严立科条,无或更犯事也。”此处的“闲杂之类”应指私商,而掌握西洋布进口的“燕商”应该指的是多与清朝有贸易往来的义州商人、开城商人。为何朝鲜要进口如此多的西洋布?《中江税务监督晓谕誊书》提到:“查道光年间朝鲜在边门交易皆买斗文布为正款,渐有洋布无税,朝鲜商人俱置洋布,全不贩买斗文布。”“斗文布”即“斗纹布”,这是清朝生产的土布。朝鲜商人因进口西洋布无税,所以抛弃土布转而进口西洋布。道光年间也是西洋布大举进入清朝市场的时期,与清朝市场紧密联系的朝鲜市场也因此受到波及。要言之,朝鲜大举进口西洋布一是因为本国布匹供应不足,二是因为一开始时进口西洋布不用缴税,转销成本较低,更有价格优势。
开城商人(又称“松商”)
十八世纪晚期以来,以天主教为代表的“洋学”在朝鲜半岛迅速传播开来,尽管朝鲜官方多次下令禁教,但收效有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将西洋布与天主教联系起来,因而对西洋布持负面态度的认知在士人中扩散。儒者洪直弼在一八四九年撰写的《进士苏公行状》里褒扬苏洙榘之德,称苏洙榘禁止家人穿用西洋布,理由是“灭伦乱常,未有如洋贼者。宁冻死耳,不可以此贼手中物近身也”。洪直弼又在同年撰写的《可庵崔君墓碣铭》中称赞崔济默:“被服尚俭,家人欲衣以洋布,君责之曰:‘洋人无父无君,岂可服其布乎?’”曾任大司谏的柳致明为去世的儿媳金恭人撰写的行录里提到:“恭人临绝,戒勿用洋布以袭敛。洋布者,出西洋绵布也,丽密为服饰之佳品。自洋学滋蔓,而布遍于国中。识者占时变,恭人之言,所以正终也,亦可以观识度矣。”禁用价廉物美的西洋布成为可以在死后得到歌颂的德行,但也反证出这样做的人应该只是少数。
西洋布进入朝鲜半岛后,不仅引发了士人的警惕,还影响了朝鲜本土布匹的生产,导致消费文化发生变化。一八五〇年,前掌令姜继遇上疏称:“挽近洋货狼藉于世,家家效颦,人人贪玩,如非倭洋木,不着于身。至有绵农之乡,谓之无利,废而不耕,是不独当世之大病,洋学之不能灭熄,专由于通货之致也。将来之忧,有不可胜言者矣。”在姜继遇看来,西洋布进口严重冲击了本土布匹的生产,且天主教正是沿着西洋布进口线路进入朝鲜,不禁西洋布就难以禁绝天主教。因此他建议:“请自莱馆、湾府,一切禁断,则讵不为一举两得之政乎?”哲宗对此表示:“予将嘉纳矣。”“莱馆”是位于东莱的倭馆,“湾府”是位于中朝边境的义州。这两处都是朝鲜官方许可开展对外贸易的地点,也是西洋布进入朝鲜半岛的关键口岸。由于西洋布太受朝鲜市场的欢迎,甚至有人开始仿制西洋布。如“晋州一班户作广布,几如西洋木,一匹直六七十金。而一年断数匹。故未足为货云”。即仿制品生产成本高、产量低,无法与进口产品匹敌。西洋布在朝鲜的扩散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作为西方工业生产的象征,西洋布的流行意味着朝鲜民众的消费习惯开始受到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影响。这种消费文化的变化,不仅体现在对西洋布的接受与仿制上,也预示朝鲜民众对其他西方商品的兴趣和接受度会逐步提高。
东莱倭馆
西洋布不仅经由东莱与义州,还经由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的朝鲜西海岸进入朝鲜半岛。十九世纪中叶,朝鲜西海岸走私贸易盛行,黄海道等地多次查获沿海民众出海与清朝人交易货物的案件。如一八六一年,金楚善等人在黄海道长山串前海以人参九百三十三斤与清船船员换得西洋布七百匹;金应西等人在黄海道长渊近海以红参六十斤换得西洋布七十八匹以及清朝布匹;一八六四年金正连等人在黄海道甕津沿海以人参一百一十八斤换得西洋布一百七十匹等货物;一八六六年,金正烨等人在延坪岛海域以红参一百四十斤换得西洋布一百五十匹;等等。这还只是被查获的部分案件,未被朝鲜官府发觉的走私西洋布之数更是难以估计。朝鲜朝廷虽然多次下令清肃海防,但在贸易利润的吸引下,沿海民众与清朝船只的走私贸易禁而不绝。由此可见,西洋布已然经由陆路与海路等多种渠道进入朝鲜半岛。
一八六六年也是朝鲜历史上的一个关键年份,该年发生了法国军舰入侵事件,史称“丙寅洋扰”。在朝鲜民众的抗击下,法军败战撤军,但该事件实际上成为外国势力武装干涉朝鲜事务的起点,此后美国、日本等外国势力接连侵入朝鲜并染指朝鲜事务。在“丙寅洋扰”爆发之初,副护军奇正镇上疏称:“近日豪华轻薄,喜蓄洋物,贪服洋布,最为不祥,殆海寇东来之兆。”并提出了“命中外官搜括廛人所储洋物,焚之通衢。嗣后贸来者,施以交通外寇之律”的解决方案。高宗认为:“所陈诸条,明白痛快,可使洋丑足以破胆。”朝鲜君臣眼中的西洋布早已不是“圣恩”的象征之物,而变成了外国势力入侵的不祥之兆。
“丙寅洋扰”爆发前夕,左议政金炳学向高宗提到:“近日洋货之殆遍一国,已为有识之所忧叹,而番舶之来请交易,未尝不因其所好而然。”他建议:“凡属洋物,毋论纱缎器用,一切禁断。三江搜验后,如有冒犯而现发者,即其枭警之意,著为定式。何如?”即禁止进口包括西洋布在内的一切洋货,并强化义州地区的处罚力度。该建议得到了高宗的批准。到了十月底,议政府又称:“闻洋物之从莱府流出者,亦自不少云。其所禁止,宜无异同。一体关饬于该府,另为探察,俾毋敢如前交买。若有犯者,先斩后启。苟或掩覆,有所入闻,则该府使从重论勘之意,严饬何如?”也就是把禁止洋货进口的搜验地区范围从义州扩大到东莱,并将搜验工作的责任直接落实到东莱府使。该建议也得到高宗的批准。朝鲜这一系列禁令的执行情况如何呢?从《义州府状启誊录》的记录来看,这一时期义州仍有查获西洋布的走私案件。如一八六八年五月,义州商人赵重甫、金子甸两人“潜贸洋缎,恣意冒越”被查,随即被枭首示众。同年朝鲜朝廷在发往庆尚道左水营的公文中承认了“边禁荡然,谁执其咎?思之及此,宁欲无言”的现实,可见禁令收效不佳。回到文章开篇提到的一八六九年王宫盗窃案件,这些案件都是发生在朝鲜朝廷反对使用西洋布,颁布西洋布进口禁止令之后。宫廷女眷消费西洋布,商人们继续销售西洋布,事实上也瓦解了这些禁令的效力。
朝鲜义州街道
东莱邑内大市场
一八七一年,美国派军舰入侵朝鲜,逼迫朝鲜同意缔约通商等要求,与朝鲜军队爆发冲突,史称“辛未洋扰”。“辛未洋扰”开始后,朝鲜全国各地竖立起内容为“洋夷侵犯,非战则和,主和卖国”的“斥和碑”,排外情绪一度达到顶点。按理来说,遭遇两次洋扰之后的朝鲜应该更加严禁西洋布的进口,然而政策发生了变化。一八七四年,领议政李裕元向高宗报告:“度支用度,虽百万两,未易排用。而义州商税,曾有洋木等税,今为禁物。又有铁税,清钱今又革罢,税入渐缩,管税厅事势,渐不成样矣。”管税厅是一八一四年朝鲜在义州设立的收取贸易关税的机构。按一八四九年刊行的义州地方志《龙湾志》的记载,西洋布此时已出现在管税厅的收税物品目录中。一八五四年起,朝廷直接向义州派遣监税官将税款收至中央,因此管税厅也被称为户曹的外库。从李裕元的报告可知这些税款曾是管税厅的重要收入来源,而西洋布进口禁令严重影响了税收。针对该报告,高宗回答:“洋木初以洋物而禁之矣。今既为广东织造,则似不必禁之矣。”既然高宗已然松口,李裕元随即顺着高宗之意接着说:“近日称为洋木者,皆是广东木矣。”高宗担心允许进口广东布之后,可能会出现西洋布与广东布混杂的问题,又问道:“洋产与广东产,或有辨别之道乎?”李裕元回答:“定禁条,则似有可辨之方矣。”最终高宗决定:“广东木则许用,而申饬湾尹每于出来时另加搜验,期无洋货混出之弊也。”也就是说朝鲜仍维持西洋布的进口禁令,但允许进口广东布。但如何区别西洋布与广东布呢?高宗只是寄希望于义州府尹的搜验,这在实践中却难以落实。所谓广东布,就是从广东口岸进入中国的西洋布。广东布的进口许可,实际上打开了西洋布以广东布的名义进入朝鲜的方便之门。
斥和碑
其实部分朝鲜官员此前已了解广东布即西洋布。曾任北评事的郑元和向高宗报告:“广东木,即西洋木之别名也。”一八七三年冬他在咸镜道庆源“捉得广东木潜卖十余同于通衢上而焚之”。“同”是朝鲜常用的布匹计量单位,一同为五十匹,即郑元和查获的走私广东布多达五百多匹。至此,西洋布流入朝鲜的入口从半岛西北角的义州、东南角的东莱、西部沿海扩展到东北角的庆源。西洋布从朝鲜半岛四周的边境地区源源不断地走私进入内陆,导致朝廷的禁令难以收效。基于这样的情况,朝鲜官方许可合法进口广东布,既为了解决税源问题,也是面临管控无效局面时的无奈之举。
在西洋布之外,自鸣钟、望远镜、洋琴等西洋产品也曾在十七世纪前后陆续流入朝鲜半岛。但自鸣钟等物只是流通于上层人士中,从未像西洋布一样成为上至王室成员,下至普通民众日常可以接触、可以使用的共同喜爱之物,也不像西洋布一样真正满足了朝鲜民众的生活需求。换言之,西洋布才是证明朝鲜市场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关系的代表性物品。朝鲜通过与清朝、日本的贸易,间接而又广泛地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产生交集,西洋布正是经由早已存在的东亚跨国贸易渠道大举流入朝鲜半岛的。朝鲜从未远离大航海时代后的全球化浪潮,而且还是贸易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西洋布作为西方典型工业产品广泛流通于朝鲜市场,渗透至朝鲜基层。可以认为,早在《江华岛条约》签订前,朝鲜业已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一八七六年开港后,朝鲜市场更加深度嵌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使用西洋布等西方工业产品日益成为朝鲜民众的日常。西洋布在朝鲜半岛的流行不只是商品流通,背后反映的是朝鲜社会的深层次转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深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影响的社会转型。这一过程不仅重塑了朝鲜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结构,也为该国近现代充满波折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