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在信州(今江西上饶)铅山县鹅湖寺举行了三天的学术讨论会,史称“鹅湖之会”。今年适逢鹅湖之会850周年,想起2023年8月中旬,本公众号曾经连续发表《鹅湖之会史话》分题共五篇,本来就不是鹅湖之会的研究者,对鹅湖之会了解得很少,其哲学意义更是似懂非懂,所以写作该文,应该说就是一次自学的过程。今年11月1日,本公众号发表了《乾隆版<铅山县志>有关鹅湖之会综述》,目的是介绍《铅山县志》中历朝文化名人对鹅湖之会的评价,综述这些引文可以看出,乾隆八年、四十九年的《铅山县志》对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学术观点的分歧是持“始异而终同”(程敏政)的观点的。翌日,前上饶师院副院长、本人挚友吴长庚教授于微信中指教:
“关于朱陆学术异同问题,自朱子在世起,至明清300年始终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出现论著不下二十余部,见于四库书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程敏政的《道一编》陈建的《学蔀通辩》王阳明的《朱子晚年定论》李绂的《朱子睌年全论》王白田的《朱子年谱》。2000年,我将上述五种整理点校为《朱陆学术考辩五种》已由江西髙校出版社出版。我这里还有郑之侨编的《鹅湖讲学会编》收有雷鋐和郑之侨的二篇论文,讨论朱陆学术异同,亦颇有见地。后我们举办朱子国际学术会,我写了万字论文《朱陆学术异冋早晚论的历史考辩》。发表于当年的《朱子学刋》,可供你参考。”
长庚先生编注的《朱陆学术考辩五种》一书现存于江西铅山家中,远水不解近渴,按照长庚先生的提示,我在古籍网站查到了雷鋐(hóng)于清嘉庆十六年付梓的《经笥堂文钞》 ,内收《鹅湖诗说》一篇。
雷鋐,字贯一,号翠庭,福建宁化人。是清代中期的学者、官员,活跃于康熙末至乾隆年间。他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卒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鹅湖诗说》是雷鋐对南宋 “鹅湖之会”(朱熹与陆九渊学术辩论)的阐释与反思。他通过分析朱陆诗作,主张调和两家之长,既肯定朱熹 “道问学” 的扎实,也认可陆九渊 “尊德性” 的本心论,强调 “体悟本心 + 实践积累 + 研读传注” 的综合路径,体现了清代学者对宋明理学的总结与折中倾向。《清史稿》 称其 “和易诚笃,论学宗程、朱”,并记载其督学期间 “以小学及陆陇其年谱教士”,足见其学术正统性与实践精神。同时代学者 如方苞、朱轼等对其推崇备至,方苞甚至预言他将成为 “天下第一流人物”。
雷鋐的学术活动与著作,不仅反映了清代中期程朱理学的主流地位,也展现了学者对前代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其《鹅湖诗说》至今仍是研究宋明理学史的重要文献。读完这不长的一篇论述,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清朝乾隆年间的《铅山县志》对朱陆学术论争所持的中庸态度。
以下是《鹅湖诗说》全文,括号内黑色字是对加横线句的白话翻译:
乾隆八年七月,余返自江南,取道铅山,将游武夷。铅山令郑君之侨振兴鹅湖书院,躬课诸生。余与俱至鹅湖,诸生环侍,郑君请一言以示训。余曰:“讲学之书,先儒备矣,惟在心体而身验之,奚容赘?虽然,朱陆异同,聚讼至今,始于鹅湖之诗,试与诸生言之。”(关于讲学的书籍,前辈儒者已经论述得很完备了,关键在于内心体悟并亲身实践,哪里需要我再赘述呢?尽管如此,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分歧,争论至今没有定论,源头就在鹅湖之会时的诗作,我姑且和学生们谈谈这件事)
当日朱子送吕东莱先生至鹅湖,东莱约陆子寿、子静二先生来会。子寿赋诗云:
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
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
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
珍重友朋勤琢切,须知至乐在于今。
孩提知爱,稍长知敬,此孟子指出人之本心所固有,使知察识而扩充,即如筑室之有基,成岑之有址。子寿此诗,夫何间然?但所以筑室成岑,正有结构积累之功,非即以基为室、以址为岑也。圣经贤传,辨别是非邪正,以开牖人心,正恐卤莽涉猎,不得其精微之意,顾谓传注可不留情、精微可不着意乎?(圣贤的经典著作,辨别是非邪正,用来启发人心,正担心人们草率浏览,不能领会其中的精微之意,怎能说经传注释可以不重视、精微之处可以不用心呢?)当曰“溺情章句翻榛塞,着意空虚更陆沉”,则得之。
子静和云:
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积至沧溟水,卷石崇成泰华岑。
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
俗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自今。
子静此诗,首二句即子寿引孟子之意。子寿未说及工夫,子静斡旋之,故曰“涓流拳石,积至沧溟、泰华”。沧海不择细流,泰山不辞土壤,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集义以生浩然之气,正如是也。如谓自有易简工夫,则孔子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亦为多事矣。人不尽生安之质,不致知力行、日积月累,如何能践形尽性?若奋然立志,返求为己,则真伪之辨明,自下升高,非一蹴可至也。(如果说本身就有简易的功夫,那么孔子的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不就成多余的了吗?人并非生来就有安分守己的资质,不通过致知力行、日积月累,怎么能实现自身的本性、发挥自身的潜能呢?如果奋发立志,转而追求为了提升自己,那么真伪就能分辨清楚,从低处向高处进步,并非一步就能达成。)
朱子三年后乃和诗以寄怀云:
德义风流夙所钦,别离三载更关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篮舆度远岑。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沈。
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
此追忆当日相会时事也。“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沈”,此探问别后工夫也。因子寿脱离传注,子静自矜易简,恐开蹈空之弊,故曰“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厥后朱子答项平甫书云:“近世学者,务返求者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以内省为狭隘,左右佩劒,各主一偏,而道术分裂,不可复合,此学者之大病。”又云:“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上多了。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偏。”
朱子之心虚公广大,所以为百世儒宗。子静白鹿洞讲义,朱子深取之,谓其足以发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盖陆先生兄弟之学,固不可因鹅湖二诗定其生平。朱子答吕东莱书云:“近两得子寿兄弟书,却自讼前见之误。”东莱与朱子书云:“陆子寿前日经过,留此二十余日,翻然以鹅湖所见为非。’又云:’陆子寿不起可痛,笃学力行,深知旧习之非,求益不已。”朱子祭子寿文,尤深痛惜,谓其降心以从善,岂有一毫骄吝之私?
(朱熹的心胸谦虚公正、宽广博大,这正是他能成为百代儒者宗师的原因。子静在白鹿洞书院的讲学内容,朱熹十分推崇,认为它足以揭发学者内心深处隐藏的顽固弊病。可见陆氏兄弟的学问,原本就不能仅凭鹅湖之会的两首诗来断定他们一生的学术主张。朱熹在给吕东莱的信中说:“近来两次收到子寿兄弟的书信,他们都反省自己之前见解的错误。” 东莱给朱熹的信中说:“陆子寿前些日子经过这里,停留了二十多天,幡然醒悟,认为鹅湖之会时自己的见解是错误的。” 又说:“陆子寿去世实在令人痛惜,他专心治学、努力实践,深刻认识到旧有习气的错误,始终追求进步不停歇。” 朱熹在祭奠子寿的文章中,尤其深感痛惜,称赞他放下主观成见听从善言,毫无一丝骄傲吝啬的私心。)
子静与曹挺之书云:“学者且当大纲思省,平时虽号为士人,虽读圣贤书,其实何曾笃志圣贤事业?往往从俗浮沉,与世俯仰,徇情纵欲,汨没而不能自振。日月逾迈,而有泯然草木俱腐之耻。到此能有愧惧,大决其志,乃求涵养磨砺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读书、未得亲师,亦可随处用力,检点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所谓心诚求之,不中不远。若事役有暇,便可亲书册。”此段每读之,令人通身污下。陆先生未尝教人废书册,亦据此可见。
今之主张陆学者,尚曰“据依在心,岂靠书册为有无”,其弊不至不立语言文字、不入禅学不止,岂陆先生之教哉?即曰在人情事势物理上做工夫,并非顿悟,其不至师心自用、臆见自逞者几希!我辈惟在脱去俗学,如朱子所谓“读书则实究其理,行己则实践其迹,念念向前,不轻自恕”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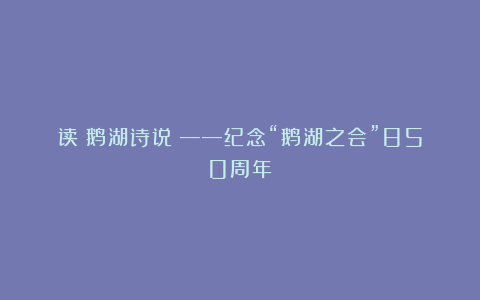
(如今推崇陆九渊学说的人,还说 “依据在于内心,哪里需要依靠书籍来证明存在与否”,这种弊端不发展到不立语言文字、陷入禅学的境地不会停止,这难道是陆先生的教诲吗?即便说要在人情、事理、物理上做工夫,并非突然顿悟,但若不注重积累,最终难免会主观臆断、肆意发挥!我们这些人只需摆脱世俗的学问,就像朱熹所说的 “读书就切实探究其中的道理,立身行事就切实践行圣贤的准则,每一个念头都追求进步,不轻易宽恕自己” 罢了。)
郑君政行事举,人皆信服,幸以此教诸生,使鹅湖山下正学日兴,人才日出,则岂特有功于是邑已哉?讲论之余,因书此贻郑君,俾诸生互切磋焉。
《鹅湖诗说》的核心观点是调和朱熹与陆九渊(陆氏兄弟)的学术分歧,主张 “体悟本心 + 实践积累 + 研读传注” 三者结合,反对学术上的片面化与极端化。
雷鋐对朱陆及陆氏兄弟的核心态度:
一、认可陆子寿 “本心固有” 的根基
赞同陆子寿提出的 “孩提知爱、长知钦” 是孟子所言的人之固有本心,但指出其不足 —— 只强调本心为 “基”,却未说明 “筑室成岑” 所需的积累与实践功夫,反对脱离传注的空泛体悟。
二、肯定陆子静 “积累为要” 的补充,批判其 “自矜易简”
认可陆子静以 “涓流积沧溟、卷石崇泰华” 补充 “积累功夫” 的合理性,但批评他将 “易简工夫” 绝对化,轻视经典传注与博学审问,担心陷入 “蹈空”“师心自用” 的弊端。
三、推崇朱熹 “兼容并蓄、知行合一” 的路径
赞赏朱熹 “心虚公广大” 的治学态度,认同其 “道问学与尊德性并重” 的主张,即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强调读书需实究理、行己需实践迹,反对 “务返求者斥博观为外驰,务博观者斥内省为狭隘” 的片面对立。
归纳起来,雷鋐的核心治学主张:
其一、反对将朱陆学说绝对对立,认为二者可 “去短集长”:陆氏重本心的 “尊德性” 是根基,朱氏重积累的 “道问学” 是路径,缺一不可。
其二、批判后世对陆氏学说的曲解:明确陆九渊从未教人 “废书册”,驳斥后世陆学支持者 “据依在心、不靠书册” 的极端观点,指出其易陷入禅学空谈的隐患。
其三、强调 “知行合一” 的实践论:主张学者需 “返求为己”,既察识本心,又通过研读经典、日积月累的力行,才能 “践形尽性”,不可妄图一蹴而就。
雷鋐早年肄业于鳌峰书院,师从著名理学家蔡世远(乾隆帝的启蒙老师),并私淑李光地,学术上以程朱理学为宗,主张 “穷理致知,躬行实践”。他强调 “居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认为理学需通过读书、体认与实践结合,反对空谈。
雷鋐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通政使、左副都御史等职,并多次担任浙江、江苏学政。他在任期间以程朱理学为指导选拔人才,整顿学风,被时人誉为 “弊绝风清,百年来所仅见”。其著作《经笥堂文钞》《读书偶记》等被收入《四库全书》,学术影响力深远。
雷鋐《鹅湖诗说》对后世学术发展的核心影响集中在学术格局、治学范式与理学传承三大层面,推动了宋明理学研究与实践的理性发展。打破 “非朱即陆” 的二元对立思维,为后世处理学术分歧提供 “去短集长” 的范例。启发清代中后期及近代学者重新审视宋明理学脉络,不再将朱陆学说视为不可调和的阵营,推动了理学内部的融合与互补。其 “知行合一” 的实践论影响后世教育与学术评价,尤其在清代学风整顿、人才选拔中,延续了 “穷理致知、躬行实践” 的务实导向。
作为程朱理学的传承者,雷鋐通过兼容陆学合理内核,避免了程朱理学的僵化,使其在清代保持持续影响力。为后世理学研究提供了 “批判继承 + 兼容创新” 的思路,影响了近代对宋明理学的整理与阐释,为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埋下伏笔。
《鹅湖诗说》起因雷鋐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七月去武夷山时途经铅山,铅山县令郑之侨重视教育,振兴了鹅湖书院,亲自为学生授课。我和他一同前往鹅湖,学生们环绕侍奉在旁,“郑君请一言以示训”,于是,雷鋐便即席就朱熹与陆九渊和陆九龄三首唱和诗说表达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分析,这随机的“一言”,客观上成为解析三首鹅湖诗的权威释义。《鹅湖诗说》披露的当时铅山县令郑之侨亲自在鹅湖书院授课,“诸生环侍”,洗耳恭听的谦卑之态,也反映了当时书院学风之正和教化之盛。
同治十二年《广信府志》对雷鋐铅山之行有载:
雷鋐,字贯一,号翠庭,宁化进士。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蔡文勤公高弟。德性醇厚,恪守程朱之学,诱掖后进,娓娓不倦。赴京取道铅山,门人郑之侨为令,攀留信宿。同僚属、绅士请诣鹅湖讲学,如朱子怀玉故事,学者多所感发。
【雷鋐,字贯一,号翠庭,是福建宁化籍的进士。他曾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蔡文勤公(蔡世远)的优秀弟子。他品性淳厚,严格遵循程颢、程颐与朱熹的理学思想,引导扶持后辈学子时,言辞恳切、不知疲倦。他前往京城途中经过铅山,弟子郑之侨当时担任铅山县令,挽留他住在铅山。当地的同僚、下属官员及乡绅,恳请他到鹅湖书院讲学,效仿朱熹在怀玉山讲学的旧例,求学的人大多受到启发。】
同治十二年《广信府志》和乾隆四十九年《铅山县志》对郑之侨延请雷鋐鹅湖书院讲学一事也有记载:
郑之侨,潮阳人。知铅山县事,乐育士子,勤政为民。以邑中捐罚欵,置鹅湖书院田租四百有奇,以广膏火。延宁化雷公鋐诣书院讲学,躬执弟子礼。一时人士,多以学业宦绩显。又纂修县志,辑《鹅湖讲学会编》,著《书田志》,刊正《六经图》。
【郑之侨,是广东潮阳人。他担任铅山县知县时,热心培育读书人,勤勉政事、体恤百姓。他用县里的捐纳与罚款款项,购置了四百多石租额的鹅湖书院学田,以此扩充书院的办学经费。他邀请宁化的雷鋐先生到书院讲学,并且亲自向雷鋐行弟子之礼。当时的读书人,大多凭借学业成就或为官政绩声名显著。他还主持编纂了《铅山县志》,辑录成《鹅湖讲学会编》,撰写了《书田志》,校正刊印了《六经图》。】
《广信府志》补充了有关郑之侨延请路经铅山的雷鋐在鹅湖书院讲学的史实,但府志的记载与雷鋐的《鹅湖诗说》在细节上有出入,前者说雷鋐是前往京城时途经铅山,而后者说是“取道铅山,将游武夷”;一个说是返程途中,一个说是去程途中。当然应该以《鹅湖诗说》为准。但雷鋐不便说的郑之侨对雷鋐“躬执弟子礼”,府志说了,这个细节表现了郑之侨尊师礼贤的优良品质和铅山尊师重教的民风。
2023年,本人在写完《鹅湖之会史话》五篇之后,曾经斗胆附庸,步先贤陆子寿之韵,和诗一首:
读鹅湖之会史谨步先贤韵奉和
鹅湖夜静梦怀钦,懵懂羞听论辩心。
笔墨常枯偏读史,江河不废更瞻岑。
秋风圮塔禅房殁,社酒盈杯讲席沉。
苔旧人新书院古,谁将俎豆祭于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