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石不语
作者:刘光新
引言:有些记忆不是被遗忘的,而是被埋进土里,等一场雨,就重新发芽。
一、归途:长岗庙的青石板
长岗庙是母亲的故乡,我儿时常被送去给外公外婆带养。
但长岗庙没有庙,至少在我这次回来时,已不见那座曾香火断续的小庙——它早已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拆毁,砖瓦被拆去修了村小学的围墙,神像则不知所终。如今只余一块斑驳的水泥碑,歪斜地立在荒草间,字迹模糊,仿佛连地名本身都在渐渐失忆。
我踩着脚下那些被岁月磨得温润如玉的青石板,一步一步走进童年。它们还在这里,泛着幽微的光,像是沉入水底多年却未曾锈蚀的旧铜镜,照得出我六岁奔跑的身影,也映得出今日五十岁的沉默轮廓。
这些青石板是母亲用脚丈量过的路。她年轻时从这里走出去,嫁人生子,老了又梦回此地,她总是呢喃:“我想多走几次东街口到外婆家那段坡。”可因为年迈以及亲人离散,她终究不能常常回来。
而我,在暌隔四十余年后,因一位远房堂舅的葬礼,成了这片废墟中唯一一个为过去送行的人。
村子早已不是村庄。年轻人去了岳阳、长沙,甚至北京、广东……;老人死的死,搬的搬。老屋倾颓,田地荒芜,唯有几株野桃树每年春天仍固执地开花,粉白的花瓣落在青石缝里,像谁遗落的一纸情书。
就在断墙残垣之间,一行褪色的红漆标语赫然撞入眼帘——“农业学大赛”。
五个字,灰红交杂,龟裂如干涸的血痕。
我怔住。这不是政治口号,这是时间的裂缝。
那一刻,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年的广播声、外公背着化肥袋走过这条街的脚步声、外婆抱着我在晒谷场上数星星的画面……全都从这行字后涌出,扑面而来。
原来我们从未真正离开过那个时代。我们只是把它藏进了骨髓。
二、三郎堰的女人:葵珍
三郎堰不是堰,是个镇集,距离长岗庙不足三华里。
一条窄街,两排低矮商铺,每逢赶场日便挤满挑担的老农和吆喝的小贩。猪叫声、鱼腥味、油条香混在一起,构成一种粗粝却真实的生活气息。
她在街开了家小店,叫“葵之珍家纺”。
店名是我取的。
那是2012年,我们在某个文学论坛相识。她是ID“月下葵花”,我是“洞庭孤帆”。她说她喜欢向日葵——“向着光活,哪怕没人看”。我说那你该叫“葵之珍”,既是名字,也是心意:你是我见过最珍贵的平凡女子。
后来我们见面了。她并不惊艳,三十多岁,长发垂肩,眉眼清瘦,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衬衫。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细纹绽开,像阳光划过秋湖。
她丈夫早逝,留下两个孩子。她靠加工并售卖床单被套维生,一天站十二个小时,手指常年贴着创可贴——被缝纫机针刺伤的。
我们一起去过附近的仙鹤寺,那里有个出身官宦之家、接受过高等教育、有份稳定工作、有一个贤淑的妻子和一个美丽聪慧的女儿,却看破红尘却遁入空门的释怀逸。
那天风很大,檐角的风铃响了一整日。我没有烧香,她也没有。我们坐在偏殿台阶上,看一只猫舔爪子。
“你说人死了会去哪儿?”她忽然问。
“也许变成一阵风,吹过你晾在阳台上的被单。”
她笑了,轻轻打了我一下:“你就这样安慰人?”
“不是安慰,是相信。”我说,“我相信有些人,死了也不会走远。”
我们在镇集靠山的东山水库边吃了一顿土鸡。辣得冒汗,她一边擦泪一边说:“这是我这几年吃得最开心的一顿饭。”
我没敢问她上一次开心是什么时候。
我也曾拍下她女儿写给老师的信的底稿,字迹工整。信写于三年前,那时候她才十五岁还在读初三,父亲刚刚过世。那封信充满感激之情:
“老师,我知道我家穷,妈妈很累。我不敢生病,怕她花钱。弟弟调皮,我会管他。您送我的画笔,我一直没舍得用,想留到考上美院那天再打开……”
老师的回信也很感人,对她满满的关爱溢于纸上:
“人不能活在过去,因为你已经无力去改变什么。但值得庆幸的是,人人都还有未来,未来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未来的日子有悲痛的妈妈需要你去安慰,有无知的弟弟需要你去照顾,你已经成了这个家庭的重心。那么长的路,你不得不坚强、乐观,积极的心态能让自己和关心自己的人都过得好一些。”
“还记得周末我叫你妹妹吗?真让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老师有个姐姐,可我却一直想着有个乖巧的妹妹。那我们兄妹就这么认了?”
在另外一封信中,老师还这样劝告与鼓励她:
“你说你爱哭,我喜欢爱哭的女孩子。感性、懂感情,这不是什么毛病,无须刻意去压抑自己。就要面临中考了,老师会关注、支撑你走到最后的,我一定是你永不倒的后盾!”
我看着那些信,眼眶发热。我把照片发到网上,标题写着:《人间岂无真情在?》
评论很多,有人说感动,有人质疑作秀。只有她看到后哭了,然后给我发来一句语音,声音颤抖:“谢谢你记得我们。”
三、浮木:两个溺水者
我们的关系,无法定义。
如果非要说,那是一段灵魂的临时避难所。
那时我正经历一场精神崩塌——工作受挫,家庭矛盾,挚友背叛,整个人像被抽空了气的皮囊,走在路上都觉得脚步虚浮。某夜我在湖边坐了三个小时,差点跳下去。
而她,刚走出丧夫之痛三年。夜里常惊醒,梦见丈夫浑身湿透站在床前说:“我没穿寿衣。”
我们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喘息的机会。
我去常德出差,绕道去她家;她去株洲进货,我在岳阳火车站等她。火车停靠五分钟,隔着玻璃窗说话,她说冷,我就把围巾递进去,让她裹着。
有一次,我在她家里留宿。没有激情,没有誓言。她煮了碗面,我们并肩坐在小床上吃。吃完她说:“你可以睡里面。”
那一夜,我们背对着背,中间隔开半尺距离。但我知道,我们都醒着。
第二天清晨,她做了煎蛋和稀饭,轻声说:“昨晚你翻了十七次身。”
这就是全部的情欲。
甚至谈不上情欲。
更像是两个冻僵的人,靠近火炉,不敢太近,怕烫;也不敢远离,怕死。
我不是不爱她。
而是不敢爱。
因为我给不起未来,也保不住现在。
我介绍她女儿去岳阳当幼师,鼓励她学画画。她真的去拜师学国画,老师被她的勤奋打动,免了学费。几年后,她的作品居然入选了市里的展览。
我默默关注,点赞,但从不评论。
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对她的帮助是一种施舍,或是一种期待回报的投资。
我们就这样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像两条平行线,在某个瞬间靠得很近,却又注定永不相交。
直到某天,我换了手机号,注销了旧微信。
再后来,她也消失了。
没有人删除谁,只是生活推着我们向前走,一步一回头,终于连背影都看不见了。
四、足迹:十年后的访问记录
十年。
我以为一切都已尘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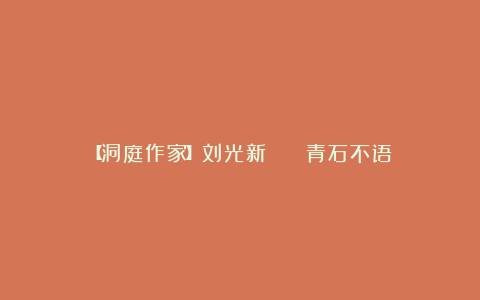
直到在微信群遇到一个三郎堰的微友,记忆的闸门才重新打开,我不但在群聊中谈起她,还在第二天写作了一篇《长岗庙的青石板与三郎堰的女人》。
第三天,我准备通过邮箱投稿。登录QQ,新足迹提示跳了出来:
*葵珍于前天17:20访问了我的主页
我的心猛地一缩。
这个名字,已有九年七个月零三天未曾出现。
我翻看聊天记录,发现就在我微信群里提到她仅仅四个小时前,她访问了我的QQ空间。
显而易见——
我在想她之时,她也正在想我。
冥冥之中,是否真有一种看不见的丝线,缠绕在两个曾经相依取暖的灵魂之间?
我小心翼翼点进她的空间。几乎没有更新。最后一次动态是一年前的5月20日,一张向日葵的照片,配文:“花开有时,人散无期。”
相册里共十四张生活照,其中三张是我们那次去东山的照片——风景、水库、农家乐门口。
没有我的脸。但我记得她当时站在画面外,举着相机,笑着对我说:’你往左边站一点,阳光更好。’
我想加她好友。犹豫良久。
又想抹掉自己的访问痕迹,怕她知道我窥探过她的世界。
可太久没有登录QQ忘记删除方式了,只能任由系统冰冷地记录下:“此人来过。”
最终,我选择留言:“如果你看到,请告诉我,你还好吗?”
三天后,她通过了验证。
第一句话是:“被弃的感觉很难受,这次?”
我回:“没有谁弃谁。你我都知道。”
她说当年以为是我删了她,伤心了很久。但骄傲让她忍住不去追问。
“后来就想,大概不属于我心灵相交集的缘吧。”
我解释只是换了账号。不知道她是否相信,但也没有深究。只是说:“那天我只是偶然上了QQ,忽然就想看看你过得怎样。没想到第二天,就看到了你写的我。”
然后她发来一串消息,热烈得像个少女:
“不喜欢也不许再拒绝[难过]”
“明天理,后天还理,一直一直都不许不理”
“再拒绝,也许就是一辈子了”
“想牵你抱你,嘻戏打闹,不成体统的疯闹都是我心里面最温馨的”
“我可以摸你的光头,你可以揪我的瓣子[呲牙]”
“见面皆欢喜,无愧于任何人[微笑]”
我看着屏幕,眼眶发热。
原来有些感情,并不需要婚姻、占有、承诺。
它可以轻如鸿毛,却重如泰山。
它不在世俗的认可里,而在深夜突然亮起的访问记录中,在十年后依然愿意为你保留三张旧照的相册里。
五、尾声:青石不语
我又一次回到长岗庙。
青石板还在,更旧了,裂缝更深了,但依旧坚硬。
三郎堰的集市仍在喧嚣。她的店还在原址,换了招牌,更大了些。橱窗里摆着绣有向日葵的四件套,标签上印着:“葵之珍·原创设计”。
我没进去。
站在街对面看了很久。
看见她走出来,抱了一叠货,对隔壁摊主笑了笑。
她头发已有些灰白,背略弯,但步伐坚定。
我没有打电话,也没有发消息。
只是默默写下这篇小说,将所有未说出口的话,所有未曾兑现的诺言,所有压抑的温柔与遗憾,都刻进文字里。
或许有一天,她会读到。
或许不会。
但没关系。
就像青石板不会说话,但它记得每一个踩过它的人的脚步;
就像那行“农业学大赛”的标语早已褪色,却依然倔强地留在墙上;
就像那段没有结果的关系,从未宣称爱情,却比许多所谓的爱更接近真实。
后记:
这个世界太多人追求轰烈的爱情,却忽视了另一种情感的存在——
那是两个破碎灵魂在黑夜中的短暂交汇,是寒夜里的相互依偎,是没有占有欲的深情,是没有契约的守望。
她们不是主角,她们是背景板上的女人。
他们是失败者,是边缘人,是社会统计表里忽略的数字。
但他们活得认真,疼得真实,爱得克制。
葵珍这样的女人,千千万万。
她们在菜市场叫卖,在夜市收摊,在孩子作业本上签字,在丈夫坟前烧纸。
她们不哭喊,不说苦,只是低头走路,一脚一脚踩在生活的青石板上。
而我愿以这篇小说,致所有在风雨中挺直脊梁的普通女性,
致所有不敢言爱却始终温柔的孤独旅人,
致那一段无关爱情、却深入骨髓的——
生存之暖,人性之光。
长岗庙的青石板不会说话。
但它记得一切。
作者简介
刘光新,网名lgx730,有江湖绰号曰“七哥”或“七爷”。师范大专科班出身,早年从教作了三年孩子王,后转行调入国营工厂,再进入商业系统,半生蹉跎一事无成,晚年混成了灵活就业者。
除中国共产党外,平生未再加入任何社会团体,无任何作品发表于纸媒,亦无任何文字工作者身份或证书。
凭恃文字薄技纵横本地于网络十余载,有文友评价“时政思想评论,偌大的岳阳无人可出其右”,又好藏否人物,惹来神憎鬼厌,人称“气煞人”、“搅屎棍”;又自诩精通法律,常抱打不平,为地方公检法目为公敌。
然而,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近段开始转向情感题材写作。
图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