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之前,笔者一直没有读到结尾,一直不知道,小说里的那个十恶不赦的坏蛋,竟然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明明知道那个漂亮的女孩,是他的私生女儿,但他还是性侵了她。
《冬天里的春天》里的这个坏蛋,名叫王纬宇,他过去是地主家的二少爷,但后来参加了游击队,建国后,他一直搞投机,文革期间更是见风使舵,成了风派人物,参与到对主人公的迫害风暴之中。《冬天里的春天》的主要线索,就是通过主人公于而龙回到游击故地,寻找他的第一个妻子被人暗害的真相,最后查出的谜底,就是背后给了他妻子致命的一枪的就是小说里的这个投机分子王纬宇。
但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王纬宇在道德上也是一个恶贯满盈的人物,在瓦解中国人信守的人伦道德上突破了基本底线,可以说在中国小说里也是一个相当罕见的恶魔。
这种用“道德审判”将小说里的恶人“人设”置于死地,可以说是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里不约而同的共性选择。
在同样是获奖小说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那个性侵最为漂亮的四女儿(北影版电影里由李秀明扮演)是她的姐夫。同样是一幕乱伦的丑剧,但比之《冬天里的春天》里施加于坏蛋的恶名,看起来要轻得多。
在《芙蓉镇》里,作为负面角色存在的投机分子王秋赦,同样是一个道德沦丧的渣男。
因此,这些八十年代文学作品里的特有的风派分子形象,都被作者赋予了最丑陋的道德污浊,形成了那个年代文学别具一格的“道德审判”火力围剿。
不过,现在看来,这种道德审判最登峰造极的还得数《冬天里的春天》,因为在这个小说里,把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拉扯到最丑恶的道德沦丧地狱里进行超越接受底线的审判。
实际上,我们注意一下,在《冬天里的春天》袭仿的苏联原著小说《多雪的冬天》里,仅仅设置了一个已经达到耸人听闻的父女疑云,并没有在这个危险的关系上,倾斜到乱伦的沟渠里,但是《冬天里的春天》变本加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原作小说里可以大加发挥的父女关系的神秘疑团基础上,简单粗暴直接地完成了生父性侵女儿的爆炸性情节设置,直接让读完这个小说的读者惊掉了下巴。
《多雪的冬天》苏联版
笔者就在读完了《冬天里的春天》一直没有读到的结尾的时候,感到了一种震惊。
然而,换一个角度,《冬天里的春天》里的父女关系恶俗趣味,与袭仿的苏联原著小说《多雪的冬天》里的最核心情节父女疑云,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相对而言,苏联原著探讨的是一个人性的问题,代表着苏联文学在一个新的时空里重新审视旧时代的丑恶基因而透露出的给予宽容的一种新的气息,相比之下,《冬天里的春天》在同样的父女疑云基础上,基本无意表现人性的冲突,反而顺手牵羊拿过来用这种父女关系在紊乱的情况下最容易达到的给予政治对手致命一击而具备的先天的道德大棒的宏大杀伤力。
这里,我们适当回顾苏联原著小说《多雪的冬天》的核心构思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多雪的冬天》的中文版“内容提要”中,看到这部小说原载于苏联《小说月报》1971年5、6两期,很快,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12月就出版了这本小说的中译本,相隔时间一年多一点,这样的翻译速度可谓相当的惊人了。
这部小说给予中国文学界带来的巨大冲击,就是小说采用了“意识流技巧”,描写时空落差巨大的现实生活。
《多雪的冬天》原文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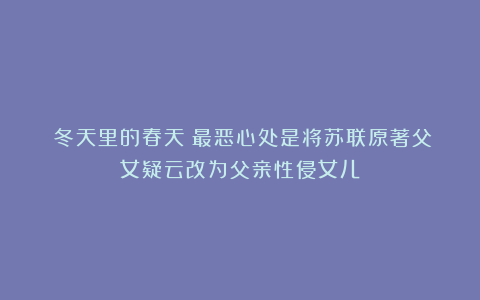
在当时西方小说尚无法进入中国的情况下,《多雪的冬天》中用意识流动,打破时间的壁垒、肆意地在现在时与过去式中自由转换的写作技巧,给予中国作家近乎带来的是教科书式的启蒙作用,一旦改革开放大幕开启,文学的春天到来,中国作家一时半会难以从西方小说里“接纳”信手拈来、为我所用的先锋文学技巧,而苏联作家作品里的这种“伪意识流”的灵动风格,便可以迅即地被中国作家快速吸收,从而形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一批由王蒙、李国文、张贤亮这些作家自发组团而成的看起来横空出世、惊艳文坛的所谓意识流作家群落。
应该说,改革开放的文学的先声,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悄然酝酿,这就是《冬天里的春天》这个标题的意思,那就是春天,是随风潜入夜地暗藏在冬天的严寒中的。
而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的意义,显然不同于《冬天里的春天》,《多雪的冬天》强调的是,即使现在已经开始迈进了解冻的年代,但是这个冬天依然是“多雪”的,历史的残雪仍是一种重压。
在《多雪的冬天》中,小说设计出的一个最为核心的情节,就是当年的游击队长在寻访故地的时候,惊愕地看遇到了当年在游击队的时候曾经同居的一个女人,她有一个女儿,而这个女儿自认为她就是游击队长所生。
而实际上,这个女孩,是游击队长同居女人与前夫所生,而这个前夫,是一个投靠德国纳粹的“俄奸”,后来被处决,但母亲一直没有告诉女孩真相,而女孩却自认为游击队长是她的亲生父亲。这样,她就有了一个根正苗红的好父亲。
发表《多雪的冬天》的苏联杂志
《多雪的冬天》的核心故事,就是如何重新审视这个基因烙印着父亲邪恶的无辜女孩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成色的重大问题。
《多雪的冬天》的出现,实际上体现出苏联对人道主义的大胆呼吁与摒弃罪恶基因遗患后代的新型观念,一句话,那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旧有观念,应该翻篇了。
一部洋洋洒洒的35万字的《多雪的冬天》就是体现了这样一种观念。但是,一个父亲是“俄奸”的女孩的身上的最致命的包袱,如同“多雪”一样,依然是一种望而生畏的巨大压力。
整个《多雪的冬天》呼吁的就是抛开这种“多雪”的负重,还女孩一个生命的自由与清白。
这样的观念,出现在苏联七十年代,有着它的必然性。毕竟苏联已经走过了斯大林时代,走过了赫鲁晓夫时间,纠结于历史与过去,就无法迈向未来,必须抛开基因中过多的“多雪”的丑恶基因的丧尸还魂。
《多雪的冬天》里这个含有深意的情节,当被《冬天里的春天》“拿来主义”为我所有的时候,原有的寓含宽容意义的内质被荡涤干净,而唯一的赋能,被赋予了泼污政治对手的大棒功能。
我们看看《冬天里的春天》里的这个父女疑云设置。
插图里的女孩就是那个被父亲性侵的无辜者
《冬天里的春天》里的主人公于而龙与《多雪的冬天》里的主人公一样,都是游击队长,他回到故地,寻访历史真相,也遇到了一个相当漂亮的女孩,这个女孩,与《多雪的冬天》里的那个“俄奸”女儿一样,也把于而龙当成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但《冬天里的春天》并没有止于此,在接下来发生的情节里,我们知道,《冬天里的春天》里的这个女孩并没有一个显性的带着罪恶基因的坏父亲,而是于而龙的政治对手王纬宇。随即情节开裂,爆出了王纬宇曾经在文革期间回到故乡的时候,性侵了这个女孩,而王纬宇明明已经知道这个女孩是她的私生女,他还是没有停止自己的罪恶之手。
小说里这样描写这个可以用鲁迅笔下使用的“嫖父”概念命名的人物内心:
——王纬宇把那个颤抖着的,哀告着“别!别!”满眼泪光的女孩子,紧紧压住,心里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万一,她真是我的亲生女儿呢?”
“管它咧!”王纬宇自己回答着自己:“需要就是一切!”——
而“需要就是一切”,正是王纬宇日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如鱼得水的恪守的信条。
中国版插图
《冬天里的春天》由此通过这个人物完成了对这种政治小丑的道德审判。可以看出,作者设计出这个人物的逻辑动因,是按照这种人物的政治选择,也就是“需要就是一切”的准则,倒推到道德维度里的信条的。
但显然这种审判是“为审判而审判”设置出来的生硬的概念化设定,因此,这个情节, 在《冬天里的春天》里的重要性与苏联小说《多雪的冬天》里的作为核心设定而振聋发聩推出的人道主义申诉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可以说是对父女关系的破解中的一种最恶俗的延伸与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