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自己,愈暖愈从容。
茶该怎么饮?
茶,不必众饮。人多则语杂,少了那缕袅袅的澄静。两三知己同品,固然清雅,却须是心意相通的友人,方能共赏茶里的山川岁月。然而,茶终究要一个人饮,才品得出深长的回甘。
冷,是一种触觉,也是心间偶尔浮起的底色。无论屋内暖意如何包裹,我们总在某个抬眼望向窗外的瞬间,遇见一片茫茫的白,或一树枝桠伶仃的静。
一个人捧着杯子站在窗前,看呵气在玻璃上晕开薄雾,外面车流无声划过像默片;一个人穿过寒风街头,竖起衣领,手中保温杯透过手套传来隐约的烫;一个人蜷在沙发里,膝上毯子渐温,壶中水声由响转轻,最终只剩茶叶缓缓沉底的静谧……即便身处暖气充足的房间,也会在起身续水的片刻,忽然觉察指尖一丝诚实的凉。
冷,是季节赋予的留白,让我们在其中轻轻蜷缩,又缓缓舒展。
在一日复一日干燥而重复的冬天里,渴望浸润。厌倦空调房里僵硬的暖,厌倦室外凛冽刮脸的风,厌倦一切需要挺直背脊的社交、保持清醒的寒暄。我开始懂得,为何总有人贪恋这一口滚烫——
茶,仿佛是冬天呵手时的那一点暖,是生活褶皱被徐徐熨开的温柔仪式。被茶汤浸润的身体,从喉间到胃腹,渐渐苏醒、舒展。所有紧绷与焦躁,在几杯茶后皆化作白烟袅袅,思绪的棱角也被泡得柔软而明亮。
然而,饮茶绝非解渴。真正懂茶的人,当学会聆听茶。何时煮水,何时出汤,何种温度配何种茶叶,皆有心意。而非仅视作驱寒之物,一饮而尽。
人间烟火,皆是寒冷岁月里扎实的暖意。想起《岁时记》里写,古人冬日起炭煮茶,看雪敲竹,“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不必多言,不必热闹,只守着这一炉红火一壶醇暖,便觉得时光悠悠,冷也成了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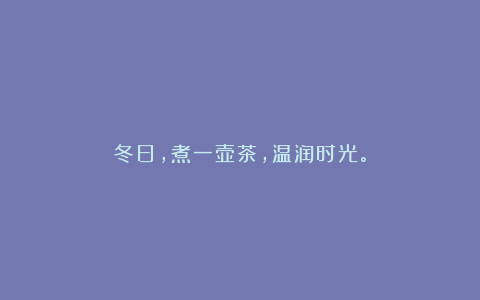
不被急促与喧嚣捆绑,安心等待一壶水开、茶叶舒展的时刻,短暂地成为自己的主人。这种专注的、近乎冥想的独处,正是冬天慷慨赠予忙碌现代人的,一种迟缓的慈悲。
正如一位茶人曾说:“在外奔波者,满身风霜又何妨。回到屋里静静煮一壶茶,让寒气从毛孔散去,让心神在茶香里归位。即使不爱甜腻,还有这一杯清苦回甘,替我接住整个冬天的萧索。”
深以为然。大概,这就是茶,在冬日存在的意义吧。
于是,一人居,一人暖,一人饮,一人看着窗外的天光从清冷转为昏黄,绝非寂寞之事。雪与诗是静的,茶与独处也是静的。或许这才是冬天平等赋予每个人的内在炉火。
小时候,不懂茶,只觉得是大人杯中褐色无趣的水,是宴席尾声潦草的收场。好像人总要走到某个年岁,才会懂得茶的厚重与轻盈。
也渐渐明白,冷是必然的,然而独自度过冬天也没什么不好,重要的是心中的暖意。想起《茶之书》里写:“茶道本质上是对’残缺’的崇拜,是在我们都明白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可能的完美,进行的温柔试探。”
一人暖,一人饮,亦可以完成这样的小小试探。
明人陈继儒在《茶话》中写:“一人得神,二人得趣,三人得味。”
原来从古至今,安宁、清澈、自在,就是一个人与茶相认的方式。
煮一壶茶,温润这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