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动静”作为中国哲学思想史上一对古老而核心的范畴,凝结了历代贤哲对宇宙法则、万物运行机理及其存在本质的深邃思索。此对范畴的演变与丰富,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哲学思辨核心议题的转向与深化轨迹,亦成为各思想流派哲学体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支点。
一、先秦:动静之道的发轫与多元基调确立
(一)老子的辩证奠基:动源与静极
道家创始人老子在宇宙本体“道”的层面开创性地对动静关系做出了深刻的哲学思辨:
“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此语揭示“道”内在的逆向、回返机制是其运行的根本特质,明确将“动”作为“道”的固有属性,深刻暗示变化是宇宙的根本法则。
“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老子·十六章》)。在观察万物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现象之后,老子提出万物运行的最终状态(“根”)和终极目标在于复归于虚静之境,认为“静”才是存在的本真状态与万物的最终归宿。“致虚极,守静笃”的修行要求,正是为了契合这一宇宙的根本法则。
老子还将“静”提升至本体高度,提出“静为躁君”(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将静视为躁动的主宰。在治国理政层面,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将“清静”视为天下秩序的根本原则。
老子首次为动静关系注入了深刻的辩证性张力:动是道的显化方式,静则是道的终极归宿,两者相互依存,统一于道。
(二)《易传》的崇动尚变:刚柔相推与寂感一体
作为儒家系统哲学化的重要成果,《易传》基于对《周易》的阐发,大力强调了宇宙变易不居的性质,并引入了“刚柔”这对紧密关联的范畴来诠释动静:
强调“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的运动永恒性,认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易·系辞下》)。阴阳刚柔势力的交互作用与推荡,直接引发变化,构成了事物运行(“动”)的核心内容,突出强调了运动变化是宇宙的普遍和根本状态。
“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易·系辞上》)。运动与静止有其规律(“常”),动静的不同表现可以直接判断刚柔力量的消长与分明界限,明确将“动”对应于“刚”、“静”对应于“柔”。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易·系辞上》)。这揭示了《易传》动静观中更深层和关键的一面:作为宇宙最高法则的“易理”(或“神”),其本体状态是“寂然不动”、“无思无为”的至静境界;然而正是这种绝对的“静”,具有不可思议的感应能力,一旦受到触发(“感”),即可畅通无阻地遍知通晓天下万物之理。这为后世关于本体之静与现象之动关系的讨论埋下了伏笔,也为“动静互含”的思想开启先河。
二、汉魏隋唐:玄佛视域下动静关系的深化与本体化
(一)王弼:以无为本,动起于静
三国玄学领袖王弼基于其“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对老子和《易传》的动静观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与融合,将“静”提升至本体的优先地位:
“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老子注·十六章》)。宇宙万有皆源于虚无(“虚”),一切运动皆肇始于静止(“静”)。此论明确规定了“静”相对于“动”在存在发生序列上的逻辑先在性。
“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周易·复卦注》)。天地宇宙的根本在于本体(“本”)。万物运动最终必然停息复归于静,并且指出本体之“静”具有绝对性与超越性,它并非是与“动”相对的、处于同一层面的存在状态(“静非对动者也”)。王弼在这里区分了作为万物运行状态相对的“动静”和作为本体特征的超越性之“静”(本体的虚寂状态)。这种将“静”本体化、绝对化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关于动静问题的讨论方向。
(二)僧肇:即动求静,动静不迁
东晋高僧僧肇融会玄学与般若中观思想,在其著名哲学论文《物不迁论》中提出了极具思辨性的“即动求静”(又称“物不迁”)说:
“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物不迁论》)。探求不变不动本体(“不动之作”)的真谛,并非是要脱离运动变化的现象世界去寻求一个孤立的静止状态(“释动以求静”),而是要在纷然万象的运动变化之中去体认那不动的实相(“必求静于诸动”)。因此,万物表面上运动变化(“动”),其本体实相却恒常寂静(“常静”)。
僧肇通过剖析时间(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可连接性,论证“物不迁”——每一事物都只在当下其特定的时空点位上存在,过去的已成过去而非延续至今,未来的尚未到来。因此,事物的每一状态在其所定位点上都是“凝然不动”的,事物在现象上有连续运动变化的“假象”,但在绝对的本体意义上并无真实的“迁流”。此观点以高度的辩证思维深刻揭示了现象(动)与本真(静)的复杂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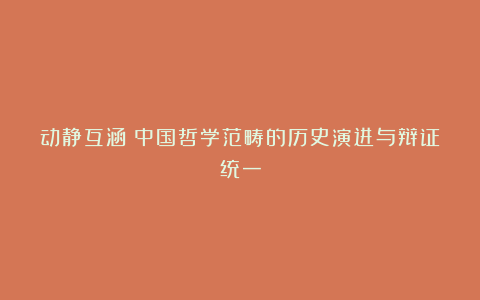
三、宋明理学:动静的体用化解析及其内在张力
(一)周敦颐:物动与神静的二元分野
北宋理学开山周敦颐在《通书·动静》章中明确区分了两类性质不同的动静: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具体有形的事物(“物”)的运作特点是:当其运动时就不包含静止,当其静止时就不包含运动。意即事物在同一时间只能处于一种状态(动或静),动与静在具体器物层面是相互排斥、截然分离的二元对立关系。
“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作为宇宙最高法则和微妙作用力的“神”(相当于太极之理或天道),其运作特点是:看似在发动作用(“动”),却并非如具体器物那样在空间发生位移或转变(“无动”);看似处于寂然不动状态(“静”),却又并非如具体器物那样完全凝固停滞(“无静”)。这揭示了超越形器之上的本体性存在(“神”)具有动静相交融、超越具体动静形式的特质。周子这一区分在概念上非常清晰,为后来理学家深入探讨动静之关系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点明了本体之理(“神”)的动静相即性(动中含静,静中有动,而又超越具体动静形式的束缚)。
(二)朱熹:体用相涵,以静为本的理气辩证
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在吸收周敦颐思想的基础上,以其庞大精密的理学体系对动静问题进行了更为系统全面的阐述:
“太极自是含动静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或理),其本身就内在包含了动静的可能性(“动静之理”)。这个“动静之理”是本体属性,并非外在于太极。
“静即太极之体,动即太极之用”(《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从“体用”关系的角度看:太极本体表现为宁静内敛的“体”的状态(“静即太极之体”),而其显现其生生不息功能(生阴阳、化万物)则表现为活跃的“用”的状态(“动即太极之用”)。体用不离,故动静亦一体。
“若以天理观之,则动之不能无静,犹静之不能无动”(《答张敬夫》)。从最高的天理层面来审视万物,则运动之中必然伴随着相对的静止因素或阶段,静止之中亦潜藏着运动的力量或趋势,两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
“方其动时则不见静,方其静时则不见动”(《朱子语类》卷九十九)。然而,当具体考察某一特定事物的具体时刻或状态时,当其表现为强烈的运动状态,此时其静态方面不易被察觉;反之,当其呈现显著的静止状态,其动态方面也不突出。这揭示了在现象层面直观感知上动静的不兼容性。
“然敬字工夫,贯动静而必以静为本”(《答张敬夫》)。在重要的道德修养方法(“敬”)上,朱熹强调“敬”是贯穿于人的动态活动与静态收敛的修养工夫,但在这种贯穿中,应确立“静”作为“根本”与主导地位。这不仅基于其体用观(体主静),也考虑到修养实践的需要——未发状态的持守(涵养于静)是已发状态调御(省察于动)的基础。
四、明清之际:向实学回归与动静观的唯物主义革命
(一)王夫之:太虚本动,动静皆阳之实有
明清之际的卓越思想家王夫之,以其深刻的实学精神和彻底的唯物主义气论,对传统的动静观尤其是宋明理学以静为本的主调进行了具有革命性的颠覆和重构:
“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张子正蒙注·大易篇》)。批判性地指出,运动(动)与静止(静)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或绝对本体(如无、理、心等)的属性,其承担者是作为宇宙唯一实体(“实有”)的“阴阳二气”本身。动静只是阴阳之气的两种状态表现。
“太虚本动”(《周易外传·系辞下传》第五章)。宇宙本体(“太虚”)就其本质而言,就是永恒运动着的物质性之气(“絪缊不息之本体”)。“太虚”并非王弼所谓的绝对寂静之“无”,而是内在蕴含着永恒运动机能的实在。“本动”二字斩钉截铁地确立了运动的绝对性与根本性。
“动极而静,静极而动……方动即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思问录·外篇》)。王夫之以精妙的辩证法剖析了动静的内在关系:运动发展到极点(“动极”)自然导向相对静止(“静”),静止积累到极致(“静极”)必然引发新的运动(“动”)。不仅如此,在运动的当下(“方动”)就内含着向静止转化的趋势和可能性;在静止发生的瞬间(“方静”)也同时包含着向运动转化的因子和动力。因此,静止之中本身就蕴含着(“含”)运动的因素,运动的过程同样无法舍弃(“不舍”)静止的因素。动静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依存,形成动态的辩证统一体。
“是静因动而得常,动不因静而载一”(《周易外传》卷二)。静止(“静”)的状态和形式,必须依赖于运动的变化发展才能得以确立(“得”)其相对的稳定性(“常”)。反之,运动(“动”)的存在(“载一”——承载其同一性),不依赖于静止作为根本前提(“不因静”),它自身就是最根本的存在形式。此论彻底打破了一切以静为终极基础的观点。
“废然无动而静,阴何从生哉!”(《思问录·内篇》)这是王夫之对其动静观的总结性、革命性断言:假如存在一个彻底、绝对的、没有丝毫运动成分的寂静状态(“废然无动而静”),那么作为对立面的“阴”(在阴阳动静对应中,“静”常与“阴”相联)将丧失其产生的动力源与生成依据(“何从生哉”)。这从根本上否定了“绝对之静”的现实可能性,确立了运动是宇宙万物存在的唯一根本方式,无动静无阴阳万物的根本论断。
结语:
纵观中国哲学史,从老子揭示“道”之动与万物归根之静的辩证统一,到《易传》崇扬变动不居的宇宙法则并赋予“寂感”一体的深层启示;从王弼将“静”赋予本体优先地位,到僧肇在佛理光芒下照见“即动求静”的般若之境;从周敦颐清晰区分物动神静,到朱熹以体用精义整合动静于理中却仍隐含张力;最终至王夫之气魄宏大、立场鲜明的“太虚本动”论,深刻完成向唯物主义辩证动静观的历史性复归——对“动静”范畴的思考与探索,已然成为中华先贤叩问宇宙本源、洞察存在特质、规范人生境界并建立系统学说的核心支点之一。
不同学派、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围绕“动静”构建的理论体系,不仅是抽象概念的推演,更是其整体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集中映射。其中,是否赋予动、静以本体或属性的地位,两者是辩证统一还是二元分离,或是以谁为主导力量,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深刻影响了关于世界本源(气理心物)、变化规律(常变)、人生态度(有为无为)、修养方法(主敬主静)乃至理想境界等几乎所有根本哲学问题的探讨。王夫之“动静者乃阴阳之动静”、“太虚本动”、“静含动、动不舍静”等论断,可谓终结了玄思、理思中割裂动静本体基础的倾向,其深邃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更是将动静关系的理解推向全新高峰,其彻底性与革命性成为中国古代动静辩证思想发展的光辉顶点。
这绵延数千年的智识结晶昭示我们:“动”与“静”——作为宇宙存在不可分割的两面——始终在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规定的永恒辩证运动中展现着存在的丰赡与深邃。它远非抽象思辨的游戏,而是根植于对世界本质的终极追问与人文关怀的永恒哲思。
参考文献: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史哲大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