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谷声里,太皇河沿岸的麦穗渐渐染上金黄,风过时,平原如巨大的金毯起伏,麦浪直铺天边。陈家庄的晒谷场早早被碾得平实如镜,只待新麦登场。
庄头李四站在河边高处,望着这片被陈之信陈老爷握在手中的七百多亩膏腴之地,轻轻吁了口气,二十余户佃农的汗水,即将在此归仓。
陈之信老爷踏着晨露出来,青绸直裰拂过沾着露水的草尖。他如今四十上下,面庞光润,这田庄所出,不过是他家当里寻常一隅。
城里三间绸缎庄、两处粮店的流水,足以让他在太皇河畔的隐居别墅里从容度日。此刻他穿过自家桑林,那沙沙叶响,也似算盘珠般清脆悦耳。
李四快步迎上,递过粗麻布巾让他擦手,又递上账本:“大哥,麦子割得七七八八了,新垦那五十亩薄地,头年种麦,收成稀稀拉拉,您看租子……”他小心觑着东家神色。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陈之信接过布巾擦了擦手,随意翻开账本,目光掠过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最终停在“新垦地”那一栏上。他指尖在粗糙的纸面上轻轻一叩:“新地,头年不易。按老规矩,熟地八斗,中地六斗,至于这新垦之地……”
他略一沉吟,仿佛在斟酌一粒麦子的分量,“四斗吧!”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定数。李四连忙应下,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东家手面宽,果然是太皇河一带出了名的。
收租的日子,晒谷场早早喧嚣起来。佃户们推着吱呀作响的独轮车,载着装满新麦的麻袋,如蚂蚁归巢般汇聚于此。沉甸甸的麦袋被卸下,堆在场边,空气里弥漫着新鲜麦粒干燥而踏实的香气,混着汗味和尘土的气息,是土地最本真的语言。
“王老五,熟地十亩!”司秤高声唱喝。王老五黑红脸膛笑开了花,忙不迭将金灿灿的麦子倒入大斗:“老爷恩典,李四哥照应,好年景啊!”斗里的麦子堆得冒了尖,司账的伙计拿起木制的“概”,贴着斗沿利落地一刮,刮平斗口,那多余的麦粒沙沙落回袋中,不多不少,整整十斗。
账房先生蘸饱墨汁,在册子上工整记下:“王老五,熟地十亩,收麦八石!”王老五看着自家的麦子倒入老爷的大仓,搓着手,脸上是如释重负的笑。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轮到赵老蔫,他推着中地的租麦,脸上带着庄稼人常有的、对老天爷既感激又敬畏的忐忑:“李四哥,您看这麦粒……”李四伸手插进麻袋深处,捞出一把麦子摊在手心,饱满的麦粒在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
“成色不差,老蔫实诚人!”赵老蔫家的麦子倒入斗中,刮平,记下中地租额八斗每亩,他那张被风霜刻满皱纹的脸上,紧张的神色才稍稍松弛。
最后是张老倔,他沉默地拖来新垦地的租子。麻袋解开,倒出的麦粒明显颜色黯淡,夹杂着不少干瘪的壳。司秤的伙计皱了眉,李四也蹲下身,捻起几颗瘪麦看了看,又抬眼望向张老倔那倔强又隐含不安的脸。
晒谷场上的喧闹似乎低下去几分,几道目光无声地投过来。李四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浮尘,声音不高却清晰:“新地薄,收成不易,瘪壳麦也是地里长出来的力气。倒吧,按数收!”张老倔紧绷的肩膀几不可察地松弛下去,低头默默看着自家的麦子哗哗流入大仓,记下了新地五斗的租额。
日头偏西,晒谷场上堆积如山的麦袋渐渐矮了下去,尽数归入陈家那几口深阔的仓廪。浓烈的、带着阳光温度的麦香从仓门里弥漫出来,沉甸甸地包裹着整个场院。李四捧着一本墨迹簇新的蓝布面账册,恭敬地递给正在桑树下坐着歇息的陈之信:“大哥,都收齐了,账目在此!”
陈之信“嗯”了一声,接过那册子,却并未立刻翻开。他微微侧首,目光投向那几座仓廪,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那新麦的醇厚香气都吸入肺腑。半晌,他才用指腹摩挲了一下账册粗砺的蓝布封面,缓缓掀开。纸页翻动发出细微的窸窣声,一行行墨字整齐排列: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陈家田庄 一十七年夏 麦租总账:
一、熟地
亩数:三百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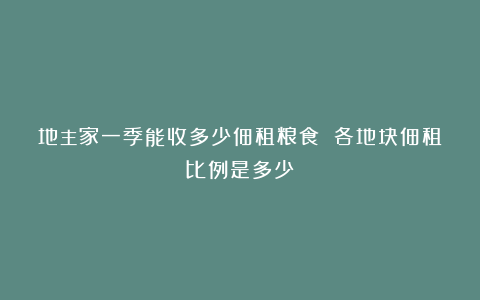
租额:每亩收麦八斗
实收麦:二百四十石整
佃户:王老五(十亩)、刘大(十五亩)……等八户
二、中地
亩数:三百亩
租额:每亩收麦六斗
实收麦:一百八十石整
佃户:赵老蔫(十二亩)、孙二(十八亩)……等九户
三、新垦地
亩数:一百亩
租额:每亩收麦四斗
实收麦:四十石整
佃户:张老倔(二十亩)、吴三(十五亩)……等三户
四、河滩荒地(本年免租)
亩数:五十亩
佃户:钱老七等
总计:实收麦:四百六十石整
李四垂手侍立一旁,低声道:“新垦地和河滩地,按大哥的吩咐,都减了收成。尤其是那钱老七,河滩地沙性大,今年头回试种,苗都稀稀拉拉,大哥恩典全免了租子,他感激得直磕头……” 李四顿了顿,声音里带着点不易察觉的试探,“只是……新垦地那五成租,张老倔家那麦子成色……终究是差了些!”
陈之信的目光仍落在账册末尾那“四百六十石整”几个墨字上,手指轻轻地划过那坚硬的纸面。晒谷场彻底安静了,只余下归巢鸟雀在桑树枝头零星的啁啾。佃户们早已散去,唯有河滩地方向,隐约传来钱老七家方向一两声压抑不住的、欢喜的叹息。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嗯!”陈之信终于合上了账册,那声轻微的“啪嗒”在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他抬眼,望向仓房那黑洞洞的大门,里面新麦的气息依旧浓郁而安稳地流淌出来。
“新麦入仓,最怕湿热捂了气。”他站起身,蓝布直裰的下摆拂过微温的土地,“告诉看仓的老赵,头半个月,每日后晌记得把仓板门打开半扇,透透气!”
他不再看那账册,信步向宅院走去。李四捧着那本蓝布面的册子,看着东家从容的背影融入暮色渐起的桑林小径。太皇河水在不远处汤汤流淌,声音浑厚而绵长,如同这片土地沉稳的脉搏。
新麦的香气,混合着河水的湿润气息,无声地弥漫开来,笼罩着平原,笼罩着仓廪,也笼罩着那些刚刚交罢租、炊烟正次第升起的佃户屋舍。
账簿封面的蓝粗布纹理在夕照下泛着幽微的光,内页的墨迹早已干透。那四百六十石新麦,连同河畔的晚风与渐起的暮色,一同沉入陈家庄安稳的仓廪深处,那是土地与时光本身的分量,无声无息,却足以承载起又一个丰稔的年份。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