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皇河街的风里,总是裹着水腥气与尘土味。陈记石料厂那面斑驳的土墙上,一张新贴的告示被风掀得哗啦作响。“转让石料厂”几个浓墨大字,刺眼地贴在那里,像一道新鲜的伤疤。
消息像河滩上的水鸟,扑棱棱飞遍了街巷。人们围在告示前,摇头咂嘴:“啧,陈掌柜那厂子,县衙欠的可是上千两的窟窿,谁耗得起?”“石料这行当,看着红火,骨头缝里榨油,难哪!”议论声嗡嗡的,汇入太皇河永不停歇的呜咽里。
消息自然也钻进了王世昌的耳朵。这位靠着精明算计在太皇河街立住脚的大财主,正歪在自家厅堂那张宽大的太师椅上,眯着眼,慢条斯理地捻着一串油光水亮的紫檀佛珠。他听着伙计禀报,捻佛珠的手指蓦地一顿,眼皮掀开一条缝,眼珠里掠过一道光。
“县衙欠着上千两?”他低声重复着,嘴角不自主地向上扯了扯,一个念头像河里的水泡,咕嘟冒了出来,越来越大,越来越亮。他猛地坐直身体,佛珠也不捻了,胖手一拍大腿:“嘿!这哪里是窟窿?这分明是座金矿!等着人去挖!”
那笔县衙欠款,在别人眼里是烫手的山芋、无底的深坑,在他眼中,却成了明晃晃、沉甸甸、唾手可得的银子。他几乎能听到铜钱叮当作响的美妙声音。可转念一想,这矿脉虽好,也得有趁手的家伙事去掘开,光凭他王世昌,恐怕还差那么点分量。
他立刻想到了一个人,丘世裕。丘家是太皇河两岸数得着的大地主,丘世裕虽然纨绔但精明,更关键的是,丘世裕的族叔丘尊龙,正是县衙里手握实权的巡检!王世昌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仿佛已看到那白花花的银子正淌进自家库房。他不敢耽搁,立刻吩咐备轿,直奔丘家那气派的青砖大院。
丘世裕正翻看着自家粮行的账册,听闻王世昌急匆匆地来了,有些意外。两人在书房坐定,王世昌开门见山,把陈记石料厂和县衙那笔欠款的事一说,又特意点明:“丘贤弟,你族叔丘巡检在县衙说话可是响当当的!这事儿啊,非老弟你出马不可!咱俩联手盘下那石料厂,等于盘下了一张县衙的欠条!这钱,别人要不回来,对你族叔来说,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他唾沫横飞,描绘着那笔唾手可得的巨利,眼睛发亮。
丘世裕听着,手指轻轻地敲打着红木书案。他虽不缺钱,但白捡的便宜谁不喜欢?尤其是想到族叔丘尊龙那张威严的脸,县衙里谁敢不买几分面子?这买卖,听着确实只赚不赔。他沉吟片刻,缓缓点头:“王兄说得在理。这陈秋生也算时运不济,该着这笔钱落到咱们兄弟手里。我看,可行!”
买厂需要本钱,丘世裕虽家大业大,但银钱出入,尤其大额,向来要过少夫人祝小芝的手。这位少奶奶心思细密,管着丘家的账房。当晚,丘世裕便把盘算好的事向祝小芝说了。
祝小芝正对镜梳理一头乌发,闻言,手中的玉梳停住了。她转过身,烛光映着她清秀的眉目,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世裕,这账本……毕竟是陈掌柜的血汗钱,县衙欠着,他才落到今日这般田地。我们接手,等于捡了他的漏,这……”她顿了顿,声音柔和却坚定,“价钱上,莫要太刻薄了人家。都不容易!”
丘世裕一怔,随即笑道:“芝妹就是心善。放心,我丘世裕也不是那等落井下石的小人,总归让他过得去便是!”他答应了祝小芝,买价上会“公道”些。
得了丘世裕的准信,王世昌心中大定。具体操办买卖的事,他交给了自家商队里最得力、也最精明的管事张栓子。张栓子二十岁,一张秀气的脸,透着生意人的油滑与干练。他得了王世昌和丘世裕的授意,揣着二百两银票,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踏进了陈秋生那间货行的小账房。
陈秋生形容枯槁,比前些日子更显憔悴。他看着张栓子递上来的银票,那“二百两”的字样刺得他眼睛生疼。这价钱,连他石料厂那些笨重工具和堆积的边角料都未必值回,更别提那本承载了巨大亏空和无数血汗的账册。
他嘴角抽搐了一下,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砂石堵住。窗外细雨沙沙,敲打着瓦片,也敲打着他破碎的心。半晌,他那只握惯了算盘和铁钎的手,微微颤抖着,终于还是伸出去,接过了那张轻飘飘却又重逾千斤的银票。
另一只手,则缓缓将桌上那本边角磨损、墨迹深重的旧账本,推了过去。账本封皮上那暗红的“陈记”二字,仿佛凝固的血迹。他闭上眼,挥了挥手,示意张栓子可以走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背影,仿佛瞬间被抽走了最后一丝生气。
张栓子拿到账本,如同拿到了打开金库的钥匙。王世昌和丘世裕立刻行动。丘世裕亲自登门拜访了族叔丘尊龙。丘巡检在自家花厅接待了侄儿,听明来意,目光扫过丘世裕身后王世昌那张堆满笑容的脸,又落在张栓子恭敬呈上的、那本熟悉的陈记账册上。
他蒲扇般的大手摩挲着下巴,发出粗粝的沙沙声,随即洪钟般地大笑起来:“哈哈哈!好!世裕啊,这陈秋生做事拖泥带水,要个账都畏畏缩缩!如今你们接手,这账目清晰,又是为公家事出力,岂有拖欠之理?包在叔身上!”
另一边,王世昌也没闲着。他深知夫人刘芸与少夫人祝小芝交好,而祝小芝曾对刘主薄的女儿刘玉梅有过不小的恩惠。从前刘玉梅重病,是祝小芝出面从南京请到了太医的方子,从而治愈了刘玉梅。
王世昌便让刘芸带着几匹上好的苏杭软缎和一支精巧的赤金点翠步摇去拜访祝小芝,委婉提及请她“玉成”石料厂欠款之事。祝小芝看着那些贵重礼物,又想到丈夫和王世昌的谋划,心中明白,这步摇最终会插在刘玉梅的发髻上。
她轻轻叹了口气,终究还是写了张便笺,让贴身丫鬟小蝶送到了刘主簿府上,只说是“问候玉梅妹妹近安”,并未提钱款半个字。
然而,刘主薄是何等玲珑剔透的人?接到丘巡检那边递来的话头,又见丘家少夫人送来这含而不露的“问候”,那张圆润白净的脸上立刻堆满了心领神会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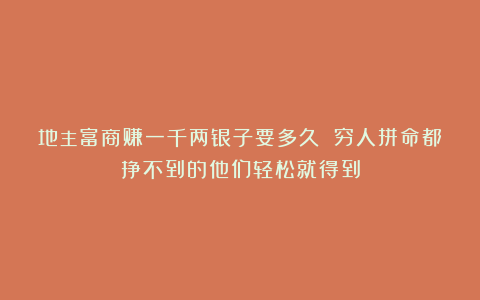
他捻着几根稀疏的胡须,对前来“拜会”的王世昌和张栓子打着官腔:“哎呀,陈记……哦不,现在是丘王记石料厂这笔款项嘛,关乎防汛大计,下官早已报请县尊大人,列为头等要务!无奈库银一时周转……不过二位放心!有丘巡检督促,下官定当竭力斡旋,尽快拨付,尽快拨付!”
他拍着胸脯,话说得滴水不漏,那笑容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真诚”了几分。
果然,两个月不到,一千一百两白花花的官银,便由县库拨出,一分不少地交到了丘世裕和王世昌手上。丘、王二人心照不宣,各自取出一百两足色纹银。
丘世裕亲自送到了族叔丘尊龙府上,言明是“孝敬叔父操劳茶水”。丘尊龙掂了掂那沉甸甸的银包,满意地哈哈大笑,拍着侄儿的肩膀连说“好小子”。
王世昌则让张栓子包好另一份,悄悄塞给了刘主簿府上的心腹长随。刘主薄摸着那包银子,圆脸上的笑容愈发“和煦”,只觉这太皇河的秋风都透着股暖洋洋的甜意。
除去打点的二百两和买厂的二百两,短短三个月,七百两净利便如同太皇河水般,稳稳流入了丘、王两家的库房。那曾经让陈秋生焦头烂额、夜不能寐的千两巨款,在丘巡检的豪迈和刘主簿的“斡旋”下,竟解决得如此轻描淡写,顺理成章。
丘世裕和王世昌在“海天楼”推杯换盏,脸上是掩不住的春风得意。至于那刚到手还没捂热的石料厂?两人早已抛在脑后。丘世裕忙着去府城物色新式家具,王世昌则把心思都放在了刚谈妥的一批南货上。
那石料厂,连同里面蒙尘的工具、散乱的石料、空荡荡的工棚,仿佛成了一件穿完就扔的旧衣裳,被随意地遗忘在太皇河喧嚣的河风里。
然而,有人并未忘记。一日午后,祝小芝带着丫鬟,乘轿路过石料厂旧址。轿帘被风微微吹开一角,她无意间瞥见那巨大的采石场。曾经叮当作响、人声鼎沸的地方,如今一片死寂。
荒草在石缝间疯长,几架废弃的轱辘车歪倒在泥地里,锈迹斑斑。几只野鸟在空旷的工棚顶上跳跃鸣叫,更显凄凉。风吹过空荡的场院,呜呜作响,像是在哀叹。
祝小芝的心,像是被那荒凉狠狠揪了一下。这厂子,曾是陈秋生半生心血,也曾养活了数十个壮劳力及其家小。如今成了丘王两家赚快钱的工具,用过即弃,荒芜至此,实在可惜,更是不该。
她回到府中,心绪难平。傍晚,她径直去了王世昌家。王夫人刘芸正在窗前绣花,见祝小芝神色凝重地来访,有些意外。祝小芝坐下,也不客套,指着石料厂的方向,开门见山:“芸妹妹,那厂子荒着,我看着心里实在难受。风吹雨淋,好好的东西都糟蹋了。陈掌柜当初那些伙计,听说日子也艰难!”
刘芸放下绣绷,她是个温婉妇人,素知祝小芝心善。想起丈夫王世昌提起石料厂时那满不在乎的神情,再听祝小芝这么一说,也觉得那偌大的产业荒废着确实可惜,还白白惹人闲话。她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可那地方……世昌和你家丘少爷,心思都不在上头了。这重新开张,本钱、人手、销路,千头万绪的……”
“本钱我们两家凑一凑,总能支撑起来。销路?”祝小芝目光清澈而坚定,“太皇河年年水患,官府年年修堤,石料总是要的。至于人手,”她顿了顿,“陈掌柜当初辞退的那些老伙计,都是熟手,如今散在各处打零工,生计艰难。若能请回来,他们必定尽心尽力。”她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量。
刘芸看着祝小芝认真的神情,也被打动了。她想起自家库房那刚入库的、沉甸甸的银子,其中一大半,正是从那石料厂“生”出来的。她点点头:“姐姐子说得对。荒着是败家,用起来才是正理。回头我就跟世昌说,这事儿,我们姐妹俩牵头来办!”
祝小芝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释然的笑意。
几天后,丘王记石料厂那扇紧闭多日、落满灰尘的大门,吱呀一声被重新推开。这次来的,不是投机取巧的商人,而是两位衣着素雅的夫人。祝小芝和刘芸亲自带着管事,走进了这片荒芜之地。
她们指挥着雇来的短工清理杂草,整修坍塌的工棚,给锈蚀的工具上油。最重要的,是派人四处寻访那些被陈秋生无奈辞退的老伙计。消息像长了翅膀,老石匠赵五正在几十里外的一个小采石场背石头,脊背佝偻得更厉害了。
当他听说丘王记石料厂要重新开张,东家夫人亲自来请他们这些旧人回去,工钱还比从前涨了一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那张如同风干橘皮般的脸上,浑浊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亮光。其他散落在各处打短工、扛大包的老伙计们,也陆陆续续被寻了回来。
当赵五和几个同样苍老却依旧硬朗的石匠,重新站在熟悉的采石场上,抚摸着那些冰冷的、久违的巨大青石时,粗糙的手指都在微微颤抖。阳光炽烈,照耀着他们黝黑脸庞上深刻的皱纹,也照亮了眼中那份失而复得的、沉甸甸的踏实。不知是谁,试探着拿起了一把沉甸甸的大锤,高高抡起,又重重落下!
“咚!”
一声闷响,如同沉睡的心脏重新搏动。锤头狠狠砸在钢钎上,发出清脆的撞击声,钢钎下的巨石应声裂开一道白痕。这声响,打破了太皇河畔长久的死寂,惊飞了荒草丛中栖息的野鸟。
“嗬!”赵五嘶哑地吼了一声,仿佛要把胸中积压的浊气全数吐出。他布满老茧的手紧紧握住锤柄,又是一锤砸下,力量带着一种近乎悲壮的宣泄。其他几个老伙计也如梦初醒,纷纷抄起熟悉的家伙什儿。
叮叮当当的凿石声,低沉有力的号子声,再次在这片空旷的河滩上响了起来。虽然人比从前少了许多,声音也略显苍凉,但那节奏,那力量,却重新灌注了这片土地的生机。
祝小芝和刘芸站在不远处的坡上,静静地看着。刘芸轻轻摇着团扇,低声道:“这声音……听着倒是踏实!”祝小芝没有回答,目光投向更远处奔流的太皇河。风扬起她的裙角,也带来了石料厂新生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