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迟迟不肯降临六月的重庆。6月7日下午五时许抵渝,安顿停当后外出晚餐,解放碑一带已是华灯初上。
这座山城的夜色来得格外矜持,直到近八点,天才真正暗下来。
二十年光阴流转,解放碑商圈早已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那座记录抗战胜利的碑体依然庄严肃穆,但四周低矮的商铺已化作摩天大楼的森林。
玻璃幕墙折射着夕阳余晖,Gucci、Louis Vuitton的橱窗里,奢侈品在精心设计的灯光下熠熠生辉。
有趣的是,碑体周围自发形成的圆形广场上,依然聚集着拍照的游客和摇着蒲扇纳凉的本地老人,新与旧在这里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路过国泰艺术中心时,我不禁驻足。这座由加拿大BTA设计事务所打造的建筑,像一堆随意摞起的红色积木,又似传统中国建筑的斗拱结构的现代表达。
黑红两色的钢管以看似无序的方式交叉叠放,在黄昏中投下错综复杂的阴影。
跨过一座钢结构的天桥,眼前景象忽然一变——人声鼎沸处,便是洪崖洞了。
初见洪崖洞,竟不知如何定义它。说是景区,却分明是座活色生香的商业城;说是商场,又带着千年巴渝的历史风骨。
这座依山而建的11层建筑群,灯火通明地矗立在嘉陵江畔,恍若一座垂直的市井。
战国时期的巴人,大约是最早懂得与这片山水谈判的民族。他们发明了吊脚楼——这种半悬空的建筑,是对陡峭地形的温柔妥协。
洪崖洞的设计灵感正源于此,它将传统吊脚楼的智慧放大成了一个建筑群落。
走在其中,常有恍惚之感:明明身处高楼,却见脚下仍有数层灯火;以为到了地面,仰头却见更多楼阁悬于头顶。
这种空间错觉,恰是重庆这座立体城市的最佳隐喻。
下到滨江,人声鼎沸。挤满了观景的游客。
有的眺望江景。有的观览洪崖洞的璀璨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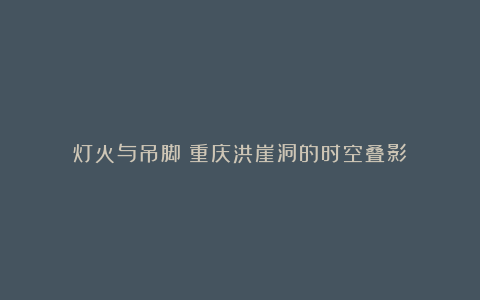
嘉陵江大桥一侧摆满了各色摊位,商贩吆喝声与游客谈笑混作一团。卖冰粉的老妪、烤苕皮的中年汉子、现场制作酸辣粉的姑娘,他们的面容在霓虹灯下忽明忽暗。
我想起北宋范成大《吴船录》中描写渝州(今重庆)的句子:”民居皆依山而阁,参差如燕巢。”
八百余年过去,重庆人依然保持着这种”燕巢”式的生活智慧,只不过木结构的吊脚楼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洪崖洞,不变的却是那种与山共舞、与水相依的城市精神。
二十年前初访重庆,记忆中的解放碑还带着几分朴素。那时的国泰大剧院还是苏联式的方正建筑,周边多是卖麻辣烫和小面的摊贩。
如今的洪崖洞,则像是一个微缩版的重庆——火锅店里翻滚的红汤、茶馆中清脆的麻将声、特产店铺陈列的怪味胡豆与合川桃片,还有那些站在观景台上举着自拍杆的年轻人,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代版的《清明上河图》。
在滨江道,回望洪崖洞全貌,更觉震撼。整座建筑如一座发光的山体,层层叠叠的灯光将巴渝传统建筑语汇解构又重组。
最妙的是那些看似随意悬挂的红灯笼,远观竟组成了一条蜿蜒的光带,宛如一条火龙盘踞山间。
这让我想起清代张问陶《重庆》诗中的描绘:”城郭生成造化镌,如麻舟楫两崖边。”当年的诗人若见今日洪崖洞夜景,不知会写下怎样惊叹的诗句。
洪崖洞的魔力,在于它完美调和了历史与当下。11层楼中,既有展示川剧变脸、蜀绣制作的传统艺术区,也有售卖网红奶茶、文创产品的时尚店铺。
夜渐深,人流却不减。千厮门大桥的灯光倒映在嘉陵江上,与洪崖洞的辉煌相映成趣。
江面游船驶过,掀起的水波将那些光影揉碎又重组,恰似这座城市不断被改写又始终保持本真的历史。
我突然明白,洪崖洞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它的建筑奇观,更在于它成功地将市井生活升华为了一种美学体验。
在这里,吃一碗小面不再是单纯的果腹,而成为参与山城日常的仪式;买一把剪纸不只为留念,而是触摸巴渝文化的脉络。
离开时已近午夜,洪崖洞依然灯火通明。回望这座不夜的山城建筑,想起《华阳国志》中记载巴人”勇锐歌舞”,今日重庆人的热烈与坚韧,或许正是这种古风的延续。
二十年间,解放碑长高了,国泰剧院变身了,但骨子里那份与山水共生的智慧、那份将平凡日子过成节庆的能耐,却愈发鲜明。
洪崖洞恰如一面棱镜,将重庆的过去与现在、市井与高雅、本土与世界,折射成了令人目眩神迷的光谱。
这一夜,我在解放碑的时尚光影与洪崖洞的市井烟火间,读懂了重庆的某种本质——它永远在攀登,却又始终扎根于自己的山水;它拥抱变化,却从未真正离开过那些吊脚楼里的古老智慧。
洪崖洞的灯火,照亮的不仅是一处景点,更是一座城市与时光对话的方式。
2025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