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我们迎来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 1925-1995)诞辰一百周年,这位法国哲学家的思想仍以其非凡的活力激荡着当代理论界。在这个特别的纪念年份,’图像之书‘特别策划了“德勒兹100年”专题,呈现德勒兹电影理论的多重面向:从他对运动与时间的深刻洞见,到他如何理解影像与思想的关系;从他对战后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的分析,到他与其他电影理论家的对话与争辩。通过这些文章,我们不仅回顾德勒兹的理论贡献,也探讨他的思想如何继续影响当代影像创作与理解,特别是在数字技术和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
文献说明
这首曲子属于Pinhas的’德勒兹系列’作品,通过层叠的合成器音色、循环结构和非线性发展来音乐化德勒兹的哲学概念。作品中你能听到多重音轨的重叠与交织,创造出一种’音响织物’,这与德勒兹关于多元性和’生成'(becoming)的哲学理念相呼应。音乐中没有传统的旋律-和声进行,而是创造了一种声音的’平滑空间'(smooth space)。作品标题中的’Hyperion’既指向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神,也暗示了超越性和变异的可能,而’Beyond’则可能暗示了德勒兹思想中不断超越既定范畴的特质。
本文字数7908,阅读预计需要18分钟。
关于运动–影像
(1983)
吉尔·德勒兹 / 文 李洋 / 译
提问:您的书并非一部电影史,而是一部关于影像(images)和符号(signes)的分类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您之前一些作品的延续。例如您曾对普鲁斯特作品中的符号进行过分类。但在《运动–影像》(L’image-mouvement)中,您第一次决定要解决的不再是哲学问题或某个特定的文化(如斯宾诺莎、卡夫卡、培根或普鲁斯特的文化),而是一个整体领域——即电影。与此同时,尽管您拒绝将其视为一部历史著作,但您仍然以历史的视角来审视它。
德勒兹: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的确是一部电影史,但它是一部“自然史”。就像我们对动物进行分类一样,它也是对影像类型和相应标志的分类。那些主要的类型片,如西部片、犯罪片、历史片、喜剧片等,不能说清影像的类型或其内在特征。另一方面,镜头、特写镜头、长镜头等,已经被确定了类型。但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光线、声音和时间。如果我将电影领域视为一个整体,那是因为它建立在运动–影像的基础上。因此,它能够揭示或创造最大数量的不同影像,尤其是通过蒙太奇将它们组合在一起。这里有知觉–影像(images-perception)、动作–影像(images-action)、情感–影像(images-affection),还有更多其他的影像。每次,这些影像都有其内在的符号,从其起源和构成的角度来描述其特征。这些符号并非语言符号,即使涉及声音符号也是如此。像皮尔斯这样的逻辑学家的重要性在于,他对符号进行了极其丰富的分类,且相对独立于语言模式。这让我更想看看电影是否带来了一种移动的材料,以致于需要对影像和符号有新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试图写一本逻辑学的书,一本电影的逻辑学。
提问:此外,您似乎还想弥补哲学对电影的某种不公。尤其是,您批评现象学误解了电影,通过将电影与自然感知进行比较和对比,贬低了电影的重要性。您认为柏格森已经完全理解了电影,甚至已经预料到了电影,但却无法或不愿认识到自己的观念与电影的交汇点。在他与这门艺术之间,仿佛存在着某种追逐。在《物质与记忆》(Matière et mémoire)一书中,他在对电影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提出了“运动–影像”这一基本概念,以及运动–影像的三种主要形式:知觉–影像、动作影像、情感–影像。这些内容预示了电影的创新性。然而,在《创造进化论》(L’évolution créatrice)中,这一次他真正面对了电影。他对电影提出了质疑,但质疑的方式与现象学家完全不同:他认为电影与自然感知一样,都是一种古老幻觉的延续,即认为运动可以通过固定的时间切片重组起来。
德勒兹:这非常奇怪。我觉得现代哲学的“想象”(imagination)概念并没有将电影考虑在内:要么它们相信运动但压制影像,要么它们保持影像但压制运动。奇怪的是,萨特在《论想象》(L’imaginaire)一书中考虑了所有类型的影像,唯独没有考虑电影影像。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对电影很感兴趣,但他将电影与感知和行为的一般条件对立起来。柏格森在《物质与记忆》中的处境是独特的。或者说,《物质与记忆》在柏格森的作品中是一本独特而非凡的著作。一方面,他假定运动、物质和影像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他又发现了一种时间——这种时间是所有时间层次的共存(物质只是最低层次)。最近,费里尼曾说,我们同时是童年、壮年和老年,这就是柏格森式的。因此,我们在《物质与记忆》中看到了纯粹精神主义与激进唯物主义的结合。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说维尔托夫和德雷尔同时出现在这两个方向上。但柏格森不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放弃了关于“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的这两个基本进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认为这是因为柏格森正在发展与相对论相关的新的哲学概念:他认为相对论隐含着一种时间概念,但这个概念本身并不能揭示时间,而应该由哲学来建构。只是人们误以为柏格森是在攻击相对论,是在批评物理学理论本身。柏格森认为这种误解过于严重,无法消除。因此,他回到了一个更简单的概念。事实上,在《物质与记忆》一书中,他描绘了一个运动–影像和一个时间–影像,这些影像后来可能进入了电影。
提问:这不正是我们在德莱叶这样的导演身上发现的吗?他在您的书中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最近又看了《葛楚》(Gertrud),这部影片将在二十年后重新上映。这是一部精彩的电影,其中对时间层次的调节达到了只有沟口健二的电影才能达到的精致程度(例如《雨月物语》结尾处陶瓷匠的妻子死而复生式的隐身与显现)。德莱叶在他的《著作集》(Écrits)中不断提到,我们必须摒弃三维,即深度,转而制作平面影像(images planes),以便将其与第四和第五维度——时间和精神——直接联系起来。例如《词语》(Ordet)的奇特之处在于,他明确指出这不是关于鬼故事或痴呆症,而是关于“精确科学与直觉宗教之间的深刻关系”。他还引用了爱因斯坦的话,我引用一下:“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后,新科学已经证明,在我们感官的三维世界之外,还存在着第四维度——时间维度,以及第五维度——心灵维度。我们已经证明,体验尚未发生的事件是可能的。我们开辟了新的视角,使我们认识到精确科学与直觉宗教之间的深刻关系。”……让我们回到“电影史”的问题上,您讨论了“连续性”(successions),比如战后您说这样或那样的影像出现在这样或那样的时刻。因此,您不仅仅是在进行抽象的分类,甚至也不是在进行自然的历史分类,您还需要考虑历史的运动。
卡尔·西奥多·德莱叶
Carl Theodor Dreyer
德勒兹:首先,影像类型显然不是预先存在的,它们必须被创造出来。平面影像,或者相反,景深,每次都必须被创造和再创造。如果你愿意的话,符号总是指向一个签名。因此,对影像和符号的分析必须包括那些重要作者的著作。让我们举个例子,在我看来,表现主义就是在光明与黑暗的关系中构想光明的,而这种是一种斗争关系。战前法国学派则截然不同:没有斗争,而是交替。不仅光本身在运动,而且有两种交替的光——太阳光和月亮光。这非常接近画家德劳内(Delaunay)[1] 的风格。这是反表现主义(anti-expressionnisme)[2] 。如果说今天像里维特(Rivette)这样的作家隶属于法国学派,那是因为他重新发现并彻底更新了这种双光主题。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令人惊叹。他不仅接近德劳内,而且在文学上也接近奈瓦尔(Nerval)[3] 。他是最接近奈瓦尔的电影人,也是唯一的奈瓦尔式电影人。在所有这些中,显然有贯穿电影的历史和地理因素,这些因素使电影与其他艺术相接触,使电影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同时也(向其他艺术)施加影响。这就是一部完整的历史。然而,在我看来,这段影像史并没有发展。我认为,所有影像都以不同的方式结合了相同的元素、相同的符号。但任何组合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随意出现:一个元素要得到发展,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否则它就会萎缩,或者变得次要。因此,发展是有层次的,每个层次都尽善尽美,而不是后代或分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谈论“自然史”,而不是“历史的历史”。
提问:你的分类同样也是一种评价。它意味着对你所选择的作者的价值判断,因此也意味着对你勉强提及或未提及的作者的价值判断。这本书无疑宣告了续集的到来,它让我们站在了超越“运动-影像”本身的“时间-影像”的门槛上。但在第一卷中,您描述了二战末期和二战之后的动作-影像的危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等),您所描述的这场危机中的电影的某些特征——承认现实的不完整性和分散性,一切都成为陈词滥调的感觉,主次之间的不断变化,情节的奇妙衔接,打破特定情境与人物行动之间的简单联系,难道不是已经出现在两部战前电影《游戏规则》和《公民凯恩》中吗?这两部电影被认为是现代电影的奠基者,但您却没有提及。
德勒兹:首先,我并没有声称自己有什么发现。我提到的所有作者都非常有名,我也非常钦佩他们。例如从专著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罗西(Losey)[4] 的世界可以被定义为一个高高的平崖:上面栖息着大鸟、直升机和令人不安的雕塑,下面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小城市。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有一条坡度更大的线。这是罗西为自己的目的重新创造自然主义坐标的方式。这些坐标也可以在施特罗海姆(Stroheim, 1885-1957)[5] 和布努埃尔(Buñuel)的作品中以另一种方式找到。从整体上看待一部作品,我不认为一部伟大的作品会有什么问题。对于罗西来说,《鳟鱼》(La Truite)甚至被手册派们(les Cahiers)误解了,因为这没有被放回到作品的整体背景中。这是一个新夏娃。所以你说存在一些洞,威尔斯(Welles)、雷诺阿(Renoir),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作者。只是我无法在这卷本考虑他们所有的作品。在我看来,雷诺阿的作品以某种戏剧与生活的关系为主导,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实在影像(image actuelle)与潜在影像(image virtuelle)的关系。在我看来,威尔斯是第一个构建了直接的时间–影像(image-Temps directe)的人,这种时间–影像不再是简单的运动结果。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雷奈(Resnais)也是紧随其后。但在这第一卷中,我无法讨论这些例子,但我可以谈论整个自然主义。即使是新现实主义和“新浪潮”,我也只能是在最后才谈到最表面的内容。
提问:您最感兴趣的似乎是自然主义和唯灵论(一方面是布努埃尔、施特罗海姆、罗西,另一方面是布莱松和德莱叶),也就是说,要么是自然主义的堕落和退化,要么是精神、第四维度的推动和崛起。这些都是纵向运动。您似乎对横向运动、动作序列不那么感兴趣,例如在美国电影中。当您谈及新现实主义和新浪潮时,您有时谈到动作-影像的危机,有时谈到整个运动-影像的危机。在您看来,是整个运动-影像陷入了危机,为超越运动本身的另一种影像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还是只剩下动作-影像,让运动-影像的其他两个方面——感知和纯粹情感——继续存在,甚至得到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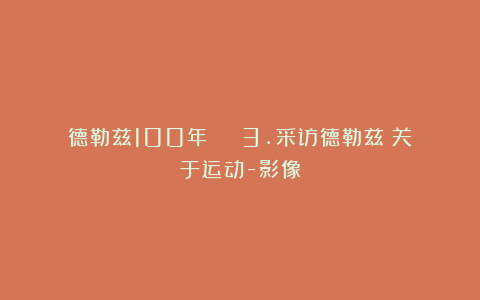
德勒兹:仅说现代电影打破了叙事性是不够的,这只是结果,原理还在别处。动作电影(cinéma d’action)揭示的是感知–动作情境(situations sensori-motrices):在某种情境中,人物根据他们的感知采取行动,有时是非常激烈的行动。行动源于感知,感知延伸为行动。现在,假设一个角色发现自己处于一种日常或特殊的情境中,这种情境压倒了所有可能的行动,或者让他毫无反应。它太强烈、太痛苦,或者太美了,于是感官与运动的联系就中断了。他们不再处于感知–运动的情境中,而是处于纯粹的视听情境中。这是一种不同的影像。以《火山边缘之恋》(Stromboli)中的外来女人为例,她经历了捕捞金枪鱼、金枪鱼的痛苦,然后是火山爆发。她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回应,因为太强烈了:“我完了,我害怕了,多么神秘,多么美丽,我的上帝……”再如《一九五一年的欧洲》(Europa’51)中工厂前的资产阶级妇女:“我以为我看到了死刑犯……”我认为,这就是新现实主义的伟大发明:我们不再那么相信对情境采取行动或对情境做出反应的可能性,但我们一点也不被动。我们甚至在最日常的生活中也能抓住或揭示一些无法容忍、难以忍受的东西。这是一部通灵者(Voyant)的电影。正如罗伯–格里耶(Robbe-Grillet)所说,描述取代了对象。但是,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纯粹的声光情境中时,崩溃的不仅仅是动作和叙事,还有本质上发生变化的感知与情感,因为它们进入了一个与“经典”电影的感知–运动系统完全不同的系统。此外,这也不再是同一类型的空间:失去了运动联系的空间变成了一个断开或空洞的空间。现代电影构建了非同寻常的空间;感知–运动符号让位于“光符号”(opsignes)和“声音符号”(sonsignes)。当然,运动始终存在。但是,整个运动–影像才是问题所在。在这里,很明显,新的光学和声音影像指出了战后出现的外部条件(变化),哪怕只是被拆除或废弃的空间,取代行动的所有形式的“游荡”(ballade),以及随处可见的难以忍受的爬坡。
提问:您对语言学以及受语言学启发的电影理论持批判态度。然而,您却说影像变得“可读”而非“可见”。然而,“可读”一词应用于电影,在语言学统治时期风靡一时(“阅读电影”、电影的“解读”……)。您使用这个词难道不会造成混淆吗?您的“可读影像”一词是否涵盖了语言概念之外的东西,或者它是否又把您引回了语言概念?
德勒兹:不,似乎没有。将语言学应用于电影的尝试是灾难性的。的确,像麦茨(Metz)和帕索里尼(Pasolini)这样的思想家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批评工作。但他们对语言学模式的引用最终表明,电影是另一种东西。如果它是一种语言,那也是一种类比的语言或调节的语言。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对语言模式的引用是一种转移视线的做法,最好不要这样做。在巴赞最优美的文章中,有一篇是这样解释的:摄影是一个模子,一个铸模(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语言也是一个模子),至于电影整体就是调制(modulation)。不仅仅是人声,还有声音、灯光和动作都处在持续不断地调节中。作为影像的参照,它们被设定为变化、重复、闪烁、循环等等。如果说所谓的经典电影在这一方向上已经走得很远,那么电子影像(image électronique)则从两个角度实现了进化:大量增加的参数和对发散系列的建构,而经典影像则趋向于系列的聚合。这就是为什么影像的可见性变成了可读性。这里的可读性指的是参数的独立性和序列的发散性。还有一个方面与我们之前的评论有关,这就是垂直性问题。我们的光学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垂直姿态的影响。美国评论家列奥·斯坦伯格(Leo Steinberg)解释说,现代绘画与其说是由纯粹的光学平面空间定义的,不如说是由放弃垂直特权定义的:就好像窗户的模型被一个不透明的平面所取代,水平的或可倾斜的,上面刻有数据。这就是可读性,它并不意味着一种语言,而是一种类似于图表秩序(ordre du diagramme)的东西。这就是贝克特(Beckett)的公式:躺着比坐着好,坐着比站着好。现代芭蕾在这方面堪称典范:有时,最有活力的动作是在地板上进行的,而站着的时候,舞者会聚在一起,给人一种一旦分开就会摔倒的感觉。在电影院里,银幕可能只是名义上垂直,却起到水平或倾斜平面的作用。迈克尔·斯诺(Michael Snow)曾严肃批评垂直的特权,甚至为此制造了一个装置。伟大的电影导演就像音乐大师瓦雷兹(Varèse)[6] :他们必须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进行创作,但他们需要新的装置、新的乐器。这些工具在平庸的作者手中会空转,取代思想。相反,伟大作家的思想却需要这些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电影会因为电视或录像而消亡。每一种新媒介都对电影有用。
提问:这正是格劳贝尔·罗恰(Glauber Rocha)的最新影片《大地的年纪》(L’âge de la terre)的核心所在。然而,仅仅从“几何”和空间的角度来考虑电影,您是否忽略了一个具有专属于戏剧性的维度,比如从希区柯克或朗(Lang)等导演所处理的凝视问题中出现的维度?在希区柯克的作品中,你提到了一种类似“计谋”(démarque)的功能,似乎暗指凝视(regard)。但您的书中完全没有“凝视”这个概念,甚至这个词本身,这是有意为之?
德勒兹: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否必不可少。眼睛已存在于事物之中,它是影像的一部分,是影像的可见性。这就是柏格森所展示的:影像本身是发光的或可见的,它只需要一个“黑屏”,这个黑屏阻止它与其他影像一起向各个方向移动,阻止光的扩散,阻止光向各个方向传播,阻止光的反射和折射。“始终在传播的光永远不会被揭示……”眼睛不是照相机,而是屏幕。至于摄影机,由于它的所有命题功能,它更像是第三只眼睛,即心灵之眼。您提到了希区柯克的案例:诚然,他将观众引入了电影,正如特吕弗和杜谢(Douchet)[7] 所展示的那样。但这不是看的问题。相反,这是因为他用一整套关系网来构架动作。举例来说,影片中的行为是犯罪。但关系是另一个维度,在这个维度中,罪犯将自己的罪行“给予”他人,或者交换,或者还给他人。这正是罗默和夏布洛尔所擅长的。这些关系不是行为,而是只存在于心理上的象征性行为(给予、交换等)。而这正是摄影机所揭示的:摄影机的取景和移动体现了心理关系。如果说希区柯克是英国人,那是因为他感兴趣的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和悖论。对他来说,摄影机的取景框就像一个挂毯框:它承载着人际关系的经线,而动作则只是穿梭其间的纬线。因此,希区柯克引入电影的是心理影像。这不是看的问题,如果说摄影机是眼睛,那它就是心灵的眼睛。因此,希区柯克在电影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超越了动作–影像,走向更深层次的东西,即精神关系,一种千里眼。但他没有将此视为动作–影像的危机,更广泛地说,是运动–影像的危机,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完成,一种饱和。以至于,如果你愿意可称它为最后一个经典导演或第一个现代导演。
提问:对您来说,希区柯克是最杰出的关系电影导演,也就是您所说的“三元性”(tiercéité)电影导演。关系就是您所说的整体吗?这是您书中的一个难点。您从柏格森那里得到启发,说:“整体不是封闭的,相反,它是开放的,是永远开放的。封闭的是集合,所以不要混淆……”
Alfred Hitchcock
德勒兹:众所周知,“开放”是里尔克钟爱的一个诗学概念。但它也是柏格森的一个哲学概念。重要的是集合与整体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混淆了它们,整体就失去了意义,我们就会陷入著名的“集合之集合”的悖论。集合可以汇集多种多样的元素,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封闭的、相对封闭的或人为封闭的。我说“人为”,是因为总有一条线,无论多细,将整体与更大的整体连接起来,无穷无尽。但整体有不同的性质,它是时间的秩序:它贯穿所有的整体,恰恰是这一点阻止了它们实现自己的终极趋势。换句话说,阻止了它们完全封闭自己。柏格森曾说:时间是开放的,它是变化的,且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地改变自己的性质。它是一个整体,但它不是一个封闭的整体,而是从一个整体到另一个整体的永恒通道,是一个整体向另一个整体的转化。要思考时间与万物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非常难的,可恰恰电影让它变得容易。可以说,电影有三个并存的层次:景别(cadrage),即确定一个人为封闭的临时整体;剪切(découpage),即确定分布在整体元素中的一个或多个运动;但运动由此表达了整体的变化或变异,这就是蒙太奇的问题。整体贯穿所有的集合,阻止它们完全闭合。当我们谈及“画外空间”(espace off)时,我们指的是两件事:一方面,任何给定的集合都是二维或三维的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所有的集合都陷入了另一种性质的整体,即四维或五维的整体,而这个整体通过它所经过的集合,无论它们多么庞大,都不会停止变化。在一种情况下,它是空间和物质的延伸;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是精神的决定,就像德莱叶或布莱松那样。这两个方面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有时会偏重于其中一个方面。电影从未停止过对这两个并存层面的探索,每一位伟大的导演都有自己的方式来构思和实践这两个层面。在一部伟大的电影中,就像在任何艺术作品中一样,总有一些东西是开放的。每当你寻找它的时候,它就是时间,它就是整体,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电影中。
上下滑动查看
(1)此处应为法国画家罗伯特·德劳内(Robert Delaunay,1885-1941)。——译者注
(2)此处应为法国电影导演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 1928-2016)。——译者注
(3)此处应为法国诗人、作家热拉尔·德·奈瓦尔(Gérard de Nerval, 1808-1855)。——译者注
(4)此处应为英国电影导演约瑟夫·罗西(Joseph Losey, 1909-1984)。——译者注
(5)此处应为埃里克·冯·施特罗海姆(Erich von Stroheim, 1885-1957)。——译者注
(6)此处应为法国音乐家埃德加·瓦雷兹(Edgard Varèse, 1883-1965)。——译者注
(7)此处应为法国影评人让·杜谢(Jean Douchet, 1929-2019)。——译者注
扩展观看:沙丹谈策展人的主要工作
近期直播:
文字编辑 |郑博航
微信编辑 |沈思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