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9日 印度尼西亚·万丹
8月9日,考察团自雅加达包车前往万丹古城区(Banten Lama),考察当地的历史遗迹。16世纪立国的万丹苏丹国被认为是马六甲苏丹国衰落后,该区域新崛起的伊斯兰港市国家。至16世纪末、17世纪初,除华人、穆斯林商人在其国经商外,荷兰、英国商人也陆续造访万丹,并先后在当地设立商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建立据点后,与万丹形成商业竞争,双方时战时和。后续荷兰人利用军事优势渐次对万丹苏丹国的内政外交施加干预,并在胡椒贸易上攫取利益。至19世纪初的荷属东印度时期,巴达维亚当局对该国的干预已到了直接出兵抓捕苏丹的地步。一般认为,万丹国祚终于英军登陆爪哇后的1813年,当年万丹苏丹沙利欣二世(Salihin II,1810—1816年间在位)与代表英殖爪哇当局的莱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签订协议,割让其领地,此后沙利欣及其子虽保留苏丹名号,实已丧失权力(Ota 2005: 16-18, 145-146)。
考察万丹的第一站,考察团先到了国立万丹博物馆。对中国人而言,博物馆院内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门前一侧陈列的数方华人墓碑。这些墓碑出土于万丹的华人区(Pecinan),年代均为清中后期,年代最早的两方 是乾隆六十年(1795)平和人林赵官和同安裔的甲必丹林容斋的墓碑。从“甲必丹”职衔看,林容斋应是18世纪中后期当地华人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丹的华商早期多在万丹与各胡椒主产地间从事胡椒贩运,到18世纪下半叶,当地华人社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面临转型。据太田淳的研究,一方面,荷兰势力更深地介入了万丹政局,1760年代起,尽管VOC承认苏丹对万丹的主权,以换取苏丹提供稳定的胡椒供应,但荷兰人已开始通过万丹商馆长来干预苏丹宫廷的相臣任免并把控华人甲必丹的人选。另一方面,该时期由于海盗劫掠和英商的介入,万丹以往作为胡椒主要集散地的贸易地位受到挑战,而由VOC推动、由华人开垦的甘蔗种植园则发展成为万丹属地的另一大财源,苏丹对地方的控制力也因此受到削弱(Ota 2005: 77-78, 96, 141-142)。
博物馆大院中展陈的石制糖绞便是万丹华人甘蔗种植园遗留的史迹。展品介绍牌称,当时的蔗糖生产主要集中在华人区,由当地华人运作,产出的蔗糖转运至巴达维亚,而后行销中国和日本。这些石糖绞由耕牛驱动,用于将甘蔗榨汁,在笔者的家乡澄海,本土蔗农直到20世纪仍用此种工具制作乌糖(红糖)。
晚清潮汕的榨糖作业,汕头英长老会会正汲约翰(John C. Gibson)著《华南的传教问题与方法》(Mission Problems and Mission Methods in South China, 1901)一书收录的照片
除了华人区出土的文物,来自苏罗索万王宫遗址的建筑构件上似乎也有中国元素。展出的宫门石质构件中,那几块雕有鳞、爪、牙图案的残件,看似是原来龙形浮雕的一部分;不过,根据博物馆展板的说法,这些图案刻画的是某种鸟类。
博物馆大院中展出的另一重要文物是一门名为Ki Amuk的大型火炮。该炮长345厘米,口径31厘米,重约6吨,炮身上刻有阿拉伯字母,炮口饰太阳纹。此炮原用于拱卫苏罗索万王宫,炮口面北,指向海岸。当地关于此炮的来源说法不一,或称此炮是淡目(Demak)苏丹与万丹联姻时送给苏丹茂拉纳·哈桑努丁(Maulana Hasanuddin,1522-27?—1570?年间在位 )的礼物,或谓此炮来自中东的波斯或土耳其(Ota 2005: 224-225)。
进入室内展区,可以感受到万丹博物馆在展陈的历史叙述中着力强调本土的多元文化,在布展上既有对早期印度化遗存的追溯,也将近代早期以来伊斯兰、中国、欧洲(荷兰)的文物并列展示。展厅通过陈列来自各国的钱币、瓷器和本土的香料等货物来呈现万丹这一港市国家往日繁盛的商贸。
馆中展示的万丹风格佩刀、不同式样的墓碑、少数民族民居模型等展品,则表现了不同族群在万丹的共存。该馆的部分展品介绍也颇具国际视野,例如,在介绍采用阿拉伯字母的古兰经印版时,馆方不仅介绍了阿拉伯语与本土语言的融合,还以万丹国王致英王查理二世的信件为例,讲述了阿拉伯文当时作为外交通用语的运用情况。 美中不足的是,该馆对荷属东印度时期的万丹历史的介绍仍较为有限。
万丹博物馆正对面便是苏罗索万王宫遗址,遗址的日常管理似乎也由博物馆负责,考察团在馆方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得以进入遗址。
苏罗索万宫是万丹苏丹国最早的王宫,据传是由建国苏丹哈桑努丁创建,因此也可说该宫是万丹建国的象征。不过,有关万丹建国的史事现今只能通过传说来加以勾勒。根据《万丹纪年》(Sejarah Banten)的说法,一位名为莫拉纳(Molana)的伊斯兰教导师从巴昔(Pasai)来到井里汶(Cirebon)并成为当地的统治者,号称Susuhunan Gunung Jati,后续他将井里汶和万丹分给他的两个儿子,鼓励幼子哈桑努丁在万丹建立一个新王国。根据对此人出身和经历的描述,不少学者认为,Susuhunan Gunung Jati所对应的就是巴洛斯(João de Barros)在《亚洲旬年史》中所记载的法特拉罕(Fatalahen,雅加达的Fatahillah广场也因他得名)。法特拉罕在淡目苏丹的支持下,出征印度化的巽他王国,于1527年攻取了巽他噶喇吧(Sunda Kelapa)并将之更名为雅加达(Jayakarta),且在此一时期取得了对万丹的控制,这两个商港此前均处于巽他王国治下。因此,太田淳认为,在万丹建立之初,其国应深受淡目苏丹国影响。平托(Fernão Mendes Pinto)在《远游记》中说万丹是淡目属国的说法可能确有所本(Ota 2005: 15-16)。
苏罗索万宫遗址城墙边展出的苏丹加冕石座(Watu Gilang)。据《万丹纪年》的传说,圣人Batara Guru Jampang曾于该石上打坐修行,岿然不动,直至鸟雀在其头巾上筑巢。传说又称,该石座为哈桑努丁所有,其父在指示他建城之时曾叮嘱他不得移动此石,一旦移走,其国将灭。
无论凭借文本还是眼前的遗迹,如今已难以想象苏罗索万宫在其建立之初的模样。该王宫在17世纪初经历火焚后原址重建,其后又经多次改建,最终在19世纪万丹苏丹国覆灭后遭陆续拆毁,仅留下环绕宫殿的宫墙残垣和殿宇地基。如今遗留的宫城格局是在1680—1681年间奠定的,主持修建者为从巴达维亚逃来、改宗伊斯兰教的荷兰石匠卡德尔(Hendrik Lucasz Cardeel,苏丹赐封号为Pangeran Wira Goena)。从现存遗址的俯拍图可以看到,该王宫的宫墙整体为长方形,四角修建有棱堡,在南北面的长边城墙上又增建有半月形堡垒。建筑学者认为,该王宫的城防设计与波兰、意大利、葡萄牙等地修建的美第奇式棱堡呈现出相似的风格,体现出欧洲军事知识在东南亚的在地化(Andrade 2011: 152-156; Tikhonova 2025: 402)。
上图为苏罗索万王宫遗址俯拍图,可见其距离海岸之近。王宫西北方有白色宣礼塔矗立之处为万丹大清真寺(Masjid Agung Banten),传说始建于16世纪,哈桑努丁、蒂塔亚萨(Agung Tirtayasa, or Abulfath Abdul Fattah)等万丹苏丹的墓均在其中。其地标式的宣礼塔据传是在17世纪由一位华人设计,而寺中的议事亭则由卡德尔主持建造。
这一棱堡式的宫城甫一建成,便见证了一场卷入荷兰人的宫廷斗争。在1670年代,名义上的万丹苏丹蒂塔亚萨已退隐行宫,将国事交与王储哈吉(Haji, or Abul Nazar Abdul Kahar)。然而,哈吉与荷兰人合作的政治倾向引起宫中高层的不满,他因此担忧父亲会改立他的弟弟为继位者,于是在1680年发动政变,软禁其父。这正是哈吉任用卡德尔改建王宫城防的背景。1682年2月,忠于老苏丹的权臣发起反对哈吉的政变,围攻修缮一新的苏罗索万宫。哈吉于是向VOC求援,荷兰军队进攻万丹为哈吉解围。哈吉正式即位后,便于1684年与VOC签订协议,给予VOC胡椒垄断权并允诺不许其他欧洲商人进入万丹,以换取荷兰人的军事援助(Ota 2005: 17-18)。 考察团头顶烈日登临城墙,以脚步丈量这一故宫。行至城角处,见水井、棱堡营房等防御工事遗存结构尚算完整,虽历数百年,仍可供想像当年士兵在此卫戍之姿。到18世纪,荷兰人已然将王宫的棱堡视作他们自己的防御工事,称之为“钻石要塞”(Fort Diamant),在1789年,更有61名荷兰士兵入驻棱堡(Ota 2005: 22)。
相比起较为完整的城墙,苏罗索万的宫苑今已残破不堪,保存稍好者,大概仅有大殿殿座和王家浴池。苏罗索万宫作为万丹苏丹的王宫,除了是政治决策的中心外,也是万丹胡椒贸易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在立国初期,万丹苏丹便将统治范围扩张到了楠榜(Lampung)、明古鲁(Bengkulu)等苏门答腊岛上的重要胡椒产地。在楠榜发现的“波戎法令碑”(Dalung Bojong Charter)便反映了17世纪万丹苏丹对该胡椒产区的控制,其铭文中写明:“满载运往苏罗索万宫的胡椒货物须附上一封来自廷臣的介绍信”(Pratama et al 2023: 736-737)。 正是依靠对属下各产地的胡椒集运和贸易,万丹王室才得以积累起大量财富,对胡椒的有力把控,也成为万丹与欧洲势力谈判过程中的筹码(Pratama et al 2023: 739-742)。 宫城中现存的几处浴池遗址是苏丹财力的见证之一,这些遗址尚存梯阶、人工岛等结构,引人遐想昔日万丹王室的生活场景。宫中用水来自附近的山泉,山泉先引至王宫西南面约2公里处的皇家别苑Tasikardi,再经水道引入王宫。Tasikardi意为“山中之海”,是一座建于湖中心人工岛上的两层建筑),建成时间应不晚于1684年,引水水道则是在1701年建成的(Ota 2005: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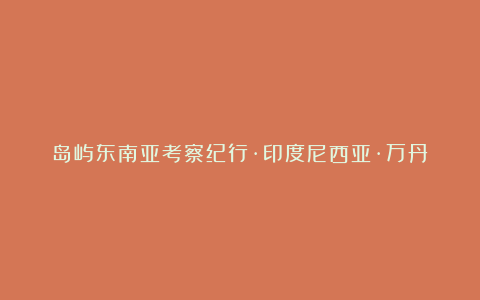
森森宫墙仍在,却未能守住堂皇殿宇.如今的苏罗索万荒草萋萋、不见宫阙,幸有史料可借以剥开此地遗留的历史层累,从中管窥近代以来欧亚文明的交融与冲突。
午餐后,考察团一行来到斯皮威克堡,考察VOC在万丹留下的遗迹。
斯皮威克堡坐落在万丹的旧海岸线上,扼守万丹河口。该堡垒建于1685年,以当初下令介入万丹政争的东印度总督科利内斯·斯皮尔曼(Cornelis Jansz Speelman)命名。它的建设与此次军事介入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是VOC为保障其在1684年条约中攫取的利益而建(Ota 2005: 23)。
荷兰人对这一战略要地的占据的确发挥了作用。1685年8月15日,搭乘着“国王数学家”的法国赴暹使团航抵爪哇岛,出于季风原因和对沿岸暗礁的担忧,使团决定先在万丹抛锚,而非直赴巴达维亚。由于跨洋航行中许多乘客患上了坏血病,使团便在次日早晨派出福尔班(Claude de Forbin)中尉上岸交涉,以求觐见国王、获取补给并让病人上岸休养。驻守要塞的荷兰中尉拒绝了福尔班的所有请求,理由是万丹国王不允许任何(其他)外国人踏上其国土(Forbin 1996: 36-37)。 尽管荷兰人在过后给法国人送来了补给,但他们从始至终都不允许法国使团登岸,千方百计以苏丹的名义加以推脱,使团船队只得转往巴达维亚休养。同行的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因此说:“荷兰人才是万丹的主人,被他们当作拒绝的借口的万丹国王完全受他们的控制,甚至由他们的军队看管” (Gatty 1963: 67)。由此可见,通过建立斯皮威克堡,荷兰人一方面对外限制了万丹苏丹与他国船只的联系,得以在欧洲对手面前强化其对万丹贸易的垄断;对内而言,由于苏罗索万宫就在该堡东南方不远处,且可沿万丹河溯流而至,该堡的驻军又对苏丹形成了军事威慑。
除了踏查该堡垒的城墙、地堡、城门外,在老师的提醒下,考察团还在棱堡台地上的草地和砖瓦间动手翻找,捡拾到不少珊瑚礁石和中国瓷器碎片。据斯皮威克堡遗址的简介折页所说,该堡地处海滨,在建造时就地取材,混合使用了珊瑚礁、沙砾和砖石来建造城墙。
考虑到斯皮威克堡也是VOC万丹商馆的所在地,散落地面瓷器碎片既有可能来自当年荷兰商船搭载的外销瓷,也有可能是当地驻员遗留的日用瓷器残片。2009—2011年间,由印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主持的万丹考古工作中,考古队在苏罗索万宫发掘出了数量可观的中国瓷器。由类型学特征判断,这些瓷器主要产自景德镇和闽粤两省,以盘和小碗等日用器皿为多(Ueda et al 2016: 105-109)。 可见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多和瓷器贸易的发展,明清时期的中国外销瓷已深深嵌入其时万丹的社会生活之中。
下一个行程是荷兰人驻地对岸的华人区。考察团对该地区的考察从与斯皮威克堡隔河相望的观音庙开始。
根据该庙的介绍牌,当地传说称,这座观音庙的建立与阿桑努丁之父Susuhunan Gunung Jati与中国公主凤珍(Ong Tien)的联姻有关。传说中国皇帝的女儿凤珍来到爪哇与Susuhunan Gunung Jati成亲,这位伊斯兰教导师见她的随员中仍有许多人坚守华人信仰,于是在万丹大清真寺附近建立中式庙宇供他们崇拜,1774年才迁建到现今的位置。另有说法称该庙始建于1652年,结合明清易代时期华人南渡的历史背景,这一建庙时间点似乎更为可信。
事实上,爪哇各地都流传有关于“凤珍公主”的传说。马来西亚学者郭宗华(Koh Chong Wah)利用井里汶的文献分析了“凤珍公主”传说的起源和传播路径。郭宗华认为,“凤珍公主”的原型可能是井里汶归化华人哈芝·陈英发之女,她之所以被传为“中国公主”(putri cina),是因为该词在印尼语中有“中国公主”和“中国女子”两个含义,数百年来历史的叙述者出于强化苏丹权威等考虑,采用了“公主”一义融入传说中加以传播。总的来说,凤珍公主的传说反映了爪哇社会对15—16世纪穆斯林统治者与当地华人联姻的历史记忆(郭宗华 2022: 175-199)。
该寺的主殿已是新建,除主祀被称为“万丹佛祖”的观音菩萨外,主殿两侧的神龛还有供奉有大伯公、马婆佳、关公等从祀神明。主殿中保存的文物已寥寥无几,除神像外,可见者有光绪二十七年(1901)由信徒傅孙模献立的“神通广大”匾,以及据称始作于1895年、在1960年由翁兆美(Ang Tiauw Bie)出资修整的观音神轿。翁兆美是当地侨领,1892年出生于万丹的他早年在家族的椰子园帮工,1930年代,他移居楠榜,在当地投资椰子加工业,此后又进军航运业,商业版图不断扩大。在经营航运业期间,他利用自己往来荷属东印度与新加坡的货船为印尼军队运输武器,这一贡献使他在印尼独立后获得数枚由军方颁发的勋章。1960年1月15日,印尼总统苏加诺赐名翁兆美为Anggakusuma。 除结交独立初期的印尼高层外,翁兆美与地方华人社会也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不仅资助家乡万丹的观音庙,还在发家地楠榜被推举为楠榜福建会馆的名誉主席, 在1963至1967年楠榜大兴庙的扩建工程中,翁兆美也是发起人之一(李汉青 1968:28;傅吾康 1988:563)。 某种程度上说,翁兆美的生平轨迹体现了万丹港与楠榜地区历史联系的现代延续。除此之外,主殿的雕花隔屏上还有一处细节值得留意:该屏落成于2012年,而右侧又题写着与公元纪年对应的“民国壬辰年”,这一对纪年传统的固守,不知是敬献者某种政治倾向的表达,抑或只是本土使用习惯的延续。
绕过整饬一新的主殿,殿后供奉的神位似乎更能反映该寺早期的祭祀形态。观音庙大殿后有乾隆十九年(1754年)南靖裔华人高彩官的墓碑,台上神龛里又供着其他高氏先祖的牌位。据日惹大学学生Miskaningsih的研究,高彩官是此庙迁至此地后的首任住持,若真是如此,观音庙在此处建立的时间似应早于简介牌所说的1774年。高氏先祖的神位隔壁还有白虎神和“万丹伯”的神位,传说“万丹伯”是第一位到达万丹的华人,万丹伯的神龛中供奉着“何浦清将军”的牌位,或许这位何浦清便是万丹伯神化之前的历史原型(Miskaningsih 2017: 49-50)。 与万丹伯相邻的是用于祭祀井神的祭坛,当地又将该井称作“万丹伯井”,相传其井水可祛病消灾。
离开观音庙,考察团乘车前往南面不远处的华人区清真寺(Masjid Pecinan Tinggi)遗址,Tinggi在印尼语中意为“高的”,不知在此形容的是地点还是建筑本身。当地传说中将该清真寺的建立时间同样追溯到哈桑努丁之父传教的时期,该寺的所在地是华人聚居区,这或许反映了早期定居万丹的华人皈依伊斯兰教的历史。据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推测,曾替荷兰人与万丹苏丹谈判、在巴城接待过明朝使节的VOC代理商“杨昆”(Jan Con),便是一位在巴达维亚建立初期由万丹逃往巴城的华人穆斯林(包乐史 1990: 70-71)。
该清真寺在建造中也使用了珊瑚礁作为建材,但如今损毁严重,仅余主殿地基、朝拜龛和宣礼塔。清真寺遗址北面还有一座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夫妻合葬墓,为中式墓而非穆斯林墓的样式,不知该墓与清真寺是否有关。主殿遗址南面的地基遗址像是原来的穆斯林墓,其形制与遗址围墙外的几座穆斯林墓类似,或许清真寺南面才是该寺的穆斯林墓葬区。
离开位于苏罗索万宫西北方的华人区,考察团又乘车到苏罗索万宫东南方向的卡伊彭宫考察。据介绍牌所说,卡伊彭一词来自ka-ibu-an,意为“母亲的住所”。该宫殿是万丹末代苏丹沙菲乌丁(Tsafi Uddin,1816—1832年间在位)母亲拉图·艾莎(Ratu Aisyah)的住所,据说这位太后在其子年幼时摄政,而这位末代苏丹则在1832年被荷属东印度当局以意图谋反之名流放至泗水,标志着万丹苏丹王系的终结,卡伊彭宫也在同年被毁(Ota 2005: 226)。
相较于见证过王权顶峰的苏罗索万宫,见证了苏丹国末日的卡伊彭宫虽规模较小,却存留了更为丰富的宫殿建筑结构。据介绍牌所说,宫殿外墙上的圆拱型小门与内部方正的二道大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象征着外部俗世空间与内部神圣空间的严格区分。说其内部神圣,是因为该宫殿的核心建筑原为一座高大的清真寺。位于东侧的殿宇遗址据推测可能原为拉图·艾莎的寝宫,此处基座中设计有诸多方形隔间,或许是用来引入宫外水道里的水,以为寝宫降温。 沧海桑田,卡伊彭宫如今仍有水道环绕,溪边老榕树与矮墙里的茵茵绿草,将这座早已凋零的宫殿变作了儿童乐园,即使暮色渐至,仍见朝气蓬勃。
在万丹的最后一站,考察团到了爪哇海之滨的卡兰甘都码头。卡兰甘都河是万丹东部的另一条入海河流,荷兰人也曾在此河口西岸构筑一座较小的堡垒,称卡兰甘都堡(Fort Carangantoe,见前文地图),但在1770年后,此处便因荷军兵力供应不足而撤防(Ota 2005: 23)。 卡兰甘都河东岸的集市数百年来未易其址,它一度是万丹城区最大的集市,每天早上开市,1780年代荷兰人的记录称,正是它和另外两座集市为万丹居民提供了一切生活必需品(Ota 2005: 25)。
尽管海岸线已大幅北移,卡兰甘都河的入海河道仍然通畅,此处的码头是游客乘船往吞达岛(Palau Tunda)等处的出海港,也是众多渔船停靠的避风港。由于这里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红树林等独特景观,如今堤岸上已建起联排的食肆餐馆供游人休憩消遣。走到河口栈道的终点,万丹湾天然的半月形海岸线一览无遗。站在“弯月”中央眺望海面,这片明人笔下的西洋、近人口中的南洋、欧人称为东印度的海洋,在考察团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北方。
日落时分,告别卡兰甘都的往来船只,考察团乘车离开万丹这一多方汇通之地,返回雅加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