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湖南农科院田间杂草控制创新中心2016年发表在Pakistan Journal of Botany的英文文献《Comparative anatomy of Myosoton aquaticum and Stellaria media and its systematic significance. 》在形态学方面论证了鹅肠菜应该归繁缕属。
我说今天晚上好像在联合战斗一样,好有趣啊。
凌晨1点,感觉终于可以睡觉了……但是,定鹅肠菜的前辈是已经长眠了,我睡不着。
我想起来上学期科幻科普创作理论课上,吴老师说:“做科普用着不知道转了多少次的二手、三手、甚至十几手资料,能去对一下科研资料就不错了。”确实,比如写植物科普的号能不只靠网络资料,去认真比对一下《中国植物志》之类的专著就已经算是认真了,多得是抄也没抄对的资料。如果再多查几个植物书互相论证一下,就是对自己写的东西很负责了。至于这个转了十几手的资料的可信度究竟多少,就更是无从查起,人云亦云了。
科普个鹅肠菜你这么较真干嘛?不就是图一乐吗。
吴老师也说过:“科普的第一要义是如何吸引留住观众,要像讲脱口秀一样,15秒就得有个包袱。科普切忌追求完美。”
对于科普工作者来说,第一要义当然是把有趣的科学知识以公众最能接受的方式传递过去。但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严谨的符合客观事实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对我来说要花很多时间去查的文献,隔天早上Tcy就已经找到了1794年将鹅肠菜单列属的Moench的最原始的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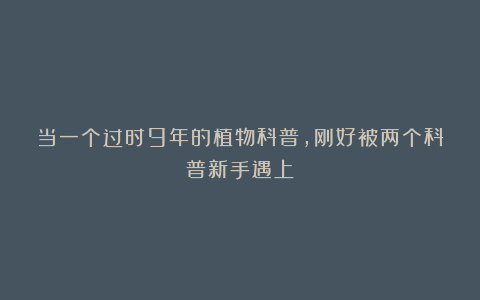
Tcy大概翻译是鹅肠菜属(Myosoton)花萼5裂,花瓣5枚,先端2深裂。雄蕊10枚,花柱5枚……
但话说回来,2016年由湖南农科院发表的论文就提到野外广泛观察到柱头数目3-5,并不是只有我观察到。那为什么到现在还靠5-10公式辨认广布全国,门前屋后的鹅肠菜?是我们俩太较真,还是大家都不较真呢?诚然,这只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甚至不能称作“错误”的问题,只是信息更新不同步即时而已。
但这依然是我觉得值得记录的一个晚上。依靠我对植物分类产生的敏锐,我在守卫科普应该对存疑的问题认真查询。而Tcy作为一个植物分类的学生,也不放过她碰到的任何科学问题。就像她公众号的文章植物分类学,就是认识植物吗?里面说的:“认识植物,是植物分类学研究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如果能从整个植物分类对植物的认识过程来看,这只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调整。
我突然想到,如果仅靠我现在做科普的经历,我不一定有继续“较真”的坚持和找到答案的能力。如果仅靠Tcy,她也可能在漫长的科研生涯里,不会去细看一个不是她研究类群的分类历史。而我们睡前的偶然讨论,似乎成为了一场植物科普和植物科研默契的合作。
但这不仅仅是科普有没有“抄对”的问题,而是第一份被做出来的作业,经过二百多年的科学发展,人类对鹅肠菜这个物种的认识的多次讨论,又一次被推翻。但是还在抄这份作业的同学,并不知道这个答案已经不对了!
分类之所以是植物科学的“基石”,就在于它是第一份交出去的作业。不论科普做的多么天花乱坠,不管某个植物的种植规模、经济价值达到多大,文化含义多么重要,最后发现——你从一开始就没搞清楚人家是谁,就会闹一个乌龙。
那又会被质疑了:“怎么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没做对?分类天天变来变去的,这个也要修订那个也要推翻。”
那我还得为把鹅肠菜单列属的Moench说句话:“你知道这在18世纪是多时尚多大胆的分类吗?”林奈出版《自然系统》时,依据雄蕊和雌蕊的类型、大小、数量及相互排列等特征,将植物分为24纲。Moench当年追随林奈,凭柱头5单列一个属,已经是走在科学前沿了。《Flora of Europe》
《Flora of China》和《Flora of India》都还将鹅肠菜单列属,如果我不是偶然找到了鹅肠菜柱头数目3456都有,我也会拥护这是一个稳定的质量性状。
但现在不管是形态学上的证据还是分子证据都支持鹅肠菜属于繁缕属,这恰恰又证明了植物系统分类课上王老师说的:“我们对植物的了解不深刻,就要不停地修正,变就是认知在变,所以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认知有限,我们无法深层地了解。”植物分类当然有用,可问题是,它为什么非要有用?(又call back了,怎么不算一种脱口秀呢?)
一个小属修订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就是二百多年后,一个在奶奶菜地里发现鹅肠菜的柱头有345的年轻人记下了这个问题,并与和她一样为此不睡觉的另一个年轻人进行了一个小小的探究,而她们还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被更多人知道。因为那个菜地,是她幼年时最熟悉的地方,因为她的奶奶一辈子也不知道,那个总是出现在她地里的小花叫什么名字,和其他的小白花有什么区别,而只叫它们喂鸡草。
一个小属的修订,是一个过去两百多年才被遥远的国度的人们看见的故事,背后是无数植物学家对它兜兜转转的认识。
Scopoli在1772 年将该种从卷耳属转入繁缕属,Moench在1794 年将该种归入鹅肠菜单属,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分类学家根据 Scopoli 或 Moench 的观点,对鹅肠菜的分类地位进行了争论。
一个小属的修订,是关于我们如何认识植物,如何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科学发展下,不断更正我们对自然的理解,不断思考生命的历程会如何交融,两百年来前人与后人对话,爱种菜的老奶奶通过孙女认识了地里年年都在的野草。
上个星期我问deepseek,我如果做环境教育的同时又喜欢植物分类,会不会不够纯粹呢?
D老师告诉我:环境教育/博物学是“横向”的广度,植物分类学是“纵向”的深度。两者结合才是“T型人才”的终极优势。有了这个深度,你的“横向”传播将更有根基、更具穿透力。你可以向公众更精准、更有底蕴地解释植物的奥秘,而不仅仅是泛泛而谈。
* 能否将你的发现转化为科普内容,让公众理解一个小属修订的意义?
* 思考你的工作如何为理解植物多样性、演化提供了一块坚实的拼图?
* 展示标本馆工作的魅力、野外发现的惊喜、解决一个分类难题的智力乐趣、形态学观察的精妙。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特而强大的环境教育!让公众看到科学研究的另一面!
我没想到这个实践的机会来的这么快——那么,我想表达的东西,有好好地传递过去吗?
就像Scopoli和Moench也在对我说:“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有好好地通过那些泛黄的纸张,跨越两百年的时光,传递给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