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又听了一期的《文明之旅》,中间罗胖子讲到了一个名词叫“司马光困境”。
立刻马上,我就跟“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联系到一起了:当司马光自己也掉进“缸”里时,他该如何脱困呢?会有人在外面拿大石头把缸砸破救他出来吗?如果没有,他又是如何自救的呢?如果连自救的法子都没有,他会不会听天由命呢……
我写的很粗糙,详略也分配不当。想要了解详情,还是去看罗胖子的视频吧。
公元1071年,大宋熙宁四年,王安石变法的第三个年头。
翻开这一年的史册,仿佛打开了一部充满黑色幽默的政治讽刺剧:反对派与变法派彻底撕破脸,前任宰相富弼公然抗旨不执行新法;司马光在对王安石进行了一番“人品鉴定”后,潇洒地挥一挥衣袖,前往洛阳专心编写《资治通鉴》去了。
在这场变法大戏中,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为什么几乎所有初衷良善的新法,最后都变成了老百姓的新负担?为什么那些由顶尖聪明人设计的、经过试点和修补的利民措施,最终都难逃“龙种变跳蚤”的魔咒?
要理解这场变法为何屡屡跑偏,我们得先认识一下北宋社会的“隐藏主角”——特权。
我们不妨这样想象:当时的北宋社会,就像一场盛大的魔术表演,而特权就是那位手法娴熟的魔术师。
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只要沾上皇权一点边儿,就能拥有特权,好比宫廷里的宦官也能权势熏天;第二,只要和特权来源的联系一断,特权立刻消失,就像魔术师一松手,魔法就会失效。
汉朝萧丞相对此有着深刻理解,这位权力顶峰的人物,买房子置地时专挑又偏又贫瘠的土地。
他解释道:我的子孙如果有本事,就用不着好地;如果没本事,我留下这一堆破地,那些后世有特权的人家也不至于抢他们的。
多么痛的领悟啊!那些个特权在手的人,会清醒地认识到:特权是无法继承的,特权拥有者一旦失去与皇权的紧密联系,立刻成为被宰割的对象。
王安石变法的核心理念相当现代:用自由的市场交易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通过创造新的市场和交易类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为国家创造增量财富。
青苗法的设计初衷十分美好:由官府出钱参与民间借贷市场。民间高利贷平均7分利,官方只要4分,既让农民在青黄不接时有钱可用,又让国家资本获得金融收益。
问题在于,自由交易的前提是双方对等。然而交易的一方是代表特权的官僚系统,情况就变得魔幻起来。
一旦面临风险,特权立刻脱下“对等交易对手”的外衣,露出本来面目。官府懒得跟贫家小户打交道,直接把青苗钱摊派给富户:老爷我给你们一个机会,帮朝廷一个忙,现在拿100块走,明年利利索索地交140块回来。什么?你家不需要?怎么那么不懂事呢?
如果你认为这违背了帮助贫民的初衷,别担心,特权自有办法:把青苗法跟保甲法绑定,每五户或十户组成一甲,穷人借了钱还不上?让同甲的富人帮忙还啊!
可能有人会抗议:这不是违反“自愿”原则了吗?
这都不叫事儿,特权官僚有的是办法,让所有被迫借钱的人承认他们是“自愿”的?
就这样,在特权的一次次伸张中,龙种终于成功变异为跳蚤。
最富戏剧性的,莫过于“司马光困境”了。用句俏皮话来说,就是司马光也掉进缸里了。
九年前,司马光曾给皇帝上奏,指出当时社会的一大痛点:地方州县的劳役往往落在稍有结余的家庭身上,这些家庭因为有点财产,“既是铠甲,也是软肋”,容易被官府拿捏,许多因此破产。
司马光当时建议:不能让普通农民干这些事,应该让官府花钱雇佣城里人来干。
然而,当王安石推出本质上实现司马光建议的免役法时,司马光却跳出来反对。
后来的宋史研究者们对此大加抨击:问题是你发现的,主意是你出的,现在人家照你的想法做了,你却反对。这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吗?
司马光给出的反对理由,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两难:
如果少收钱低价雇人,雇来的必然是街面上的游手好闲之徒,这些人品行不端,监守自盗,犯事后远走他乡,无从追查。
如果多收钱找靠谱的人?基层贪官污吏等的就是这句话!“好嘞!朝廷有令,多收钱、雇好人,弟兄们,并着肩地去收钱啊!”最终遭殃的还是老百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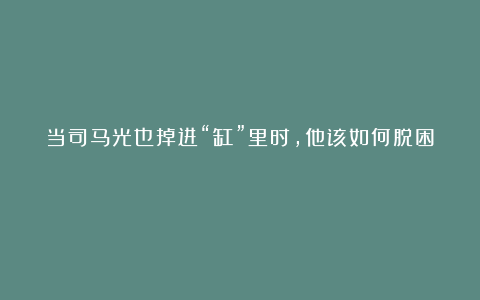
这就是“司马光困境”——改也不行,不改也不行。或者说,砸缸也不对,不砸缸也不对。
为了遏制特权的恶性发作,朝廷不是没想办法,比如制定各种规矩。但这又带来了相反的作用——一刀切。
宋代劳役摊派的基础,是把农民划分为五等,按资产摊派,听起来很合理,简直是朝廷出面“劫富济贫”。
这个制度一旦固化,魔幻现实就上演了:老百姓想方设法不“升等”。
司马光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他在乡下问百姓为何不勤劳致富,百姓回答:我要是胆敢多种一棵桑树,多置办一头牛,邻居很快就会报官,说我家有钱,应该升等,承担更多劳役。我还敢增加田产、修房子吗?
不勤劳致富,最终也躲不过这一刀。当最富有的那批人被摊派折腾破产后,还是要“矮子里拔将军”,选一批比较富裕的人家顶上去。
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百姓之间的互害机制。
想要不升等,老百姓还有更极端的办法:分家。
朝廷却有明文规定:祖父母、父母健在不能分家。
于是,一幕幕的人间悲剧在堂而皇之的规定缝隙中产生:有的老父亲把心一横,自我了断,让子女分家;有的六十多岁的老娘被迫改嫁,只为让家人能合法分家。
这些荒谬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是那条固化的界线——一旦达到那条线,成为“富户”,就完蛋了。
面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困境,你可能会问:难道朝廷什么都不做才是对的?
这一问,反倒触及到了真相:中国政治一直有“垂拱而治”的传统,希望君王“垂衣拱手”,什么都不用干。
是不是太被动、太保守了呢?其实人家的真正意思是:你要是不垂拱而治,就给了那些坏人机会,天下就会不治。
小苏说得精辟:上有毫发之意,则下有邱山之取;上有滂沛之泽,则下有涓滴之施。
上面动了头发丝那么大的念头,到了下面,就要找老百姓要一座山那么大的利益;上面像下暴雨一样的恩惠,到了老百姓那儿,也就剩下一滴两滴的好处。
中间的“放大器”和“拦截阀”是谁?不言而喻,就是整个官僚系统。
所以说,君主们最好什么也别干。动个念头,经过放大器之后,都是扰民。
与之前的朝代相比,宋朝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田制不立”——没有制订土地管理制度,土地相对可以自由交易。
结果如何?当然有土地兼并问题,更重要的是,民间活力被点燃,土地利用效率提高,整个社会变得有弹性。
你可能会认为,宋朝皇帝懂现代经济学,建立了土地交易市场?哪儿啊!这完全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很多时候,大家争论的都是政策对错。但在历史的真实逻辑里,尤其是站在民生立场上,统治者没有做什么,往往远比做了什么更加重要。
就像坐电梯的人,你在100层采访他,他告诉你爬到100层是因为在电梯里做俯卧撑。其实,他什么都不用做。
回到1071年的开封城,王安石正与他的反对者们争论得面红耳赤。或许他们都没错,只是新法生错了时代。
在一个特权无处不在的系统中,任何良好的初衷,都可能被那只看不见的“魔术手”变化成对百姓们的新型剥夺手段。
这场千年前的改革闹剧,留给我们的不应仅是一声长叹,更应是一个永恒的思考:在制度设计与人性现实的拉锯中,我们究竟该如何避免“龙种变跳蚤”的魔咒?
或许,承认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的,都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少些对基层民众的指手画脚,尽可能给社会留出更多自发秩序的空间,才是真正的智慧。
而这一切,对今天的我们,又何尝不是一面镜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