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冬天,福建永泰的下傺寺里,空气都有点凝重。那天一早,门口进来四位穿着有点正式的人,为首的是位老郑,其余三人都是调查专员,听说分属省市县三级组织部门,算是来头不小。寺里的杨道明和尚本已经年逾八十,平日里稳得很,可一见这阵仗,眼里居然泛起泪光,有点说不出话来。
按道理说,这种场合和尚总不会失态,但杨道明就是忍不住,眼角通红。他看着几个调查专员,嗓子发颤地说:“你们找的妙圆,就是钟循仁。我已八十多了快走到头了,虽然他生前千叮万嘱,不许我说出他的身份,但我越想越怕,一旦我走了,他就彻底成了党史里的谜案,对党也不是好事。”
一听这话,寺里一时间静得连风声都听得见。外人不明就里,其实这事,说起来足够让人扒拉一晚上。谁是这位钟循仁?又为何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掖着藏了大半辈子?
钟循仁,老江西兴国人,1905年的生人,不算太早的那一波,但出去念过书,有家学底子。其实那年代,乡下能堂堂正正上学的,家里没点分量真不行,人也因此见识早开。那时候兵荒马乱,街头巷尾好多孩子一到年根就开始吃糠咽菜,饥一顿饱一顿。钟循仁心里很不舒服,别人苦他能看在眼里,是那种天生心软,还常常被街上的流浪娃撩拨着郁闷半天。
但命运有时穿插得巧。他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籍,又碰见了江西地下党活动的几个老同志。外头动荡,钟循仁却是动了真心,愿意扎进去做点实事。他没那么多花头,实打实地想着,“只要对大家好,对得住良心。”说起来,他不是那种讲场面话的人,但实际参加党组织,开始从基层帮着乡里人东奔西跑,比如后来参与高兴乡农民协会,出了不少力气。那些年,他不停帮乡里穷苦户摆平了债务、挪腾一些田,干得热火朝天,很快就被推举成了区委书记。
其实早年的苏区干部不太讲究衣着和排场,大多数人做事直来直去。钟循仁就是这种骨子里较真的人。好多兴国青年听他一番话,都愿意跟着干,算是一呼百应。当时大家说,“这才是带头人。”其实他也有家庭,说是带着家属下田也不稀奇,百姓见了都服气。
有个细节我记得特别清楚。1932年冬天接近年关,一场募捐救助活动刚办完,钟循仁在寒风里拍着冻得通红的手,亲自一份份登记有多少粮食、棉被、旧衣服,有个小伙子看见他自己不添名字,咧嘴问:“钟书记你家里缺吗?”他就笑着回:“我家有,不缺。”这话让人记了一辈子——他没让亲属优先得东西。
到了赣南,形式更紧张,敌军一度疯涌进来,每天都有人被抓走。红军主力离开后,部下都愁得不行,有一天夜里,钟循仁拎着小马灯挨个去看阵地,鞋子又湿又冷,还背着土豆包送到前线,“大家别怕,老钟在!”就这几句,换回一夜安稳。
进入1934年,他当上了赣南省委书记,责任大,说是天塌了也得硬撑着。其实那一年,外头风声鹤唳,很多同志怕得天天关窗,只敢深夜开会。钟循仁反倒经常半夜敲门找人闲聊,说是聊,其实就是摸底,“你心里想啥?”没啥铺排,硬是让一堆人重新上了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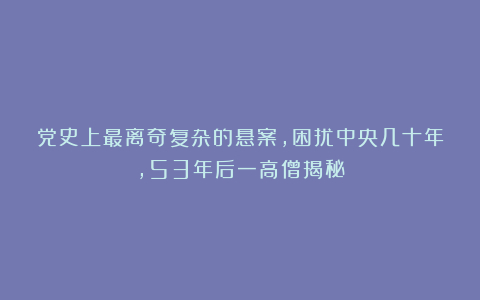
不过人终究有力竭的时候。后来他接到调令,要去福建闽赣继续拼搏。老实说,大家都明白,这路就是一条险路:敌人密布,暗杀随时可能发生,能不能活着回来的说法可就只有天知道。真到了福建一带,原本的自己人却各怀心思,不团结得一塌糊涂。军区那几位领导拥兵自重,谁也不服谁。领导说话当耳旁风,心思不在正道上,把战友说成“拖后腿的”,有两位甚至私下里叹气:“还有啥好干的?不如投了。”这种气氛,钟循仁有心无力,几次开会,只觉得大家心都散了。
其实他也摆出诚意,试着找宋清泉(那时的军区司令)喝了次茶,没怎么谈工作,就随口聊起家乡小吃。宋清泉爱吃辣,钟循仁老家偏甜,两人说到最后,谁也没真正打开心门。后来发生“诈降传言”,倒是让人一下子毛了。钟循仁查清楚后,没多说,只在晚上找到几个亲信,“我们都辛辛苦苦熬了这么久,不至于到现在投敌。”但众人的心思已经盛开铁锈,想拉也拉不住。
最离谱的一次是敌军送上大肥猪,稀里糊涂就被带进了据点。普通士兵饿得脸黄,见油腻就馋得要命。当时有人在后山偷偷烤猪肉,香气飘了一夜。钟循仁在屋外皱着眉头发呆,杨道明则在一旁不停地叹气:“真的守不住了。”第二天一早,敌军和军部里应外合,队伍就此瓦解。
眼瞅着只有不到三十个忠实同志还愿一起坚持,大家散着哭,急急忙忙突围,这一夜之后好些人都成了无名英雄。后来只剩七人。钟循仁苦笑着安慰杨道明:“总有路走。”其实连夜奔逃期间衣衫褴褛,山路泥泞,有次蹚水时脚都冻伤了。杨道明问他,“你还后悔吗?”钟循仁说,“只要没害人,不后悔。”
到了后来的那段日子,变名字藏起来。钟循仁自称黄家法,杨道明换名谢长生。从市井到深山,最后干脆进了寺庙出家。那地方冷冷清清,白天帮着挑水种地,晚上坐在堂前烧纸。寺庙里有个师傅叫老邱,经常开玩笑,说这两位“面相不一般”。其实大家都是苦中作乐。两个月后剃度,那一刀落下,其实比战场上挨一枪还心疼,但也没办法,活下去总归要有隐蔽处。
退隐之后,他们没闲着。钟循仁在寺里敲钟种田,拉着几个老僧一起试着种豆,种到后来,全庙的粥都是自己收的粮。过了些年,有食堂来请教种地的窍门,寺庙让他们吃饱喝足再回去。有人曾讥笑,“你们是俗人。”他倒一点不计较,只悄悄捐了两条旧被给邻寺。
其实这期间,他经常夜里坐在蒲团上,看着窗外月光就掉眼泪。一次和杨道明下棋,钟循仁都走错了三步。他忽然说,“这一辈子,总觉得对不起上面交代。”杨道明安慰道,“你已经做得够多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风平浪静的日子总算来了。但他们俩却始终隐姓埋名,见着老同志也不敢相认。其实身边很多人不明白,“为啥不去北京报到?”实际上内心的愧疚比什么都压人。钟循仁常说,“怕见老战友,怕丢人。”其实没人指责他俩,但就是过不了心里那道槛。
可就在这事迷了几十年后,还是杨道明最后选择说了出来。他红着眼圈和调查组说:“别等到都走了才知道真相,党史不能留这样悬案。”其实妙圆和尚一生寂寞,钟循仁再大能耐,最终也只是一介隐姓的老人。
这些故事,换了谁听,多少都有点难受。人这一生,能做几件顶天立地的事,已经不枉了。钟循仁,是历史里的风风雨雨,也是我们村头说起“旧社会的硬汉子”的样板。遗憾是留下了,但那种骨头里的担当,再过五十年还有人会念叨。
每每想起这片故事,不知道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心里忽然沉了点。其实人生里最重的不是荣誉,是别辜负自己。到底该如何评价这样一位“消失的英雄”?也许历史总是留下个谜,那就让我们多记一段传奇,不让他轻易随风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