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糟糠
"杨老头,我不干了。你还是请个保姆吧。"赵大妈放下手中的抹布,语气里有着说不出的复杂。
我一愣,手里的茶杯停在半空,心里咯噔一下。
这半年来,我早已习惯了她的身影在厨房忙碌的样子。
"为啥?是钱不够吗?"我试探着问。
赵大妈摇摇头,目光躲闪,只说自己想通了,觉得不合适。
我叫杨守仁,今年七十岁,是八十年代全市有名的西安机械厂高级工程师,那会儿可是个吃商品粮的"金饭碗"。
去年冬天,我的老伴儿王淑芝因病去世,膝下无子,从此一人独居在老旧的筒子楼里。
我和老伴儿结婚四十三年,早已习惯了她在身边的日子。
那时候,每天清晨醒来,她已经把热气腾腾的稀饭端上桌,咸菜碟子摆放得整整齐齐。
如今,老伴儿走了,家里的一切仿佛也跟着失去了色彩。
日子像是被剪断了线的风筝,飘飘荡荡,不知归处。
电视机落了厚厚的灰,我懒得打开,那上面放的都是年轻人的节目,像天书一样让我看不明白。
家里的双人床,我只睡一半,另一半永远空着,就像我的半边身子也跟着老伴儿一起走了。
那是去年腊月,天冷得刺骨,我穿着老棉袄在小区的长椅上发呆。
"杨师傅,这大冷天的,您咋坐在这儿呀?"赵桂珍大妈裹着件红色的羽绒服,拎着刚从菜市场买回来的萝卜白菜,站在我面前问道。
她是小区里的熟人,比我小两岁,是我们单位老领导王大爷的表妹,听说我老伴儿走了,脸上露出惋惜的神情。
"回家也是坐着,在哪儿不是坐。"我苦笑道。
"我听说您老伴儿……"赵大妈的话没说完,我的眼眶就红了。
老伴儿走的那天,医院的走廊冷冷清清,只有我一个人在太平间外面站着,撕心裂肺的痛让我几乎窒息。
"您这样不行啊,饭总得吃,日子总得过。"赵大妈叹了口气,"要不这样,我来帮您搭个伙吧,反正我一个人吃饭也是吃,两个人吃也是吃。"
赵大妈说这话时,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上的皱纹像是扇面上的折痕,透着岁月的痕迹。
我知道赵大妈也是孤身一人,丈夫是知青下乡时在山区出了事故,膝下有个儿子在广东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
她住在小区另一栋楼里,靠着微薄的退休金过日子,儿子虽然偶尔寄钱回来,但她舍不得花,都存着。
我想了想,不能白占人家便宜,就说每个月给她五千块钱,权当是工钱。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赵大妈连连摆手,"咱们都是老街坊了,还说这个干啥?"
"那不行,您搭伙是帮忙,可做饭洗衣总归是劳动。"我坚持道,"咱爹妈辈都说,人活一辈子,钱是身外物,咱们做人不能糊涂。"
赵大妈起先不肯收,后来拗不过我,也就应了。
就这样,我们相处了大半年。
每天早晨,窗外的喧嚣声中总会传来赵大妈的脚步声,伴随着塑料袋摩擦的声响——那是她从早市买回的新鲜蔬菜。
她总会提前到,说是赶早市便宜,其实我知道,她是怕我一个人起不来,又或者起来了却不知道该干什么。
"杨老头,看看今天买了啥好菜,都是新鲜的!"赵大妈总是这样兴冲冲地推门进来,仿佛带来了一整个菜市场的烟火气。
中午时分,家里便飘着饭菜香,有了人气儿。
赵大妈手艺不错,她蒸的馒头松软如云,炖的排骨酥烂入味,就连最普通的青菜炒饭也能做出不一样的滋味。
最让我惊讶的是,她竟然会做老伴儿最拿手的"醋溜白菜"——那是我最爱吃的一道菜,老伴儿在世时经常做给我吃。
"这是王师傅的拿手菜,当年在厂里食堂,我就经常看她做。"赵大妈边炒菜边解释道,"看多了,也就学会了。"
我没说话,只是默默地吃着,心里泛起一阵酸楚。
原来,赵大妈和老伴儿早就认识,只是我竟然不知道。
日子仿佛回到了从前有老伴儿在的样子,但我心里清楚,那个熟悉的身影再也不会回来。
我常常在饭桌前发呆,筷子夹着菜忘了送进嘴里,眼前浮现的是老伴儿忙碌的身影。
那个曾经坐在我对面,絮絮叨叨讲着厂里大大小小事情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对着空气发呆。
赵大妈总是不动声色地把我唤回现实:"杨老头,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她从不问我在想什么,好像心里都明白。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赵大妈开始叫我"杨老头",像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我也不反感,反而觉得亲切,仿佛这个称呼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看到我们一起买菜回来,总会意味深长地笑,有时还会开玩笑说:"杨工,您这是找到伴儿了?"
每次我都会慌忙解释:"别胡说,赵大妈就是帮我搭个伙。"
而赵大妈则一脸笑意,从不解释,任凭他们打趣。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心情渐渐好转,不再整日沉浸在失去老伴儿的悲痛中。
偶尔,我还会主动打开许久不看的电视机,听赵大妈讲讲小区里的新鲜事。
"老李头家的孙子考上了北京大学,昨天全楼都放鞭炮庆祝呢!"
"三单元的张大姐种的月季开花了,红得跟火一样。"
"小区新来了个跳广场舞的团队,听说领队是个退休的舞蹈老师。"
这些琐碎的生活小事,慢慢地填补了我空落落的心。
可今天,她突然说要走。
在我愣神的片刻,赵大妈已经收拾好了围裙,站在门口准备离开。
"等等,"我急忙叫住她,"到底为什么突然不干了?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我的声音有些发颤,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这半年来,赵大妈的陪伴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赵大妈深吸一口气,眼睛看向窗外的梧桐树,那是一棵已经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老树,见证了小区的沧桑变迁。
"杨守仁,"她难得地叫我全名,"你总是对着饭菜发呆,眼神里全是过去。我想,也许是我不够好,让你想起了王师傅做的饭菜。"
我一怔,王师傅是我老伴儿在厂里的称呼,只有熟识多年的老工友才这么叫她。
"那时候厂里聚餐,大家都爱吃王师傅做的菜,我也曾跟她学过几手。"赵大妈继续说道,声音低沉,"可我知道,我做得再像,也不是她。"
听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
原来赵大妈这半年来,一直在努力模仿老伴儿的做菜方式,就是想让我找回一些熟悉的感觉。
"你这是何苦呢?"我声音哽咽,"老伴儿走了,我就是一根枯木,哪还有什么盼头?"
赵桂珍坐到我对面,手上的老茧在阳光下格外明显,那是几十年家务劳动留下的印记。
"杨守仁,人活一辈子,苦也好甜也罢,总要往前看。我丈夫走得早,这么多年我不也过来了吗?"她语气坚定,"你不能让自己停在原地,那对不起你老伴儿在天之灵。"
"王师傅生前最疼你,要是看到你这样,该多心疼啊。"
听她这么说,我心头一酸,眼泪不住地往下掉。
是啊,老伴儿生前最怕我一个人孤单,总担心自己先走了,我会照顾不好自己。
她甚至在住院期间,还专门叮嘱病友照顾我,生怕我连饭都吃不上。
"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过…"我喃喃道。
"你看我,我不也是一样吗?儿子在外地,一年难得回来一次。"赵大妈叹了口气,"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儿女有儿女的生活,我们有我们的活法。"
我沉默许久,突然想起老伴儿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人这辈子,要学会放下,也要学会拾起。"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赵大妈说的话。
她走后,我的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冷清,孤独,没有生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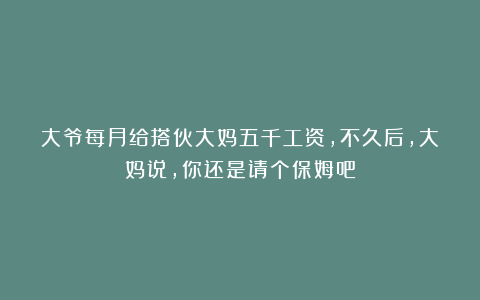
我翻出了尘封已久的相册,看着老伴儿和我年轻时的照片:工厂门前的合影,领结婚证时的笑脸,带着厂里职工去北戴河旅游的场景…一张张照片,记录着我们共同走过的岁月。
有一张照片特别引人注目,那是八十年代厂里组织的联欢会,老伴儿和赵大妈站在一起,两人都穿着厂里统一发的蓝色工装,笑得那么灿烂。
原来,她们的交情比我想象的还要深。
我又想起赵大妈临走时说的话:"杨守仁,我不是要抢王师傅的位置,我只是看不得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咱们都老了,相互有个照应,不好吗?"
几天的独处让我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老伴儿走了,不代表我的生活也要跟着结束。
或许,接受赵大妈的好意,不是对老伴儿的背叛,而是对生活的尊重。
我早早起床,煮了一锅粥,切了些咸菜,还特意跑到小区门口的早点摊买了两个刚出炉的肉包子。
七点半,我站在赵大妈家门口,深吸一口气,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赵大妈一脸惊讶地看着我,头发还有些凌乱,显然刚起不久。
"杨老头,你这是…"
"赵大妈,我想明白了,"我直视着她的眼睛,"以后,我们一起做饭吧。搭伙,就该有个伙字的样子。"
赵大妈愣在门口,眼圈有些泛红。
"那五千块钱——"
"不提那个,"我打断她,"咱们就这样,一起过日子。"
我的话一出口,自己先愣住了。
这句"一起过日子",好像有些暧昧不清。
赵大妈似乎也察觉到了这点,脸上泛起一丝红晕,那红晕在她饱经风霜的脸上显得格外明显。
"杨老头,你这话说得,让人怪不好意思的。"她低头整理着衣角,语气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柔软。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有些慌乱地解释,"就是想说咱们年纪大了,相互有个照应。"
赵大妈轻轻地笑了,那笑容如同冬日里的一缕阳光,温暖而不刺眼:"我明白你的意思,不用解释。"
从那天起,我们的相处模式悄然改变。
不再是她单方面为我做饭洗衣,而是我们一起分担家务。
我教她如何修理收音机——那是我年轻时的特长;她教我如何包饺子——那是北方人过年必备的技能。
我们一起去菜市场,一起在楼下的棋牌室下象棋,甚至一起参加了小区组织的老年人健步走活动。
小区里的老头老太太都说我和赵大妈越来越像一对老伴儿,我也不再急着解释,只是笑笑。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笑容越来越多,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和赵大妈坐在阳台上乘凉,聊起了各自的过去。
"其实我早就认识你了,"赵大妈突然说道,"那时候你还是厂里最年轻的工程师,戴着眼镜,腋下夹着图纸,走路都风风火火的。"
我惊讶地看着她:"你怎么从来没提过?"
"提这个干啥?都是过去的事了。"赵大妈笑着摇摇头,"那会儿厂里很多姑娘都偷偷议论你,说杨工程师长得帅,又有本事。"
我忍不住哈哈大笑:"那时候我可不知道还有这事!"
"可不是嘛,后来你娶了王师傅,大家都说你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赵大妈眼里闪烁着回忆的光芒,"王师傅人好,手艺也好,把你照顾得妥妥帖帖的。"
说到这里,她顿了顿,声音低了下来:"我那时候挺羡慕她的。"
我心头一震,不知该如何接话。
"羡慕她找到一个这么好的丈夫,"赵大妈继续说道,眼神却避开了我,"我那会儿刚从农村回来,丈夫已经……"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但我明白她的意思。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夜色渐深,远处的街灯一盏盏亮起,像是点缀在黑幕上的星星。
"桂珍,"我第一次叫她的名字,"谢谢你这半年来的照顾。"
她似乎被我突如其来的称呼惊到了,眼睛睁得大大的,随即又笑了:"杨老头,你还会叫人名字呢?我还以为你只会叫'赵大妈'呢!"
我也笑了,笑声在夜色中显得格外清脆。
春天来得特别早,二月底,小区的梅花就开了。
我和桂珍坐在花下的长椅上,阳光透过花瓣洒在我们身上,斑驳成一幅美丽的画。
"杨老头,你说咱们这样算什么呢?"桂珍突然问道。
"什么算什么?"我有些不解。
"就是咱们,不是亲戚,也不是夫妻,却天天在一起。"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困惑,"小区里人都说闲话。"
我沉思片刻,握住了她粗糙的手:"咱们这个年纪,还在乎那些闲话做什么?"
桂珍的手在我掌心微微颤抖,却没有抽开。
"守仁,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咱们年轻时认识,会不会走到一起?"她轻声问道,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
我没有立即回答。
年轻时的我们各有各的缘分,各有各的路要走。
我和老伴儿相濡以沫四十多年,她和她丈夫虽然天人永隔,但那份情感也是真实存在过的。
"桂珍,"我认真地看着她,"年轻时的事,谁也说不准。但现在,我们在一起,是命运的安排。"
"你知道吗?我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孤独,老伴儿走后,我以为自己会这样孤独终老。"我继续说道,"是你,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桂珍的眼睛湿润了,她轻轻靠在我肩膀上,什么话也没说。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看着花开花落,听着远处传来的鸟叫声。
小区里的老人们从我们身边走过,有的点头微笑,有的故意放慢脚步多看几眼。
但我们都不在意。
我知道,我们都是被岁月打磨过的糟糠,在彼此的陪伴中,找到了晚年生活最珍贵的温暖。
"杨老头,你说王师傅在天上看到我们这样,会不会怪我?"桂珍突然问道。
我笑了笑,望向蓝天:"她啊,肯定会说,'你们两个老东西,好好的,别瞎折腾'。"
桂珍也笑了,眼泪却顺着脸颊滑落:"那你觉得,我们这样,算不算是'瞎折腾'?"
我摇摇头,坚定地说:"不算。人活一辈子,不就是为了寻找温暖吗?我们相互取暖,有什么不对?"
远处的梅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如同点头赞同。
我们的身后,是各自走过的漫长岁月;而前方,虽然不会太远,但至少不再孤单。
这一刻,我仿佛听到了老伴儿在天上的叮嘱:"好好活着,别辜负了大好时光。"
春风拂过,带走了最后一点寒意。
我和桂珍相视一笑,默契地站起身,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走去。
她的家,我的家,如今都是我们的家。
我们是岁月中的糟糠,相依为命,共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