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汉武帝,人们总会想到他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雄才大略。但也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这位强势帝王到了晚年,突然对自己穷兵黩武的行为追悔莫及,不仅下 “轮台诏” 反思过错,甚至痛骂自己 “即位以来,所为狂悖”。这个故事被写进《资治通鉴》,成了许多人评价汉武帝的重要依据。可如果翻开更早的《汉书》,会发现这段 “悔过” 的记载竟无迹可寻。
汉武帝 “晚年悔过” 这档子事,到底是历史真相,还是被后人刻意塑造的故事? 说汉武帝 “晚年悔过”,最核心的依据是《资治通鉴》里的一段记载。征和四年(公元前 89 年),汉武帝从泰山封禅归来,突然表态:“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段话分量极重,几乎是全盘否定了自己数十年的执政生涯。书中还说,汉武帝因此驱逐方士、停止征伐,并下 “轮台诏” 系统反思过错,史称 “轮台悔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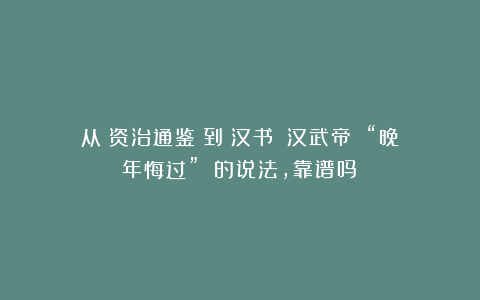
但这个说法,在《汉书》里找不到任何佐证。《汉书》作为记载西汉历史的权威正史,详细记录了汉武帝的言行和 “轮台诏” 原文,却压根没提 “所为狂悖” 这类自我否定的话。更关键的是,“轮台诏” 的真实内容,与 “悔过” 相去甚远。
当时桑弘羊等大臣建议在西域轮台驻军屯田,汉武帝驳回了这个提议,理由是 “贰师将军(李广利)败军,士卒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认为此时不宜再劳民伤财。诏书中还明确强调 “毋乏武备”,要求地方官 “进畜马方略,补边状”,显然是短期调整策略,而非否定对匈奴的整体战略。 从常理来看,汉武帝也不太可能说出 “所为狂悖” 这样的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帝王之一,一生都在践行 “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的信念。泰山封禅本是彰显功业的大典,他刚在泰山宣告自己的成就,转头就痛骂自己 “狂悖”,这种转变未免太过突兀。更何况,若他真的彻底悔过,为何不在临终前调整核心决策层?
汉武帝临终前指定的顾命大臣,恰恰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霍光(霍去病之弟)、桑弘羊(主持军事后勤)、上官桀(沙场宿将)、金日磾(匈奴降将),这四个人要么是对外征伐的核心参与者,要么是军事体系的关键支柱,没有一个是主张 “休养生息” 的儒家文官。如果汉武帝真想否定过去的战略,绝不会留下这样一个班子。
更有力的证据,来自汉武帝去世四年后召开的 “盐铁会议”。会上,贤良文学(儒生代表)与桑弘羊等大臣激烈辩论,核心是要不要废除汉武帝时代的盐铁专卖、军事扩张等政策。若是汉武帝晚年真有 “悔过”,儒生们必然会引用他的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可《盐铁论》(会议记录)里,儒生们只敢说要 “复文帝之政”(回到汉文帝的休养生息路线),桑弘羊则反驳 “不宜害先帝之功”,双方都对 “汉武帝悔过” 一事绝口不提 —— 显然,当时根本没有这个说法。
那么,《资治通鉴》里的 “晚年悔过” 是从哪来的?考证发现,这段记载其实源自一本叫《汉武故事》的野史。这本书充斥着神鬼传说,比如汉武帝与西王母相会等,可信度极低。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为何要引用这样不靠谱的材料? 这与北宋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北宋儒家文官集团掌权,推行 “重文轻武” 政策,对外常以妥协求安。他们需要塑造一个 “悔过” 的汉武帝,来证明 “穷兵黩武必招祸”,从而为自己的妥协政策辩护。
把汉武帝描绘成晚年悔过的 “暴君”,就能暗示:对外强硬没有好结果,不如像北宋这样息事宁人。
但历史的对比很残酷。汉武帝去世后,西汉延续了他的战略,最终彻底打垮匈奴、控制西域,迎来 “昭宣中兴”;而《资治通鉴》成书 40 年后,北宋就被金兵攻破汴京,酿成 “靖康之耻”。
可见,把对外强硬污名化为 “狂悖”,把妥协求安美化为 “明智”,本身就是对历史的扭曲。 回到汉武帝本人,他或许对个别战役的失利有过反思(比如李广利兵败),也确实调整过短期策略,但从未否定过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根本战略。这些功业让中原文明摆脱了匈奴的威胁,为中华文明的延续奠定了基础,绝非 “狂悖” 之举。
历史有时候会被立场裹挟,儒家文官集团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治正确,不惜从野史中找材料,给汉武帝贴上 “晚年悔过” 的标签。但只要翻开《汉书》,看看 “轮台诏” 的原文,看看汉武帝留下的顾命大臣名单,就会发现: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终其一生都为自己的选择骄傲。所谓 “悔过”,不过是后人强加给他的故事罢了。
《汉书武帝纪》《汉书西域传》 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 桓宽《盐铁论》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