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的西安已进入盛夏,东姜村考古工地的地表温度持续攀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勘探队员们正顶着烈日,对这片位于雁塔区南部、北临西安绕城高速的建筑用地进行例行勘探。
谁也没想到,这次看似平常的勘探,即将揭开一段尘封千年的异国质子往事。
墓室
这片区域西距皂河仅2.5千米,地下水位偏高,土层呈现出典型的湿陷性黄土特征。
发掘工作从4月正式启动。随着探方逐层下挖,考古队员们逐渐揭露出这座编号M15的墓葬轮廓。
6月15日,当发掘至距地表4.2米深处,探铲突然触碰到坚硬的砖砌结构。技术人员立即调整工作方案,改用小型手铲进行精细清理。
随着青砖表面菱形纹饰渐次显露,一座保存相对完整的唐代墓葬终于重见天日。
这座坐北朝南、方向193°的墓葬,由长斜坡墓道、过洞、天井、甬道及墓室组成,其形制与同时期关中地区中型唐墓高度吻合。
最先清理的是墓道部分,这个平面略呈梯形的斜坡状结构,东西两壁可见清晰的工具修整痕迹。
当考古队员清理至墓道底部时,在距地表5.6米处发现了第一处盗洞,直径约0.8米的圆形孔洞直插墓室,表明该墓早经盗扰。
在墓道东壁,考古人员发现了成组的生肖陶俑和塔式罐残片,这些高约25厘米的陶质明器,部分已残,但人身服饰的细部刻画仍清晰可辨。
墓中出土的天王俑和镇墓兽
从墓葬形制看,这座单室土洞墓呈现出典型的唐代中晚期特征。墓道长12.6米,宽1.1-1.4米,斜坡坡度22°,与同时期长安近郊唐墓数据完全吻合。
过洞与天井的组合,既符合唐代中型墓葬“一过洞一天井”的常见形制,其天井四壁保留的脚窝又显示出施工时的临时通道功能。
在甬道北端,考古人员发现了该墓的墓志。墓志为青石质,由盖、志两部分组成。志盖盝顶方形,顶面四周阴刻团云纹和宝相花纹,四刹阴刻牡丹纹。
正中刻划阴线方格,阴刻篆书“大唐故金府君墓志铭”3行9字。盖边长38、刹面宽7、盖顶边长30、厚5厘米。
志石正方形,四侧减地团云纹,志面阴刻棋盘格,其内楷书铭文25行,满行25字,共557字。志石边长38、厚9厘米。墓室中还出土了开元通宝钱币等遗物。
墓中出土的生肖俑
经考古专家们释读志文得知,墓主金泳,新罗国王堂兄金义让之孙,其父亦曾任唐廷质子。他的人生轨迹,恰似一部微缩的唐罗关系史。
这位新罗质子承袭父祖两代入唐宿卫的传统,这种父子相继的袭质现象,实为安史之乱后唐罗交通受阻的特殊产物,其生命历程深深镌刻着唐朝质子制度的时代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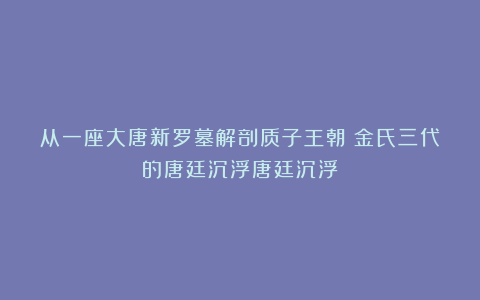
金泳出身新罗王族旁支,其祖父金义让作为新罗国王堂兄,于开元初年踏上入唐宿卫之路,最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试太常卿。
这种家族传承在金泳父亲身上得到延续,史载其父亦宿卫唐廷,获授中散大夫、光禄少卿。这种世代相继的质子身份,既体现了新罗对唐廷的臣服姿态,也构筑起唐罗关系中特殊的人才交流通道。
金泳的仕途呈现鲜明的“唐—新罗”双轨特征。大历三年(768年),他以宣慰副使身份首赴新罗,获授将仕郎、试韩王府兵曹参军。
此次出使恰逢新罗国王金乾运更迭之际,金泳作为唐廷特使参与对新罗君主的册封,彰显其作为唐廷代理人的特殊地位。
贞元元年(785年),他再度以吊祭册立副使身份出使新罗,此时已官至试卫尉少卿,更获准兼任蕃长,成为迄今所见唯一被唐廷任命为新罗蕃长、负责管理在唐新罗侨民的质子,是唐廷在新罗事务中的重要斡旋者。
墓中出土的动物俑
尽管金泳终其一生未返故国,但其在唐活动远超普通质子范畴。贞元十年(794年),这位游走于两种文化间的外交家病逝于长安太平里馆第,其葬礼由长安县令亲自主持,逝后获赠象征沟通渤海-新罗枢纽的登州都督衔,安葬于城南毕原家族墓地。
值得注意的是,其三子金士烈因父病出家为僧的记载,侧面反映出质子家族在唐社会的文化适应与身份认同困境。
唐朝新罗质子制度可追溯至隋唐与高句丽、百济的旧有惯例,但新罗质子群体呈现出独特的发展轨迹。
据《旧唐书·东夷列传》记载,新罗“每岁遣子弟宿卫”,这种常态化质子派遣机制,实质是东亚朝贡体系下宗藩秩序的具体实践。
唐朝通过接纳新罗质子,既获得牵制新罗的政治筹码,又构建起文化输出的特殊管道。新罗质子选拔严格遵循王族旁支原则,如金泳家族三代质子的经历所示,既保持血统尊贵性,又避免核心王权旁落。
唐朝则建立完整的质子待遇体系:授予散官职事官衔,如金泳所任“试卫尉少卿”;提供外交实践平台,使其参与对新罗的册封事务;允许质子在唐组建家庭,金泳与太原王氏的联姻即是典型案例。
质子在唐期间系统接受儒家教育,如金泳家族三代质子皆精通汉文,其墓志铭文采斐然,体现新罗上层对唐朝文化的深度认同。这种文化浸润反向推动了新罗官制、法律、佛教的汉化进程。
志盖铭文拓片
同时,质子制度为唐罗关系提供了柔性缓冲机制。当新罗与唐朝发生边境摩擦时,质子作为“人质”的存在,往往成为外交谈判的重要筹码。
金泳两次出使新罗的经历表明,质子群体已演变为唐廷对罗事务的专职外交官。
金泳墓志最后记载的“葬于城南毕原之北家族葬地”,不仅是个体生命的终焉之所,更是唐朝新罗质子制度的历史坐标。
这些质子如同文化使者,在长安与庆州之间架起理解之桥,其人生轨迹折射出东亚世界秩序的独特运行逻辑。
当我们凝视这座沉睡千年的墓葬时,看到的不仅是个体命运,更是一个帝国处理对外关系的智慧结晶。
·END·
点亮红心❤,以示鼓励^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