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被遮蔽的中华文明派生近代西方的事实
近代世界文明的格局,长久以来被“西方中心论”的宏大叙事所支配。这一叙事宣称,欧洲自古希腊罗马以来一直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其近代的崛起被描绘为一场内在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单线进步,仿佛一切智慧与进步的种子早已深埋于西方的古典传统之中。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条被广为传颂的西方文明演进之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套被精心建构的神话。本文旨在揭示一个被长期遮蔽的历史真相:近代欧洲文明并非“复兴”其古典源头,而是在17至18世纪,通过系统性地吸收、转化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从而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建构。 这是一场跨越洲际的、从“神州”到“欧洲”的文明知识大挪移。
这场挪移的核心媒介是来华的耶稣会士。他们深入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体,惊异地发现其典章制度、哲学思想、科学技术乃至历史记载的完备程度,远非欧洲所能及。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斯塔特曼(Alexander Statman)所指出的,当时的欧洲精英将中国视为一个“古老智慧的宝库”(repository of ancient wisdom),[1]相信那里保存着西方在大洪水中失落的“原初科学”。为了调和这种文明落差并为自身的知识汲取行动正名,他们巧妙地构建了一套“神学—历史”叙事,宣称华夏文明是诺亚子孙东迁所建,中国先民的成就实为西方“创世祖产”的海外遗存。
由此,一场规模空前的知识转移工程得以在“物归原主”的旗号下展开。从莱布尼茨通过《易经》探寻“表意汉字”的哲学梦想,到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指示马戛尔尼使团全力搜集中国科技百科全书的具体指令,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与机构都深度参与了这场对中国知识体系的“发掘”与“转运”。经由他们的翻译、阐释和重构,源自“神州”的哲学思想、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历史方法,被系统地植入欧洲的思想土壤,并逐渐被消化、吸收为西方“古典传统”与现代性的主要部分。
因此,近代欧洲文明的建构,是其自身双向互动的过程:它既是欧洲内部的社会变革,也是一场对外部高级文明成果的创造性挪用。本书将追溯这条从“神州”到“欧洲”的知识传播与转化路径,剖析中国知识体系如何作为关键性的外部变量,参与了欧洲现代性的打造,从而对“欧洲何以成为欧洲(西方何以成为西方)”这一根本性问题,提供一个全新的、基于全球史视野的解答。
第一章 神学外衣下的文明攫取:耶稣会士的使命与叙事
近代欧洲文明的建构,始于一场在神圣叙事下,针对中国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汲取运动。其核心执行者耶稣会士,为其知识转移行为披上了一件精心编织的“神学外衣”,将一场文明的攫取,巧妙转化为神圣的“使命”与“认祖归宗”。
一、“伊甸园种子”说:文明攫取的神学合法性
当耶稣会士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在典章制度、哲学思想和物质文明上都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这种巨大的文明落差,对其原有的世界观构成了严峻挑战。为调和这一矛盾,他们援引并发展了一套“古代神学”(Prisca Theologia)理论,为其后的行动确立合法性。
该理论的核心论点为:人类曾拥有一个由上帝启示的、统一而完美的原初智慧。
美国惠特沃思大学的历史学家安东尼·克拉克(Anthony Clark)写道:
对利玛窦而言,必须在中国历史中找到(伊甸园)种子——“逻各斯基因”(spermatikos logos);可以在华夏思想史或儒家经典里发现其痕迹,而《易经》等哲学论著中则潜藏着这样的“道的种子”。……欧洲传教士到东方来时,有一个先验的假设:中国古籍包含着“逻各斯基因”,那是由于(西方)古代神学被嫁接于“道”的缘故。[2]
美国学者乌尔里希·莱纳(Ulrich Lehner)指出,神父们断言儒学中蕴含着“亚当真知的种子”[3]。这套智慧在大洪水后在欧洲消失,所幸被诺亚的子孙带至东方,并在中国得到了近乎完美的保存。因此,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并非独立创造的成果,而被视为“神启逻各斯的知识宝库”(China became the repository of the logos of divine revelation)[4]。
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的研究集中体现了这一观点,他将伏羲比附为《圣经》中的先知,认为《易经》是蕴含了“从亚当到诺亚的上帝启示”的密码本。[5] 白晋和傅圣泽等耶稣会士均认同:“古代中国并不仅仅属于华夏民族,而是属于整个的早期人类社会。……’中国成为神启逻各斯的知识宝库’(China became the repository of the logos of divine revelation)。”
莱布尼茨通过白晋接触到《易经》的,获得了宋代邵雍绘制的《六十四卦图》。莱布尼茨认为:“这些卦爻(易象)好比‘种子’,它们蕴含着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密码。”他还说:“伏羲八卦是学术上最古老的丰碑。”[6]
莱布尼茨说:“中国资料可以帮助欧洲人对希腊—罗马历史的重塑”。
由此,耶稣会士的使命发生了根本性颠倒:从向“异教徒”传播福音,转变为以神的名义,从中国找回欧洲失落的“古老智慧”。美国历史学家斯塔特曼(Alexander Statman)精准概括道:“18世纪初,许多欧洲人相信……已失传的科学和知识都可以被恢复……于是,中国成为欧洲启蒙运动的智慧宝库。”[7] 这套“伊甸园种子”说完美解决了他们的认知困境:既然文明成果本属“神造”,中国只是暂时保管者;那么,西方将其“取回”则是天经地义的。
图解:耶稣会士宣称,原以为大洪水吞没了西方“原初智慧”;后者却幸运地被诺亚子嗣带到了中国,其中就有作为人类文明源头和源泉的《易经》
二、“西来说”的缘起与学术包装
为给神学叙事披上学术外衣,耶稣会士进一步附会中国上古史,构建了早期“中国文明西来说”。他们宣称华夏先祖是诺亚子孙,大洪水后东迁至神州大地。正如瑞士历史学家恩斯·艾普(Urs App)所揭示的,坦普尔爵士、拉姆塞等人不断强调的“中国是最古老的国家……难怪我们能从她那里找到‘诺亚传统’的痕迹!”[8]
这种将中国历史纳入圣经谱系的做法,有着明确的政治与文化目的。一方面试图将中国文明收编为西方“神圣历史”的分支,否定其独立起源的伟大性;另一方面为大规模翻译输出中国典籍提供“物归原主”的正当理由。中国的价值在于其为西方重建自身传统所能提供的养料。
三、神学叙事下的真实使命:文明火种的转移
剥开神学外衣,耶稣会士行动的实质清晰可见:为一个在文明层面上近乎“空白”的欧洲,转移文明的火种。中国学者李零在《我们的经典》系列研究中,通过对《易经》等典籍的考辨,强调了先秦中国思想世界的丰富性与原创性,这种自成体系的智慧绝非“神启”可概括。然而在耶稣会士叙事中,这一切都被解构为西方“古代神学”的衍生物。
他们的核心工作是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转移。正如密歇根大学教授大卫·波特(David Porter)所言,欧洲的近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即“中国化”(Sinicizing)。[9]。从利玛窦到白晋,几代耶稣会士深入钻研汉语文献,目的就是识别、筛选并输送这些“文明种子”。其所转移的“火种”涵盖现代西方文明几乎所有基础成分:
1.语言文字:将汉字表意概念植入欧洲方言,创造出现代西方语文
2.知识体系:翻译儒家经典、科技典籍,构建欧洲哲学与科学思想
3.历史架构:利用中国历史年表和编纂方法,建构西方“线性历史”
4.制度模型: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央集权模式成为欧洲国家建设蓝图
综上所述,耶稣会士通过“伊甸园种子”说和“西来说”,成功将其知识转移行为伪装成神圣的“文明认领”运动。这套神学叙事不仅提供了合法性,更深刻影响了数百年的西方中心历史观,遮蔽了现代西方文明生成的真正源头。
第二章 知识转移的机制:文献、概念、历史架构与制度的西传
在“神学外衣”的掩护下,耶稣会士开启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知识转移工程。他们不仅翻译文献,更通过一系列精妙的机制,将中国知识体系的核心成分——尤其是表意文字概念、历史编纂方法和政治制度——植入欧洲的思想土壤,从而为近代西方文明的建构提供了基本框架。
一、汉字表意概念的西植:文明媒介的再造
近代以前的欧洲语言文字,作为表音符号,主要功能是记录语音,难以胜任表达复杂、抽象的普遍性概念。耶稣会士发现,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形—意”直接关联的特性,使其成为表达哲学与科学概念的理想媒介。
莱布尼茨对此极为着迷,他通过白晋接触到《易经》和邵雍的《六十四卦图》,将其卦爻系统视为蕴含宇宙万事万物密码的“种子”[10]。他设想创造一种基于汉字原理的“通用字符”(Characteristica Universalis),认为这种符号系统能够超越语言障碍,进行精确的思想交流与逻辑演算。尽管这一理想并未完全实现,但其思想深刻影响了欧洲语言的发展。汉字所体现的“一字一概念”的表意模式,为欧洲各主要语言(英、法、德等)大规模创造抽象名词和学术术语提供了范式参考,从而将这些民族方言从“部落土话”提升为能够进行深刻思想交流的“文明媒介”。
二、中国历史架构的挪用:西方“世界历史”的诞生
18世纪前的欧洲,在史学上深受《圣经》年代学的束缚,缺乏客观、人文的世俗历史框架。卷帙浩繁、连续不断的中国历史记载,为他们提供了全新的时间尺度和编纂范例。
耶稣会士系统地将中国历史纪年、史料编纂方法以及“稽古右文”的史学观念引入欧洲。这直接导致了欧洲史学的一场革命:从17世纪“以神为本、以《创世纪》为开端”的圣经普世历史,转向18世纪“以人为本、以伏羲为开端”的启蒙世界历史。正如文件所示,后者大量使用中国资料来充实和建构古代西方的历史。
瑞士历史学家恩斯·艾普(Urs App)的研究证实,坦普尔爵士、拉姆塞等欧洲精英声称“很容易在中国文献中找到古希腊的种子”,并不断强调中国是“许多西方学说的源泉”。[11]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借鉴了中国的历史编纂形式,甚至试图将西方文明的源头“嫁接”到东方的历史树干上。中国坚实的历史记载,成为了欧洲建构自身“古典传统”和线性进步历史观不可或缺的参考框架和年代学基石。
三、制度与知识的系统性转移:从文官考试到百科全书
知识转移远不止于思想层面,更延伸至实实在在的制度与科技领域。
1.制度移植:中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科举制)通过耶稣会士的详细记述传入欧洲,其“选贤举能”的理念对欧洲的任官制度产生巨大冲击,最终被英国、法国等国家借鉴和采用,成为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雏形。秦朝的中央集权一元化管理模式,也为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构建提供了远东的蓝图。
2.科技知识的转移:耶稣会士和中国信徒合作,大量翻译中国的科技类典籍。最具代表性的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正如英国华威大学的玛戈特·芬恩(Margot Finn)所述,马戛尔尼使团带回的绘有中国生产技术的墙纸(其图样来源正是《天工开物》),直接影响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意识和技术改良]。[12]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班克斯在给马戛尔尼的信中,直言不讳地将中国称为“汇集文明遗产的地方”,并指出其科技可供西方“盗用(stolen)或是基于她的成就进行重新发明(reinvented)”。[13]
3.“百科全书”计划的东方灵感:莱布尼茨的“满语百科全书之梦”(Leibniz’s Dream of Manchu Encyclopedia)和后来法国狄德罗的《百科全书》计划,其背后都有中国类书(如《永乐大典》)的影子。莱布尼茨希望通过满文(一种欧洲人相对易学的表音文字)为中介,系统性地收集、整理和吸收中国的百科知识,建立一个“中国知识库”(Chinese repository)。[14]这种对知识进行系统分类、汇总的宏大抱负,无疑受到了中国庞大类书传统的启发。
综上所述,耶稣会士的知识转移机制是多层次、系统性的。他们通过概念移植、历史借鉴、制度模仿和技术引进,将中国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深度嵌入正在形成中的西方现代文明之中。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复制,而是一种深刻的、带有目的性的“创造性转化”,其结果是:源自“神州”的文明成果,经过重新阐释和包装,最终被建构为“欧洲”的传统与成就,从而遮蔽了其真正的来源。
17—18世纪,在欧洲王公与精英的资助和指令下,来华的耶稣会士借口找回“诺亚方舟遗产”,基于中国古籍塑造了全部的西方传统和源头。他们成功地进行了两种“置换”:
①文化:拜神迷信→知性神学(自然神学)
②故土:文化荒漠→文化源泉(两希传统)
弗兰克、霍布森和彭穆兰等学者都指出,欧洲是从“以明清中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边缘开始崛起的。[15]他们还认为,近代欧洲的发迹是基于早先中国的成就的,而与西方本身的特质和历史没有关系。[16]
第三章 案例研究:莱布尼茨、满文中介与百科全书计划
前文揭示了耶稣会士知识转移的宏观机制,本章将通过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这一关键人物及其推动的“满文中介”项目这一典型个案,深入剖析这场文明转移工程的具体运作模式,即文件中所言的清朝士人、耶稣会士与欧洲精英的“三结合”如何在实际层面展开。
一、莱布尼茨:“西学中源”的枢纽与理论旗手
莱布尼茨是欧洲启蒙时代初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系统接收、阐释并推广耶稣会士从中国传来知识的核心枢纽。他虽未亲至中国,但与白晋、闵明我等多位在华耶稣会士保持着长期密切的通信往来。
他对中国文明的推崇远超同侪。他不仅盛赞“伏羲八卦是学术上最古老的丰碑”,更将从白晋处获得的《易经》六十四卦图视为蕴含宇宙万事万物密码的“种子”。[17]莱布尼茨坚信:中国保存了西方已然遗失的“原初科学”与“普遍真理”。
二、“满文中介”:知识虹吸的战略通道
要实现大规模的知识转移,一个巨大的障碍是汉语的难度。汉字对于欧洲学者而言犹如天书。解决方案出人意料地落在了满文之上。
清朝入主中原后,试图将满语满文变成“国语”,但为了统治需要,大量翻译汉文典籍。满文作为拼音文字,其语法和拼写对于熟悉“拉丁字母”(在明朝儒士帮助下的升级版拉丁字母,另文论证)的耶稣会士来说,远比汉字容易掌握。这就形成了一个绝佳的“知识虹吸”通道:
1.易于理解:耶稣会士可以相对快速地学会满文。
2.内容宝库:满文翻译了大量汉文经典、政书、史册和科技文献,涵盖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知识。
3.中转桥梁:耶稣会士可以通过满文版本来理解和转译汉文原著的内涵,从而绕过直接攻读汉字的巨大困难。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萨雷拉(Mårten Saarela)将其称为“清朝—欧洲之收集中国知识工程”(Joint Manchu—European project of collecting Chinese knowledge)。[18]耶稣会士们积极参与清廷的编书修典工作(如编纂《满汉字典》),其目的远不止于服务清朝,更是为了以清廷的学术工程为平台,系统地获取和整理他们所需的知识资源。
图解 莱布尼茨希望(让耶稣会士)通过同属字母表音、因而容易理解的满文,来识别和收集中国百科知识
三、“莱布尼茨的百科全书之梦”与清廷的“三结合”
莱布尼茨的宏大构想远不止于零星的信件交流。他怀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编纂一部基于满文文献的“中国百科全书”(Leibniz’s Dream of Manchu Encyclopedia)。[19]
这个梦想的具体运作,完美体现了“三结合”的模式:
1.清廷朝野(中国士人):提供了知识的最初源头(汉文典籍)、翻译成果(满文文献)以及进行学术活动的官方平台(如钦天监、编书机构)。康熙皇帝本人对西学的兴趣,为耶稣会士的活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空间。
2.在华耶稣会士:他们扮演了双向中介和一线矿工的角色。他们一方面深入学习满汉语言,融入清朝的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他们甄别、筛选、翻译(或将满文版转写为拉丁文)并向欧洲输送这些知识。他们是知识虹吸管的具体操作者。
3.欧洲精英(以莱布尼茨为代表):他们是知识的接收端、整合者和理论升华者。他们根据欧洲的需求,对来自东方的知识材料进行解读、阐释和重构,将其融入欧洲自身的哲学、科学与政治 discourse(话语体系)之中。
莱布尼茨在信中反复敦促耶稣会士们系统收集中国的各类知识,从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到伦理法律。他想要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书目,而是一个结构化的“中国知识库”(Chinese repository),这无疑是受到了中国《永乐大典》等巨型类书传统的启发,并直接预演了后来法国狄德罗《百科全书》的雄心。[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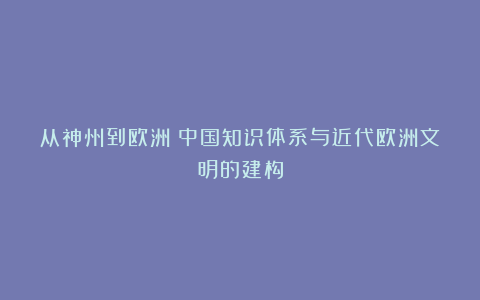
四、个案影响:从哲学到制度的全面启蒙
这一“三结合”模式的影响是具体而深远的:
1.在哲学上:莱布尼茨从《易经》中获得的灵感,参与塑造了欧洲理性主义哲学的发展。
2.在制度上:通过满文文献译介的中国官僚制度(如科举)和法律体系,为欧洲的政治思想家(如伏尔泰、魁奈)提供了批判欧洲旧制度的参照系和构建现代国家的远东蓝图。
3.在科学上:传输回去的中国技术图式(如《天工开物》中的农业和机械技术),为欧洲的农业革命和早期工业化提供了直接的灵感来源,如班克斯信件中所明确指示的那样。[21]
莱布尼茨与“满文中介”的案例表明,近代西方对中国知识体系的汲取,是一场有组织、有理论指导、有高效工具(“拉丁字母”+满文)、并深度嵌入当时中国学术体制内部的系统工程。“三结合”的模式使得耶稣会士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触和攫取中华文明的成果,并通过莱布尼茨这样的枢纽人物,将其转化为塑造欧洲现代性的关键思想资源。这一计划虽未完全实现,但其精神和路径却清晰地指明了18世纪欧洲“中国风”背后深刻的知识诉求,揭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建构过程中一个被遗忘的东方来源。
第四章 工业革命中的中国科技:马戛尔尼使团与《天工开物》的启示
前文论述了哲学、制度与概念层面的知识转移,自明末清初以来,耶稣会士便已扮演了系统窃取中国科技知识的先锋角色。他们通过翻译、信函和寄送书籍,将大量中国工艺知识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其中,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1637年)因其对农业、手工业技术的全面记载和精细绘图,尤受重视,早在17世纪便已被耶稣会士关注并西传,乃至被西方学者誉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至18世纪晚期,英国对华知识攫取的需求变得更为急切和系统化。马戛尔尼使团的访华,标志着这一活动从耶稣会士为主的、相对零散的传递,升级为由国家力量支持的、大规模、有组织的技术情报搜集行动。本章将聚焦于物质技术层面,剖析18世纪晚期中国科技知识如何通过具体渠道为欧洲的产业革命提供关键性的启示与推动。
以马戛尔尼使团系统性地知识搜集和《天工开物》等 的西传为典型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技术文明对西方工业化进程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一、使命之外的使命:有组织的技术情报搜集
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访华,其表面使命是谈判通商条约,虽以失败告终。然而,其另一项更深层、且最终取得巨大成功的使命,是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科技、经济与军事情报搜集。使团被精心组建为一个移动的“学术考察团”,成员包括科学家、医生、画家和技师,其任务是详尽记录中国的一切“有用知识”。
英国皇家学会主席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1743—1820) 是此次行动的幕后重要推手。他于1792年1月22日写给马戛尔尼的信(摘录):
阁下:谨随函附上一本中文书,供各位大人细阅,我习惯称之为“百科全书”;据说,这是共有数百卷的鸿篇巨制之一,它对(中华)帝国所有的机械装置和手工工具均有详解和图示。……另外,还附上七十卷不同类型的汉语文献,也涉及机械方面;其中包含我上次有幸遇到阁下时提到的关于中国(各方面)的简要统计资料,它对实用科学和装饰艺术皆有极大益处。……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汇集文明遗产的地方;在她那里,人类的思维达到完美境界时,将各种知识提升到了现在欧洲人所望尘莫及的高水平。……中国拥有无数项的文明赖以存在的科技,可供我们(西方)盗用(stolen),或是基于她的成就进行重新发明(reinvented)。……他们的瓷器是化学的杰作,欧洲人在这方面还是门外汉。……仅仅学习这些技艺就足以给西方带来无量福祉,但中国还拥有多少这样的古代智慧的残骸(黑科技),我们不得而知。[22]
信中的指令毫不掩饰其目的:“中国是一个汇集文明遗产的地方…………中国拥有无数项的文明赖以存在的科技,可供我们(西方)盗用(stolen),或是基于她的成就进行重新发明(reinvented)。”他随信附上一本中国科技百科全书(很可能是《古今图书集成》或类似著作的一册),要求使团按图索骥,验证和搜集相关技术。
班克斯(右)送给马戛尔尼(左)一本中国科技百科全书(鸿篇巨制当中的一册)[23]
二、《天工开物》的西渐及其技术影响
在使团搜集的诸多资料中,明末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的影响尤为凸显。这部百科全书式的科技巨著,详细记录了当时中国领先世界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并配有大量精美的工艺流程图解。
尽管《天工开物》在清中期后在中国本土一度失传,但其内容却通过耶稣会士和贸易渠道较早传入欧洲,并通过马戛尔尼使团带回的中国墙纸、绘画和器物得以强化和验证。英国华威大学的玛戈特·芬恩(Margot Finn)指出,牛津大学教授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的研究表明,马戛尔尼使团带回的中国墙纸上所绘的各种机械制造场景,其图样来源正是《天工开物》中的木版画插图:[24]
牛津大学教授马克辛·伯格(Maxine Berg)认为,尽管马戛尔尼使团在建立贸易关系方面失败了,但它在收集有关中国的“有用知识”方面却大功告成。仅在马戛尔尼带回的中国墙纸上,就有对各种机械制造的描绘。这些图画的来源是宋应星的《天工开物》。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探讨了当时中国技术和制造的诸多方面,并配有详细的木版画插图。……先前,威廉·马歇尔在其著作《约克郡农村经济》(1788)中,就中国墙纸如何传达如此有用的信息,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中的一页插图展示了扬谷机的原理。……托灵顿子爵(Viscount Torrington)于1789年访问克罗姆福德(一座新纺织厂所在地)时,曾将一幅中国画中的劳动场景,与该地区所体现的一个正在经历农业和工业革命的国家,联系起来。克罗姆福德“水资源丰富,岩石众多,人口众多,木材资源丰富,看起来就像一座中国城镇”。……马戛尔尼的墙纸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的制造业景象,当时英国正在推行自己的工厂生产体系。……墙纸内容必定强化了进步人士在产业上的企图心。……马戛尔尼使团带回的中国墙纸,俨然成为卓越制造工艺的写照;它见证了马戛尔尼外交的失败,也目睹了东西方之间交流和贸易的成功。……中国墙纸的影响遍布整个大不列颠,至少远及珀斯郡的布莱尔城堡和苏格兰西北海岸的埃格林顿城堡。[25]
这些图像和信息对正处在工业革命起步阶段的英国产生了直接而具体的影响:
1.农业机械:墙纸中描绘的扬谷机(扇车)工作原理,被直接参考并应用于英国农业机械的改良。威廉·马歇尔在其著作《约克郡农村经济》(1788)中,就曾详细分析中国墙纸上的扬谷机插图以说明其原理。
2.纺织技术:中国先进的纺纱、织布和提花技术,通过图像和实物(如丝绸样品)为英国纺织业的技术革新提供了参照。托灵顿子爵在1789年访问英国新纺织厂中心克罗姆福德时,曾将其水资源丰富、作坊林立的景象与一幅中国画中的劳动场景相联系,感叹其“看起来就像一座中国城镇”。[26]这表明中国的工业化生产图景为英国精英提供了现代化的视觉模型和野心蓝图。
3.制造业理念:马戛尔尼使团带回的“田园诗般的制造业景象”的墙纸,在英国各地庄园宅邸(如珀斯郡的布莱尔城堡)广泛张贴,它不仅是一种装饰,更是一种“卓越制造工艺”的视觉宣传,潜移默化地强化了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投身于产业革命的企图心。[27]
三、从“窃火”到“燎原”:中国技术知识的转化模式
马戛尔尼使团的行动,是耶稣会士知识转移活动的延续与升级。其模式可概括为:
1.识别目标:根据欧洲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如提高农业效率、革新纺织技术),有针对性地识别中国对应的先进技术。
2.系统搜集:通过多种手段(购买书籍、绘制图画、实地观察、聘请工匠)系统搜集技术信息,尤其重视带有精确图解的资料。
3.模仿与再发明:班克斯所用的“stolen”和“reinvented”二词精准概括了其最终目的。即先进行直接模仿,再根据本地材料和需求进行适应性改造和“再发明”,最终将东方技术转化为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
马戛尔尼使团的案例雄辩地证明,中国的技术文明是欧洲工业革命不可或缺的外部催化剂。从《天工开物》的工艺图说,到遍布英国庄园的中国墙纸,来自东方的技术信息以各种形式渗透进正在酝酿巨变的英国社会,为其提供了具体的技术蓝图、生产组织的视觉模型以及迈向工业化的雄心与自信。这一过程绝非偶然,而是一场由欧洲最高科学机构策划、国家力量支持的、系统性的“技术窃取与转化运动”。它清晰地表明,西方工业革命的“火种”,其中重要的一束,正是从遥远的“神州”取来,并在西方的土地上形成了燎原之势。
第六章 文明的重构与历史的讽刺
本文通过梳理耶稣会士的神学叙事、分析知识转移的具体机制、考察莱布尼茨的个案研究,并最终聚焦于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技术的系统性搜集,揭示了一段被长期遮蔽的全球史图景:近代欧洲文明的建构,并非其自身古典传统单纯“复兴”的结果,而是在17—18世纪通过系统性的、掠夺性的汲取中国知识体系,并辅以欺诈与暴力手段才得以实现的。这是一场在“神学”包装下,从神州到欧洲的文明劫掠与篡夺运动。
一、文明的劫掠与篡夺:被掩盖的暴力转移
本研究论证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多重根基,源于对中国知识体系的系统性攫取:
1.其哲学与概念工具,建立在对《易经》等中国典籍的误读与挪用之上,并将其成果归功于虚构的“希腊传统”;
2.其历史叙事与时间观念,盗用中国悠久连贯的历史记载所提供的框架,以建构自身虚假的古老性与线性进步史观;
3.其国家制度与文官体系,抄袭中国的中央集权模式和科举取士制度,却将其包装为欧洲的“政治创新”;
4.其工业革命的技术飞跃,则直接依赖于对《天工开物》等科技典籍所承载工艺的窃取,以及对中国工匠的诱骗与绑架,从而获得技术实现的关键人力资本。
然而,这一庞大的“窃火”工程完成后,其掠夺来源与暴力手段被迅速而系统地掩盖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叙事被精心构筑起来,将这一切成果归功于自身的“理性”与“天才”,而那个曾被其掠夺的老师,则被塑造成停滞落后的“他者”。历史的巨大讽刺莫过于此:强盗不仅洗劫了老师的家产,更依此编造了一段自己天生贵胄的神话,并将老师污蔑为乞丐。
二、当代反思:彻底祛魅与重建正义
揭开这段被掩盖的历史,对于当今世界具有至关重要的批判意义。
首先,它是对“西方中心论”的彻底祛魅与清算。它彻底撕破了所谓“欧洲奇迹”的神话,揭示其现代性的根基并非什么独特的理性或制度优势,而是一场持续数百年、跨洲际的知识与劳动力掠夺的结果。美国贝勒大学教授蒙赫洛(David E. Mungello)批评:所谓的近代欧洲从中国“借鉴”文化与物质文化,“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则是无耻的剽窃(scandalously plagiaristic)”。[28]
其次,它要求一种历史的正义。承认中国知识体系与工匠技艺对现代世界的奠基性贡献,绝非为了进行简单的功劳比较,而是为了还原历史真相,戳穿西方自我编造的神圣叙事。所谓“强烈的求知欲”,实质是贪婪的掠夺欲望;所谓“强大的转化能力”,其背后是转译大量中国典籍,并欺骗、利诱、绑架中国工匠为其实现技术破译和生产的残酷事实。忽略这一暴力维度,就是对历史的严重美化。
最后,它呼吁构建一种去殖民化的文明新叙事。这段历史提醒我们,西方现代性的“成功”路径,建立在对其他文明的劫掠之上,其模式不可复制,更绝不值得歌颂。面向未来,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绝不能依靠这种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知识霸权。我们必须彻底打破文明优劣的等级叙事,否定其掠夺历史的合法性,才能为一个真正基于平等、互鉴与合作的全球未来,扫清最大的思想障碍。
三、最终的呼应
回望历史,耶稣会士们带着“认领祖产”的虚伪面具而来,他们在中国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知识劫掠。他们盗走的文明火种,最终燃成了灼烧全球的殖民烈焰,并反过来试图焚毁其真正的源头。
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扑灭这虚假的火焰,还原历史的灰烬与创伤。这不仅是为了公正地评价过去,更是为了彻底告别那个由掠夺和谎言铸就的旧世界范式:真正的文明之光,源于自主创造与平等交流,绝不可能诞生于盗窃与压迫之上。唯有彻底认清西方现代性的暴力起源,我们才能打破其话语霸权,为所有被遮蔽、被压制的文明正名,共同开创一个真正公正的新纪元!让所有文明一起伟大,让人类和谐与共!
注释:
[1] Alexander Statman: A Global Enlightenment Western Progress and Chinese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p.107—110.
[2] Urs App: The Birth of Orienta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284-285.
[3] Ulrich L. Lehner: The Catholic Enlighte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16-117.
[4] Adeline Yen Mah: Watching the Tree to Catch a Hare, HarperCollins, 2001, p.24.
[5] Ulrich L. Lehner: The Catholic Enlighte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116-117.
[6] Urs App: The Birth of Orienta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284-285.
[7] Alexander Statman: A Global Enlightenment Western Progress and Chinese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3, p.107-110.
[8] Urs App: The Birth of Orienta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284-285.
[9] David Porter: Sinicizing Early Modernity: The Imperatives of Historical Cosmopolitanism,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Vol. 43, No. 3, China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Modernity (SPRING 2010),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0] Adeline Yen Mah: Watching the Tree to Catch a Hare, HarperCollins, 2001, p.24.
[11] Urs App: The Birth of Orienta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284-285.
12[] Kate Smith, Margot C. Fin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t Home,1757-1857, UCL Press, 2018, p.61-63.
[13] Neil Chambers: Letters Of Sir Joseph Banks, The, A Selection,1768-1820,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140-141.
[14] Mårten S.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p.122 and p.135.
[15] Gennaro Ascione: Concept Formation in Global Studies,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24, p.85.
[16] William R. Thompson, Leila Zakhirova: Racing to the Top,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73.
[17] Adeline Yen Mah: Watching the Tree to Catch a Hare, HarperCollins, 2001, p.24.
[18] Mårten S.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p.122 and p.135.
[19] Mårten S.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p.122 and p.135.
[20] Mårten S. Saarela: The Early Modern Travels of Manchu,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20, p.122 and p.135.
[21] Neil Chambers: Letters Of Sir Joseph Banks, The, A Selection,1768-1820,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140-141.
[22] Neil Chambers: Letters Of Sir Joseph Banks, The, A Selection,1768-1820,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0, p.140-141.
[23]资料来源:George Macartney,1st Earl Macartney &, Joseph Banks Portrait, Nation, Oxford Academy,1892.
[24] Kate Smith, Margot C. Fin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t Home,1757-1857, UCL Press, 2018, p.61-63.
[25] Kate Smith, Margot C. Fin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t Home,1757-1857, UCL Press, 2018, p.61-63.
[26] Kate Smith, Margot C. Fin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t Home,1757-1857, UCL Press, 2018, p.61-63.
[27] Kate Smith, Margot C. Finn: The East India Company at Home,1757-1857, UCL Press, 2018, p.61-63.
[28] David E. Mungello: 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 p.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