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最近写杜凤治系列时,有朋友评论说:’清朝是有意愚民。’ 这条评论不到半小时就被平台以 ‘无史料支撑‘ 为由删除了。
其实不止这位朋友,很多人都知道清朝文字狱盛行、民间识字率低迷,但具体有多低?
我列一组数据:明朝中后期民间识字率约 10%-15%(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到清朝中期竟跌至 5%-8%(《清代教育与大众文化水平》)。这种 ‘腰斩式’ 下滑绝非简单的 ‘愚民’ 标签能概括,而是清廷通过四套组合拳,系统性抽走了底层读书的根基。
壹
教育权:从 ‘理想化普及’ 到 ‘精英化收缩’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明朝建立了一套意图普及基层教育的硬规矩:
洪武八年定下 ‘每里设 1 所社学,15 岁以下孩子需入学‘(《明史・食货志》),理想状态下为官办免学费,穷学生可领笔墨;
当然,在实际执行中,社学因财政波动时兴时废,如正统年间广东社学 ‘十存一二‘,江南地区覆盖率相对较高,《醒世恒言》中可见 ‘乡村社学不分贫富收录‘ 的记载,而西北贫瘠县份常 ‘有令无实‘(《明代地方教育研究》)。
而与之相反的,清朝是主动的教育收缩:
- 断经费:康熙将社学经费划归士绅自筹,官府不再兜底;
- 设门槛:乾隆明确规定 ‘社学仅录身家清白、有科举潜力者’,实质将佃农、工匠子弟排除在外;
- 规模锐减:至嘉庆朝,全国社学数量仅为明朝中后期的 1/3,且多沦为士绅家族私学(《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动态对比: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繁荣期,社学在江南形成 ‘教育普及带’;清朝中期后,即使在富庶的珠三角,底层识字率也因教育权垄断而大幅下滑。
贰
文字狱:把 ‘识字’ 变成送命题
打开今日头条查看图片详情
明朝也有文字禁忌,但多针对朝堂,对民间启蒙相对宽松:
- 朱元璋虽兴 ‘表笺之祸‘,但民间《千字文》《百家姓》版本繁多,如万历年间苏州书坊刊印的《新镌百家姓》,甚至收录 ‘楚燕韩赵’ 等战国典故,未受干预。
清朝乾隆朝后的文字狱,则直接摧毁民间教育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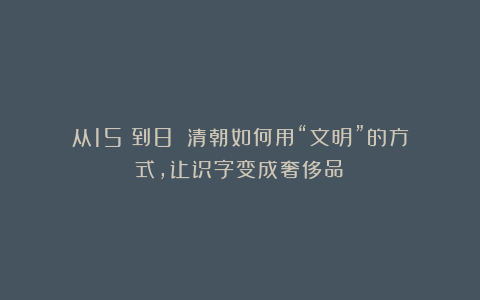
- 惨案实证:乾隆四十三年,江西私塾先生王锡侯注释《论语》时提及 ‘夷狄亦有君道’,被以 ‘讪谤朝廷’ 定罪,本人处斩,学生家长流放,刻工杖毙(《清代文字狱档》第 6 册);
- 教材篡改:民间私塾被迫删改启蒙书,如《三字经》中 ‘周武王,始诛纣’(含 ‘革命’ 意)被改为 ‘周武王,始定周’,《百家姓》仅留 ‘赵钱孙李’ 等姓氏,历史典故全被删除(《清代民间教育史》)。
- 出版管控:明朝万历年间苏州民间书坊超 200 家,可自由刊印《西游记》等小说;清朝乾隆朝全国民间书坊仅存 30 家,且只能刊印 ‘四书节本’,底层知识获取渠道被系统性掐断。
叁
经济账:从 ‘识字变现’ 到 ‘知识无用’
明朝的市井文化
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催生刚性识字需求:
- 职业溢价:苏州织工中,识字者可任账房,月薪达普通织工 3 倍;
- 外贸刚需:浙江海商需掌握 ‘洋文契券‘(中文夹葡萄牙文),如隆庆年间《海语》记载,宁波商人 ‘非通夷语、识夷字者不得预其事‘(《明代商品经济与识字率》)。
清朝中期后,识字的经济价值被制度性摧毁:
- 抑商政策:康熙规定 ‘商人不得科举、衣绸缎‘,雍正朝查封山西晋商 ‘商学‘,称 ‘重利轻义,坏我风化‘;
- 仕途阻塞:清朝科举录取率较明朝降低 50%,且 67% 名额被士绅家族垄断。据《中国人口史・清代卷》统计,乾隆朝江南佃农中能书姓名者不足 10%,而明朝嘉靖年间该比例为 30%。
- 认知转变:明朝百姓视 ‘识字‘ 为 ‘升阶之梯‘,清朝中期后底层形成 ‘识字无用‘ 共识 —— 学记账会被疑 ‘通匪’,学文墨可能惹文字狱,不如专心种地。
肆
文化毒:从 ‘生存手册’ 到 ‘服从指南’
乾隆给英国国王写信
明朝启蒙教育兼具实用性与批判性:
- 《急就章》除识字外,收录 ‘耒耜犁锄‘ 等农具名、’斗斛权衡‘ 等计量知识;
- 《事林广记・卷十二》专设 ‘词讼须知’,详细记载 ‘告官吏贪赃‘ 的状纸格式,附《大明律》’民告官’ 条款摘要,甚至提示 ‘若官吏阻挠,可击登闻鼓‘。
清朝则将启蒙异化为 ‘忠君训练‘:
- 教材篡改:乾隆朝修订《弟子规》,删除明朝版 ‘泛爱众,而亲仁‘,新增 ‘君命召,行勿疾‘ 等条款;
- 思想灌输:嘉庆朝《乡塾规程》规定,私塾必须讲授《大清律例》中 ‘谋反者凌迟’ 等条款,未设此课目者吊销办学资格(《清代文化政策研究》)。
- 本质差异:明朝识字者可凭知识维权,清朝识字者最先学到的是 ‘莫管闲事’—— 如《增广贤文》在清朝被篡改,原句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被改为 ‘管好自家,莫管他家‘。
伍
识字率和改革
明治维新时的日本民众
从 15% 到 8% 的滑坡,本质是清朝中期后(乾隆至嘉庆)主动收缩基层教育、强化思想控制的结果:
- 教育权垄断:将社学从 ‘普惠教育’ 变为 ‘士绅私学’;
- 知识恐惧:用文字狱制造 ‘识字危险’ 的集体认知;
- 价值摧毁:通过抑商政策消解识字的经济动力。
或许有人问:识字率真的重要吗?看看明治维新前的日本 ——30% 的识字率(R.P. Dore《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普通百姓能读懂法令,工匠可对照英文说明书改良工具,这才有了“维新”的国家共识,有了 “殖产兴业” 时技术的快速吸收。
反观清朝:洋务运动时,江南制造局千余工匠中,能识洋文图纸者不足五十人(1876 年《申报》),英国技师讲蒸汽机原理,得先用方言翻译、柳枝画图;1840 年英军入侵,官员误译 “和平谈判” 为 “战书”,士兵竟用黑狗血 “破洋枪妖术”。
8% 的识字率,锁住的不只是底层读书路,更是社会自我更新的能力。日本能快速消化西方技术制度,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大清的改革者却还在为 “让官员看懂章程、百姓理解新政” 发愁。
历史最终证明:当一个王朝让半数潜在学习者失去识字机会,它输掉的不只是一场战争,更是整个未来。(史料来源: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清代文字狱档》、R.P. Dore《Education in Tokugawa Ja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