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umatic brain injury: Symptoms to systems in the 21st century
锈刀十一 樱桃树下
重点
·没有药物治疗能降低中重度脑外伤后的死亡率。
·缺乏有效的药物可能是我们研究创伤性脑损伤的方式的结果。
·一种更综合的基于系统的方法可能会增加动物对人类的转化,并导致突破性的治疗。
·需要一场革命来更好地了解整个身体对脑外伤的反应,并确定其进展的标志。
·迫切需要新的系统作用药物来治疗中重度脑外伤。
摘要
重度创伤性脑损伤(TBI)是一种毁灭性损伤,死亡率约为25%–30%。尽管经过数十年的高质量研究,仍未有药物疗法能降低其死亡率。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缺乏有效药物疗法的两个关键因素包括:转化研究中使用无特定病原体(SPF)动物,以及药物设计中存在缺陷的单节点靶向策略。要更好地理解机体对TBI的整体反应、识别其进展的新标志物、发现新的全身性作用药物,就必须进行变革。
本文综述了TBI的简要历史,探讨了其全身性病理生理学机制,并提出了21世纪的新研究策略。TBI的进展始于原发损伤部位释放的损伤信号,这些信号可引发局部缺血、出血、兴奋性毒性、细胞去极化、免疫功能障碍、交感神经亢进、血脑屏障破坏、凝血功能障碍及全身性功能紊乱。免疫细胞的代谢重编程会驱动神经炎症和继发性损伤过程。我们提出,若能早期纠正交感神经亢进和免疫细胞激活,或可恢复心血管功能及内皮–糖萼–线粒体偶联,最大限度减少继发性损伤,改善患者预后。治疗目标是通过恢复内环境稳态和维持充足的组织氧供,将损伤表型转变为愈合表型。
我们团队已研发出一种含腺苷、利多卡因和镁(ALM)的小容量液体疗法用于治疗TBI,研究表明该疗法可减轻中枢神经系统应激反应、支持心血管功能并减少继发性损伤。未来研究将进一步探索其向人类临床转化的适用性。
1.引言
创伤性脑损伤(TBI)一直是损伤后死亡的首要原因,在治疗方面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Fitzgerald 及其同事,2022 年,第 217 页)。
创伤性脑损伤(TBI)是全球医疗健康的重点关注问题,每年影响约 6900 万人,即每小时约 8000 人(Dewan 等,2018;Wiles,2022;Izzy 等,2023)。它是成人和儿童死亡及残疾的主要原因(Araki 等,2017;Maas 等,2022),其主要致伤原因包括机动车事故(50%)、跌倒(21%)、袭击与暴力(12%)以及运动与娱乐活动(10%)(Maas 等,2022)。总体而言,成年男性因 TBI 住院的概率几乎是女性的两倍,死亡概率则是女性的三倍(Peterson 等,2022)。然而,在中重度 TBI 病例中,女性的院内死亡风险显著高于男性,其原因尚不明确(Mollayeva 等,2018;Breeding等,2024)。居住地也会产生影响,农村和偏远地区居民的TBI 死亡率高于城市居民(Peterson 等,2022;de Souza 等,2024)。在接触性运动中,TBI 引发的担忧日益加剧,尤其对于年轻人而言,可能导致长期不良后果(Izzy 等,2023)。在中重度 TBI 病例中,约30% 至 50% 的患者会同时伴有胸部、腹部或四肢的多发伤,这进一步增加了治疗和康复的难度(Watanabe 等,2018;Faden等,2021)。
创伤性脑损伤(TBI)依据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该量表涵盖睁眼反应、言语反应和运动功能(Maas 等,2022;Saatman 等,2008;Pugh 等,2021)。GCS 评分 13 – 15 分表示轻度损伤,9 – 12 分为中度损伤,3 – 8 分为重度 TBI(Maas 等,2022)。尽管该评分系统仍是评估意识状态的实用方法,但存在一定局限性(de Souza 等,2024),这凸显出将影像学结果和生物标志物纳入严重程度分类以改善个性化治疗的需求日益迫切(Vande Vyvere 等,2024)。轻度 TBI 或脑震荡是最常见的损伤类型(Dewan 等,2018),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冲突中,约 90% 的军事人员 TBI 事件为轻度 TBI(Madhok等,2022;Dengler 等,2022;de Souza 等,2023)。轻度 TBI 不应被视为无关紧要的损伤,一些研究表明,高达 50% 的住院患者可能需要 6 个月才能从症状中恢复(Maas 等,2022)。相比之下,中重度 TBI 的死亡率高达 25% – 30%,且幸存者中能完全恢复独立生活和正常工作能力的不足 50%(Fitzgerald 等,2022;Maas等,2022)。幸存者的住院时间更长,患神经退行性疾病、慢性心理问题的风险更高,预期寿命也会缩短(Maas 等,2022;Wilson 等,2017;Krishnamoorthy 和 Vavilala,2022;Coburn等,2023)。2022 年,《柳叶刀》委员会提出,由于中重度 TBI 的长期影响,应将其视为一种慢性疾病(Maas 等,2022)。
尽管经过数十年的高质量研究,仍未有针对 TBI 的疗法被证实能显著降低死亡率和发病率。这是为什么呢?在本综述中,我们将简述TBI 的历史,从系统角度探讨其病理生理学,并解答为何突破性进展如此之少以及 21 世纪可能的解决方案。我们认为,要更好地理解人体对 TBI 的反应、识别其进展的新标志物、发现新的全身性作用药物,就必须进行一场变革。
2.过去:创伤性脑损伤的简史
在日本、伊比利亚半岛、德国、乌克兰、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法国、叙利亚、智利、墨西哥、秘鲁和玻利维亚,都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的钻孔颅骨,其中一些已有长达 10000 年的历史(Collado – Vázquez 和 Carrillo,2014,第 433页)。
自古以来,人类就一直在尝试治疗头部的严重撞击伤或穿透伤(图 1)。局部争斗、战役和战争促使人们不断提升相关知识以及治疗损伤的外科技术与技能。一些最古老的治疗实践可追溯至公元前 8000 年甚至更早,其中包括已愈合的颅骨钻孔,推测是通过刮擦、开槽、切割或钻孔等方式进行的(Collado – Vázquez 和 Carrillo,2014;Lillie,1998;Kshettry 等,2007)(图 1)。颅骨钻孔术(环钻术、钻孔术)是指移除一部分颅骨,以释放撞击后脑部的压力。这种操作很可能是为了清除损伤后的骨碎片,或者是出于仪式性钻孔以释放“邪灵”的目的(Collado – Vázquez 和 Carrillo,2014;Kshettry 等,2007)。古埃及和古希腊对不同的外科方法有详细描述(Collado – Vázquez 和 Carrillo,2014;Kshettry 等,2007;Kamp 等,2012)(图 1)。例如,希波克拉底认为,停滞的血液就像停滞的水一样会腐烂并形成脓液,而通过颅骨钻孔可以让血液在变质前流出(Kshettry 等,2007)。盖伦延续了这一传统,并提出头部受伤后让血液渗出可以减轻“坏体液”的影响(图 1)。
图1. 从史前时期到现在,推动头部创伤治疗取得进展的重大事件简史。治疗方法从咒语、迷信和混合物,到更客观的释放颅内压的外科手术。早期的环钻术可追溯到数千年前,当时使用石器进行操作。这条时间线展示了不断变化的理念、实践和成果,当前的思想和治疗方法正是从中发展而来。一方面,我们在知识进步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另一方面,改善当前治疗方法的道路显然还很漫长。相关参考文献见正文。A.D.:公元;BBB:血脑屏障;B.C.:公元前;CNS:中枢神经系统;GCS:格拉斯哥昏迷量表;ICP:颅内压;TBI:创伤性脑损伤。
文艺复兴时期(约公元1400-1600年),人们的观念发生了显著转变,从古希腊和中世纪的超自然方法转向更多基于医学和科学的实证观察(Dobson,2016)。时间快进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生物学、生理学、医学和外科学的重大进展使得无菌操作、改良的麻醉方法以及后来的抗生素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图1)。在此之前,根据Gurdjian对美国内战(1861-1865年)期间脑部穿透伤统计数据的整理,约70%的死亡率并不罕见(Head,1973)。到了20世纪,随着新的外科技术和围手术期护理的出现,死亡率较19世纪末下降了约50%(Stein等,2010)。乔治·克里尔(1864-1943)和哈维·库欣(1869-1939)是两位最具影响力的外科医生,他们共同开创了神经外科的现代时代(图1)。下一个重大进展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患者康复成为医疗保健的重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型专业康复医疗中心兴起,患者预后得到改善。
20世纪50年代,神经生物学和病理生理学的重大进展催生了新的创伤性脑损伤(TBI)诊断方法和治疗手段(Casper,2018)。20世纪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中数十万人遭受TBI,该领域迎来了又一个快速发展阶段(Lindquist等,2017;Cernak等,2017;Agimi等,2019)。同时,与速度相关的交通事故和接触性运动导致的TBI发病率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使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I)等新技术的研发,为新的医学诊断、治疗和手术提供了指导(Pinky等,2022)(图1)。分子生物学的进步为TBI治疗奠定了后续发展的基础,而“组学时代”至今仍在不断发展。自21世纪以来,研究重点进一步扩大,从关注不同严重程度的单次TBI,扩展到具有终身影响的反复头部撞击(Pinky等,2022;McKee等,2023)。这一点在参与接触性运动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以及家庭/家庭暴力受害者中日益引发关注,且反复头部撞击与晚年慢性创伤性脑病、阿尔茨海默病和帕金森病有关联(McKee等,2023;Gr等,2017;Snyder等,2018)(图1)。尽管经过数十年的技术进步和研究,仍未有TBI疗法被证实能显著改善轻至重度TBI患者的预后。
3.现状:从系统角度看创伤性脑损伤的病理生理学
原发性损伤机制是指创伤发生时,神经元、轴突、神经胶质和血管因剪切、撕裂或牵拉而受到的机械损伤。这些作用共同诱发了继发性损伤机制(Kumar和Loane,2012,第1191页)。
头部受到严重撞击、震荡或穿透性损伤,会导致神经元、轴突、脑血管和代谢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并伴有自主调节功能障碍(Ng和Lee,2019)。原发性创伤性损伤可能是离散的“局灶性”病变,如撕裂伤或挫伤,并伴有局部出血;也可能是更弥漫性的轴突损伤,影响大脑更大范围的区域,包括白质连接束(Pinky等,2022;Snyder等,2018;Signoretti等,2010;Demirtas-Tatlidede等,2012)。这种损伤可能涉及白质降解、神经元丢失、神经递质系统改变、蛋白质错误折叠以及持续性神经炎症(图2)。约56%的重度TBI患者会出现扩散性去极化波(Seidel等,2016;Balanca等,2017)。继发性损伤的进展如同池塘中从原发损伤处扩散开来的涟漪,先局限于局部,然后波及全身,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CNS)交感神经流出、免疫功能、炎症、内皮–糖萼功能、凝血功能障碍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的异常改变(McKee和Lukens,2016;Lazaridis等,2019;Dobson等,2021;Krishnamoorthy等,2021)(图2)。低血压、肺炎、感染和脓毒症是进一步的并发症,且与高死亡率相关(Corral等,2012)。与所有重大创伤性损伤(钝挫伤、穿透伤、出血性损伤和烧伤)一样,TBI的病理生理学变化与应激相关的儿茶酚胺有关,其水平与损伤严重程度成比例,可能在数天后才逐渐下降(Rizoli等,2017;Dobson等,2022;Dobson等,2024)。尽管我们的研究重点是成人中重度TBI,但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可能因年龄相关的结构变化而有不同的反应(Araki等,2017)。这些年龄差异的研究尚不充分,是未来研究的关键课题。
图2. 头部遭受严重撞击、震荡或穿透性损伤后,损伤波会像池塘中的涟漪一样扩散至大脑主要区域,先局限于局部,随后通过免疫、炎症和神经激素机制波及全身。原发性损伤通常涉及神经元、轴突、神经胶质和血管的剪切、撕裂或牵拉。继发性损伤是指始于原发性损伤的进行性过程,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免疫功能障碍、过度炎症、凝血功能障碍、氧化应激和线粒体能量不足。其进展过程涉及大脑与多个器官回路(或轴)的部分解偶联,在严重情况下,可能引发广泛的组织低灌注、感染、免疫抑制和多器官功能障碍。CTE:慢性创伤性脑病;DAMPs:损伤相关分子模式;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4.早期免疫激活与炎症
创伤性脑损伤患者的神经重症监护在初始处理中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在“黄金一小时”内(Maurya及其同事,2022年,第45页)。
头部严重损伤后,获得确定性治疗的时间至关重要,因为继发性损伤可能导致进一步的细胞损伤。数分钟内,受损或濒死的神经元会释放大量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Dobson等,2021),进而激活驻留免疫细胞,引发难以消退的细胞因子风暴。细胞因子风暴包含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免疫调节剂、神经肽、神经传入纤维、补体、氧化剂、蛋白酶和毒性胞外陷阱(Fajgenbaum,2020)(图3)。血脑屏障(BBB)的损伤会进一步加剧细胞因子风暴,尤其是在存在多发伤和出血的情况下(图4)。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包括脑源性血管外囊泡、微粒、纤维蛋白原、膜联蛋白、血小板成分、纤连蛋白、S100蛋白、 Syndecan-1、F-肌动蛋白、5-三磷酸腺苷(ATP)、组蛋白、脱氧核糖核酸(DNA)、线粒体因子、高迁移率族蛋白1(HMGB1)、硫酸乙酰肝素、肌腱蛋白C、防御素、β淀粉样蛋白等多种物质(Kumar等,2017;Roh和Sohn,2018)。
图3. 中重度创伤性脑损伤(TBI)后,继发性损伤的程度取决于受损和/或濒死细胞释放的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这些损伤信号可被脑内和外周血中的多种固有免疫细胞识别,若不加以控制,将引发细胞因子风暴,进而导致中枢神经系统驱动的继发性损伤、全身功能障碍及不良预后。ALI:急性肺损伤;AKI:急性肾损伤;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ILC:固有淋巴细胞;MODS: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NK:自然杀伤细胞;NLR:Nod样受体;PRR:模式识别受体;RAGE: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LR:视黄酸诱导基因I样受体;
图4. 示意图显示中重度创伤性脑损伤(TBI)后,随着血脑屏障(BBB)的破坏,颅内环境发生的变化。血脑屏障是脑实质与血流之间的一道屏障。受损的血脑屏障会允许血源性免疫细胞、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及其他免疫调节因子进入,从而加剧周细胞、小胶质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的激活状态。这些变化会进一步导致脑及全身的免疫功能障碍、炎症、凝血功能障碍、氧化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CNS:中枢神经系统;DAMP:损伤相关分子模式。
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会被宿主的固有防御系统识别,该系统包括免疫细胞上表达的模式识别受体(PRRs),如 Toll 样受体(TLRs)(Kawai和 Akira,2005;Akira 等,2006;Vijay,2018;Takeuchi 和Akira,2020)(图3)。损伤信号和受体均为高度保守的基序,经进化选择后,有助于宿主在血脑屏障等屏障受损(如创伤性脑损伤)后提高存活率(Dobson 等,2021;Janeway和 Medzhitov,2002;Matzinger,2012)。这些受体表达于驻留小胶质细胞、NG2 胶质细胞、星形胶质细胞、树突状细胞、神经元、内皮细胞,以及从外周募集的浸润性免疫细胞和血小板上(图3)。血源性中性粒细胞最先穿过血脑屏障,随后是骨髓来源的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Dobson等,2021;Shrivastava 和 Shukla,2019;Kanashiro等,2020)。其他免疫细胞也会被募集,如树突状细胞、自然杀伤(NK)细胞、B 细胞、T 细胞和固有淋巴细胞(ILC)(McKee 和 Lukens,2016;Bouras 等,2022)(图3)。随着继发性损伤的进展,血脑屏障通透性增加、免疫功能障碍及炎症加剧,引发病理性“失控”级联反应,导致不良结局(Chen 等,2017)(图4)。
尽管早期炎症反应复杂(Xiao 等,2011),但向促炎状态的转变可能是潜在的可通过药物疗法干预的关键靶点。新证据表明,损伤后免疫细胞的快速激活、分化和存活似乎与模式识别受体(PRRs)激活引发的免疫细胞线粒体 – 糖酵解转换有关(Dobson 等,2021;Kumar,2019;Wang 和 McLean,2022;Namgaladze 和Brune,2023)。若能调节免疫细胞的代谢,或许可通过增强抗炎过程来减轻炎症(Kanashiro 等,2020;Bouras等,2022;Xiao 等,2011;Manson 等,2016;Dobson 等,2022)。关键在于,恢复促炎与抗炎细胞因子的平衡,对于免疫系统产生有效应答而不引发附带损伤至关重要。另一个可恢复炎症平衡的潜在靶点是抑制免疫细胞中的多蛋白炎症小体复合物,该复合物在放大早期促炎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图4)。
5.中枢神经系统应激反应、交感神经激活与附带损伤
直接作用于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HPA)轴的实验性应激源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有助于更明确应激 – 免疫通路在介导创伤性脑损伤(TBI)结局中的作用(Tapp 及其同事,2019 年,第1页)。
创伤性脑损伤(TBI)引发的局部及全身炎症加剧,对中枢神经系统(CNS)调控全身稳态功能具有深远影响(图4和图5)。中枢神经系统会通过引发全身性应激反应来应对炎症。例如,促炎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6 已被证实可激活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和孤束核,进而促使交感神经释放儿茶酚胺(Dobson 等,2021;Dobson 等,2022;Tapp 等,2019;Silverman等,2005;Barman,2020)。早期转向交感神经主导的状态会维持促炎状态(Letson 等,2022;Coppalini 等,2024),Rizoli 及其同事发现这与不良结局相关(Rizoli 等,2017;Robba 等,2020;McDonald 等,2020;Yan 等,2024;Krishnamoorthy 等,2021)。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的激活还可能导致糖皮质激素(GC)过度增加(Tapp 等,2019)。由于小胶质细胞及许多其他免疫细胞富含糖皮质激素受体,应激诱导的免疫细胞致敏会进一步加剧神经炎症(Tapp 等,2019)。此外,糖皮质激素会使循环中的白细胞介素 -6 水平升高,这可能进一步放大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的激活和全身炎症(Tapp 等,2019)。值得注意的是,重度头部损伤后交感神经释放的儿茶酚胺还会显著改变全身多个器官的功能和能量代谢(图5)(后文将详细讨论)。
图5. 中重度创伤性脑损伤(TBI)对身体各器官系统影响的示意图。几乎所有严重疾病的共同特征是大量儿茶酚胺释放和免疫介导的炎症反应,这些会引发全身性并发症。若能减轻交感神经兴奋和炎症反应,并降低血脑屏障(BBB)的通透性,或许可最大限度减少脑–器官回路(或轴)的解偶联,从而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目前需要新的药物疗法来阻断这些由中枢神经系统(CNS)驱动的损伤循环的持续发展。AKI:急性肾损伤;ALI:急性肺损伤;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CTE:慢性创伤性脑病;HPA:下丘脑–垂体轴;NTS:孤束核;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TBI:创伤性脑损伤。
创伤性脑损伤(TBI)研究中一个鲜少受到关注的领域是,性别和年龄对患者损伤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PA)轴及孤束核(NTS)反应性的影响。在健康人群中,女性对生理性应激源的HPA轴反应似乎比男性更强(Babb等,2013),但目前尚不清楚当应激源为TBI时,这种差异是否依然存在。不过,有研究显示,在轻度TBI中,雌性小鼠的HPA轴反应可能比雄性小鼠更强烈,但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Russell等,2018)。年轻的TBI患者与老年患者的儿茶酚胺反应性似乎也存在差异(Krishnamoorthy和Vavilala,2022)。随着更多高质量研究的开展,HPA轴和NTS的反应或许会成为新的治疗干预靶点,以减轻中重度TBI对全身的影响。
6.创伤性脑损伤诱发的内皮病变
糖萼的破坏使内皮细胞暴露于循环中的细胞因子、免疫细胞和其他因子,这些因子会触发多种反应,可能导致内皮病变(Gonzalez Rodriguez及其同事,2018年,第7页)。
TBI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了解内皮激活和糖萼脱落如何加剧继发性损伤的进展(Xu等,2020)。内皮–糖萼是血液和组织之间的连接点,其覆盖的表面积超过55,000平方米(Dobson等,2022),当它被激活时,就会引发所谓的内皮病变(Neubauer和Zieger,2022;Zou等,2021;Lu等,2022)。TBI诱发的内皮病变是一个过程而非终点,它与免疫细胞的激活和浸润、炎症、凝血功能障碍以及血管反应性异常相关(Neubauer和Zieger,2022;Zou等,2021;Lu等,2022)。应激激活的膜结合脱落酶会促进糖萼脱落,这些脱落酶会对多种因子做出反应,如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介素1-β、活性氧(超氧化物和羟基自由基),以及/或者大量液体复苏(参见液体管理部分)(Dobson等,2022;Zou等,2021;Anand等,2023)。TBI严重程度与内皮病变之间存在一种潜在关联,即内皮生物标志物(如 syndecan-1、透明质酸(HA)、血栓调节蛋白和细胞黏附分子)会释放到循环中(Gonzalez Rodriguez等,2018;Di Battista等,2016)。具有临床意义的是,糖萼脱落后似乎能相对快速地自我修复(Zeng和Tarbell,2014)。Luft指出:“这些细胞通常能在几分钟内重新形成缺失的‘外衣’”(Luft,1976)。然而,关于中重度TBI后糖萼的丢失与恢复情况,目前所知甚少(Zou等,2021)。
在重度TBI病例中,早期脑内皮病变可能与局部创伤后血管内微血栓形成相关,进而导致缺血、缺氧和神经元死亡(Albert-Weissenberger等,2019)。血小板激活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多聚体的过量产生会以细长链的形式黏附于内皮细胞,形成血小板-VWF“微血栓”(Xu等,2020;Ince等,2016;Chang,2019)。如果这种病理过程扩散并累及全身,可能会引发一种罕见的致命性疾病——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参见凝血功能障碍部分)。减轻内皮糖萼的早期激活或促进其脱落后的快速修复,可能成为新疗法的潜在靶点。
7.心功能障碍:急性和慢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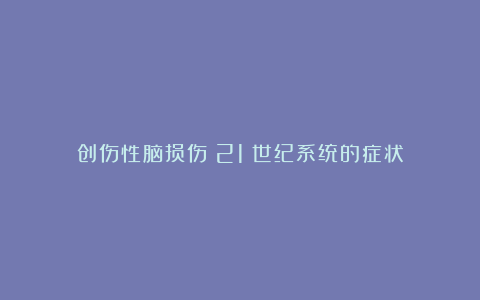
急性脑损伤会触发全身性炎症反应和儿茶酚胺激增,导致神经递质和细胞因子释放。这些物质会对大脑和外周器官产生有害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加剧脑损伤和细胞功能障碍(Coppalini及其同事,2024年,第1页)。
急性神经源性心肌损伤:中重度TBI对心血管不稳定性的影响尚未被充分了解(Chen等,2017;Coppalini等,2024;McDonald等,2020;Venkata和Kasal,2018)。早在1947年,Byer及其同事就报道过头部损伤会导致心肌损伤和心律失常(Byer等,1947)。如今,25%–35%的重度TBI患者会出现心血管并发症(Krishnamoorthy等,2021;Coppalini等,2024;Cuisinier等,2016;Mathias等,2000)。有研究提出,中枢神经系统交感神经兴奋、儿茶酚胺增加以及神经源性脑–心轴的改变,可能导致心室功能障碍、局部室壁运动异常、肌钙蛋白升高、心肌顿抑和Takotsubo心肌病(Coppalini等,2024;Gregory和Smith,2012)。心功能障碍和心律失常的严重程度与神经损伤的严重程度相关(McDonald等,2020;Salim等,2008;Cai等,2016)。大鼠研究支持中重度TBI后心功能障碍具有神经源性基础(Letson和Dobson,2018)。在小鼠中,研究表明心功能障碍还涉及脾脏的炎症细胞浸润,因为切除脾脏后,损伤程度有所减轻(Zhao等,2019)。有趣的是,TBI的病理生理学特征似乎与失血性休克、烧伤或脓毒症后的心肌顿抑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表明它们可能存在相似且统一的潜在病因(Dobson等,2022;Dobson等,2024)。需要进一步开展基础研究来阐明这些机制及其差异。
慢性影响:心血管疾病和中风:除了重度TBI后的长期不良神经结局外,这种损伤似乎还会使患者易患多种慢性疾病。最近一项针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退伍军人的队列研究显示,与未受损伤的退伍军人相比,遭受过TBI的退伍军人在晚年更易患冠心病、中风和外周动脉疾病(Stewart等,2022)。在普通人群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关联,即使是轻度TBI,也会增加10年内患冠心病、高脂血症、高血压和肥胖的风险(Izzy等,2023),以及晚年缺血性中风的风险(Radmanesh等,2024)。这些发现表明,轻至重度TBI的病程分为两个阶段:1)急性期;2)慢性期。这为《柳叶刀》委员会提出的“应将TBI视为一种慢性疾病”的观点提供了支持(Maas等,2022)。这种双阶段病程为研发新药物提供了可能,即治疗急性期的药物或许能产生连锁效应,减少晚年并发症。
8.凝血功能障碍、出血和纤溶异常
对创伤性脑损伤(TBI)及TBI相关凝血功能障碍采用黏弹性试验指导治疗的益处分析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必须承认,目前在知识层面仍存在重大空白(Bradbury及其同事,2021年)。
凝血功能障碍是一种系统性缺陷,指凝血谱异常且伴有纤溶异常(Dobson等,2020)。正常止血功能是促凝血、抗凝和纤溶通路之间的精细平衡,而这又依赖于健康的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内皮–糖萼、循环血小板和健全的免疫系统(Dobson等,2020;Dobson等,2015)。30%–50%的中重度TBI患者会出现凝血功能障碍,且这类患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更高(Epstein等,2014;Juratli等,2014;Nakae等,2022),其中近50%的病例会出现出血进展(Juratli等,2014;Nakae等,2022;Maegele等,2017;Zhao等,2023)。对于存在全身性出血且已证实有纤溶亢进的TBI患者,若在损伤后3至6小时内使用抗纤溶药物氨甲环酸(TXA),已被证实可降低死亡率(Collaborators,2019)。然而,若无法证实存在纤溶亢进,人们越来越担心使用TXA可能会造成伤害(Sigmon等,2023;Letson和Dobson,2017;Myers等,2019)。另一方面,对于伴有颅内出血的TBI患者,TXA似乎对TBI病理进程几乎没有影响(Jakowenko等,2022),尽管有部分研究报道其具有一定益处(Xiong等,2023)。鉴于在TBI患者中使用TXA仍存在争议,准确评估出血状态、凝血功能障碍和纤溶状态以指导最佳治疗,就显得至关重要(Shammassian等,2022)。
对TBI诱发的凝血功能障碍的综述显示,其凝血功能障碍谱系涉及纤溶异常、D-二聚体生成以及血小板功能障碍(Nakae等,2022;Samuels等,2019;Meizoso等,2022;Kockelmann和Maegele,2023;Chen等,2023)。这种广泛变异性可能与以下因素相关:1)头部创伤的类型和严重程度;2)检测方法和检测时机;3)颅内出血的程度;4)是否存在多发伤;5)患者年龄、性别和健康状况的差异(Bradbury等,2021)。总体而言,重度TBI患者的表型似乎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低凝状态(伴有脑出血时更为严重),且纤溶作用微弱(图6)(Letson和Dobson,2018;Shammassian等,2022;Samuels等,2019;Van Beek等,2007;Schöchl等,2011;Kunio等,2012)。TBI患者的纤溶作用微弱这一发现令人费解,尽管其死亡率与失血性休克患者相近,但两者的反应却截然不同(Dobson等,2020;Dobson等,2015;Cardenas等,2019)。这种差异可能与内皮激活的时机和程度以及组织低灌注有关,在失血性休克中,这些因素似乎更为剧烈且广泛,从而导致纤溶亢进(Dobson等,2020)。
图6. 凝血功能障碍是一种系统性病理状态,表现为血液凝固能力异常,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纤溶异常。该示意图展示了重度创伤性脑损伤(TBI)后,不同出血表型伴随纤溶异常的可能机制。若存在颅内或颅外出血,低凝状态和纤溶倾向会进一步加重,表现为纤维蛋白原水平降低、D-二聚体升高,且死亡率更高。凝血和纤溶过程由位于内皮细胞上的血栓调节蛋白(TM)–凝血酶“开关”调控。①凝血方向(高凝或低凝)取决于凝血酶-TM复合物上不同表皮生长因子(EGF)样结构域上的各种激活剂和抑制剂(Dobson等,2020)。重度TBI后,EGF样结构域4-6上的蛋白C激活会导致低凝表型②;而EGF样结构域3-6上的凝血酶激活纤溶抑制物(TAFI)减少会引发纤溶异常④,进而导致纤溶酶水平升高、纤维蛋白原减少以及血小板聚集能力下降,形成的血凝块稳定性较差。③在罕见情况下,重度TBI后可能出现致命性出血表型,此时纤溶亢进与微血管纤维蛋白沉积相关,这种情况被称为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③。目前迫切需要能够调节凝血酶-TM“开关”的药物。EPCR:内皮细胞蛋白C受体;FDP:纤维蛋白降解产物;FVIII:凝血因子VIII;PAI-1: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S100A10:S100钙结合蛋白A10;TBI:创伤性脑损伤;TPA: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物;VWF:血管性血友病因子。
关于TBI相关凝血功能障碍的早期研究包括“国际预后与临床试验分析项目(IMPACT)”,该研究报道,26%的患者入院时凝血酶原时间(PT)延长,且死亡风险增加64%(Van Beek等,2007)。2009年,Talving及其同事开展的一项前瞻性研究发现,32%的重度闭合性TBI患者和54%的重度穿透性TBI患者存在凝血功能障碍(Talving等,2009)。存在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ICU住院时间更长,死亡风险约为无凝血功能障碍患者的10倍(Talving等,2009)。一年后,Wafaisade及其同事采用血浆检测法对单纯TBI患者进行了大规模回顾性分析,再次证实约25%的患者入院时存在凝血功能障碍,且这是预后不良的独立预测因素(Wafaisade等,2010)。2012年,Schreiber团队发现,在69例伴有颅内出血的TBI患者中,9%的患者入院时血栓弹力图(TEG)提示低凝状态,且这与更严重的TBI损伤相关(Kunio等,2012)。他们还发现,纤维蛋白原水平降低和部分凝血活酶时间(PTT)延长与死亡率增加相关(Kunio等,2012)。Schöchl团队对88例重度TBI患者开展了首批旋转血栓弹力测定(ROTEM)研究之一,该研究同样发现低凝状态与更高的死亡率(推测与出血相关)相关,仅有少数患者表现出纤溶亢进(Schöchl等,2011)。最近一项关于TEG和ROTEM的系统综述表明,TBI相关低凝状态与神经外科手术风险增加、住院和ICU停留时间延长以及高死亡风险相关(Shammassian等,2022)。
Samuels及其同事近期开展的另一项高质量TEG研究显示,30岁男性单纯闭合性TBI患者入院时存在低凝倾向,且伴有一定程度的纤溶(Samuels等,2019)。纤溶状态通过最大凝块强度出现后30分钟的凝块溶解率(LY30=1.2%)与正常人群值对比来判断(Samuels等,2019)。有趣的是,该研究发现,尽管死亡率达35%,但患者的凝块强度和α角均正常。在第二组重度闭合性TBI合并多发伤的患者中,出血倾向略高(10%),且死亡率显著更高(56%),尽管纤维蛋白原水平几乎无变化(Samuels等,2019)。显然,这两组患者的表型均不属于纤溶亢进。此外,该研究也不支持TBI相关的大量脑源性组织因子、细胞外囊泡或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释放会导致高凝状态(Meizoso等,2022;Kockelmann和Maegele,2023)。大多数动物模型均支持低凝状态且纤溶作用微弱这一结论(图6)。在中度TBI大鼠模型中,Letson和Dobson发现,与基线相比,1小时和4小时后出现明显的低凝状态(PT和aPTT延长),且这一结果通过ROTEM得到证实(Letson和Dobson,2018)。同样,尽管纤维蛋白原水平降低50%,但未发现纤溶亢进的证据(Letson和Dobson,2018)。TBI模型动物的血小板聚集能力显著下降,但血小板数量未发生变化。损伤严重程度对早期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功能异常和纤溶的影响仍需进一步研究(Davis等,2013)。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重度头部损伤后的DIC表型。DIC是一种极端且罕见的表型,其特征是中小型血管内出现弥漫性纤维蛋白沉积(图4)(Dobson等,2015;Hayakawa,2017;Thachil,2019)。文献中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将低凝状态、纤溶(出血表型)与DIC等同起来(Toh等,2007;Levi和Scully,2018;Unar等,2023;Buaboonnam等,2023)。临床上,DIC的诊断主要基于包含PT、血小板计数、纤维蛋白原和D-二聚体水平的评分系统。我们认为,DIC这一概念应仅限于已证实存在微血管纤维蛋白沉积的特定表型。继续基于评分系统诊断DIC会掩盖导致高死亡率的真实表型。在其他严重创伤状态下,DIC也较为罕见。在烧伤患者中,Barret和Gomez对3331例烧伤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尸检中未发现因DIC导致的死亡(Barret和Gomez,2005)。在败血症和低血压患者中,McManus及其同事报道,275例患者中仅有5例(1.8%)出现“体外凝血功能超常”,根据小血管纤维蛋白血栓活检结果,这些患者可能患有DIC综合征(McManus等,1973)。目前尚未在TBI患者中开展类似研究。关键在于,若不存在血管内纤维蛋白沉积,临床上诊断的凝血功能障碍可能并非DIC,这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最佳治疗,并阻碍纠正其进展的新药研发。
9.多器官功能障碍:中枢神经系统–器官回路的解偶联
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创伤性脑损伤(TBI)后会出现颅外器官功能障碍。……不幸的是,尽管这些研究可能存在共同的潜在机制,但大多数先前的研究都集中在单一器官功能障碍的后果上,而非多器官功能障碍(Krishnamoorthy及其同事,2021)。
据报道,高达68%的重度TBI患者会早期出现多器官功能障碍(Faden等,2021;Yan等,2024;Krishnamoorthy等,2021)。继发性损伤似乎由神经源性脑–器官解偶联、心肺功能障碍和持续性组织低灌注驱动。如前所述,若TBI合并出血或多发伤,早期预后会更差(Watanabe等,2018;Robba等,2020;McDonald等,2020)。受影响的器官包括肺、心脏、血管、肠道、肾脏、肝脏、脾脏、脂肪组织和肌肉(图5)(Robba等,2020;Krishnamoorthy等,2021)。最近,转化研究与临床知识(TRACK)-TBI研究团队开展的一项大型回顾性研究显示,TBI相关的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MODS)可持续一年以上,且这些不良结局似乎与大脑本身以及初始多发伤均有关联(McDonald等,2020;Krishnamoorthy等,2021;De Vlieger和Meyfroidt,2023)。这些持续性中枢神经系统变化可能与各年龄段人群晚年出现的慢性疾病相关(Izzy等,2023),但还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重度头部损伤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是呼吸功能障碍,这会导致ICU住院时间延长、神经结局恶化以及死亡率升高(Robba等,2020;Krishnamoorthy等,2021;Astarabadi等,2020)(图5)。中枢神经系统交感神经输出以及脑干反射改变被认为是导致肺部并发症、炎症和水肿的主要原因(Koutsoukou等,2016)。此外,据报道,高达50%的机械通气TBI患者会发展为急性肺损伤(ALI),55%的患者会发生感染(Koutsoukou等,2016)。另外,高达20%的患者会出现急性肾损伤(AKI)(De Vlieger和Meyfroidt,2023)。大量液体复苏、血管升压药使用和渗透性治疗药物会进一步加重ALI和AKI(Astarabadi等,2020;De Rosa等,2024)。TBI还会引发快速的肝脏反应,据信肝脏会通过释放急性期蛋白和炎症介质加剧继发性损伤(Villapol,2016)。同样,中枢神经系统儿茶酚胺释放会刺激脾脏巨噬细胞,使其向外周循环中大量分泌促炎细胞因子(如TNF-α和IL-1β)(Tracey,2020),这些细胞因子可通过受损的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经系统,增强免疫反应(Chen等,2017)(图5)。
中重度TBI后,儿茶酚胺激增还会通过减少肠系膜血流量对胃肠道功能产生显著影响(McDonald等,2020;Deitch,2012;Villalba等,2017)(图5)。这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因为若肠道发生缺血,其通透性会增加,肠道细菌、脂多糖、细胞因子、神经肽和蛋白质信使可进入循环系统,加重免疫和炎症负荷,加剧凝血功能障碍,并导致多器官功能障碍(Deitch,2012;Villalba等,2017;Hayakawa等,2011;Solari等,2021)。除肠道屏障破坏外,重度TBI还与下消化道动力丧失和胃黏膜损伤相关(McDonald等,2020;Taraskina等,2022)(图5)。患者还可能进入急性分解代谢状态,需要营养支持以维持骨骼肌质量、重要器官功能和脑代谢(Yan等,2024;Foley等,2008;Kurtz和Rocha,2020;Gribnau等,2024)。这种状态涉及广泛的线粒体功能障碍,线粒体解偶联可能会增加产热,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40%-70%的重度TBI患者出现发热相关(Yan等,2024)。受损神经元释放的内源性致热原会破坏下丘脑调定点,进一步加剧发热(Yan等,2024)。无论重度TBI后多器官功能障碍和发热的潜在原因是什么,这些损伤的综合作用是预后极差的独立预测因素。
10.液体管理:有益还是有害?
由于缺乏相关数据,液体的最佳使用方案基于临床场景和专家意见。目前,院前液体的选择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Dawson等,2022,第144页)。
在重度TBI患者中,静脉(IV)液体治疗对于减轻脑水肿、稳定脑灌注压(CPP)、维持血流自动调节功能、改善脑实质组织氧合、治疗脱水以及减缓继发性损伤进展至关重要(Maas等,2022;Yan等,2024;Wiegers等,2021;Carney等,2017;van der Jagt,2016;Gantner等,2014)(图7)。若TBI合并脑内或全身性出血,可能会危及生命(Maegele等,2017;East等,2018;Montgomery等,2022;Sontakke等,2023)。过去几十年中,越来越明显的是,液体过多或过少都会导致显著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图7)(Wiegers等,2021)。如今,大多数液体和输血管理方案都是基于共识的实践(Montgomery等,2022;Sontakke等,2023)。常用于减轻脑水肿和颅内压(ICP)的液体包括甘露醇(0.25-1克/千克)和高渗盐水(3%或7.5%)(East等,2018;Gharizadeh等,2022);而用于稳定血流动力学(若出现低血压)和维持 hydration状态的液体包括生理盐水(0.9%)、乳酸林格氏液或平衡晶体液(Dobson等,2024;Dawson等,2022;Gantner等,2014;Myburgh,2018)。若出现贫血,建议输注红细胞(RBC)或其他血液制品(East等,2018;Montgomery等,2022)。静脉液体使用中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高达50%的重症监护成年患者对液体无反应,即液体无法增加前负荷和每搏输出量以改善组织氧供(Marik和Lemson,2014;Hasanin,2015)。据我们所知,尚未开展关于中重度TBI后无反应者与有反应者的对比试验。
图7. 为重度创伤性脑损伤(TBI)患者选择最佳的静脉(IV)液体成分、容量和使用时机仍具挑战性。决策应基于对患者个体需求和心脏对液体反应性的临床评估。液体管理的主要目标是减轻脑肿胀,并在平均动脉压(MAP)约为90 mmHg时优化脑灌注压(CPP)。液体输注过少、过多或过早,都可能弊大于利。迫切需要开展高质量的临床试验,为静脉液体疗法的选择和使用提供指导(Sontakke等,2023)。ADP:二磷酸腺苷;AKI:急性肾损伤;ALI:急性肺损伤;ARDS: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TP:三磷酸腺苷;CNS:中枢神经系统。
尽管缺乏比较不同静脉液体类型、使用时机和成分的高质量临床试验(图7),但迫切需要设计新的液体和疗法来保护TBI患者的大脑和全身。大量液体输注可能导致广泛的组织水肿、高氯性代谢性酸中毒、内皮功能障碍、稀释性凝血功能障碍、肾功能障碍,并加剧炎症,延长ICU住院时间,提高死亡率(Dawson等,2022;Wiegers等,2021;Cheung-Flynn等,2019;Hayes,2019;Chatrath等,2015)(图7)。生理盐水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的,20年前开展的“生理盐水与白蛋白液体评估(SAFE)”试验支持继续使用生理盐水(Sontakke等,2023;Finfer等,2004)。然而,与它的名称相反,生理盐水既不“生理”,也并非无害(Myburgh,2018;Awad等,2008;Liu和Lu,2023)。为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引入了具有生理氯离子浓度和额外阴离子(乳酸盐、醋酸盐和葡萄糖酸盐)的平衡等渗溶液,以弥补碳酸氢盐的缺失并改善酸碱平衡(Gantner等,2014;Rasouli,2019)。在危重症患者中,这些平衡溶液通常比生理盐水更受青睐,且有报道称其可改善预后(Semler等,2018)。然而,“重症监护平衡溶液研究(BaSICS)”(2017–2020)比较了平衡溶液与生理盐水,发现重度TBI患者(亚组分析)中,接受平衡溶液的患者90天死亡率显著高于接受生理盐水的患者(31% vs 21%;P=0.02)(Shankar等,2022;Zampieri等,2021)。这项研究强调,需要进一步了解现有液体疗法在TBI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差异。
最后,一个多世纪前,美国医生乔治·埃文斯(George Evans)在1911年的著作中恰当地总结了生理盐水的潜在有害影响:“如果一个人观察到盐溶液的使用常常是鲁莽的,尤其是在术后时期,而事先不了解血压状况、心脏成功处理大量液体的能力,或肾脏排泄由此产生的大量氯化物的功能,那么他一定会对这种操作的危险性留下深刻印象”(Awad等,2008;Evans,1911)。基于现有证据,显然迫切需要新的基于系统的、目标导向的疗法和循证指南,以改善中重度TBI患者的预后。
11.为何药物突破如此稀少?
“当生理学把矮胖子(Humpty Dumpty)拆解后,或许很难(甚至不合时宜)再将其重新拼凑起来。因此,像生理学中那些传统的分析方法,在应用于涉及完整生物体功能的问题时,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误导。”
乔治·巴塞洛缪(1919–2006)(Bartholomew,1986,第327页)
尽管过去五年发表了超过28,000篇论文,开展了超过250项试验,经过了数十年的高质量研究,但仍没有有效的突破性药物来治疗重度头部损伤(Kochanek等,2020)。转化成功的缺乏可能有多种因素:
–临床前研究方法学严谨性不足,无法确保实验的可重复性和用于人类转化的高质量数据。
–临床前研究缺乏对性别、年龄和合并症的考虑(若可能)。
–人体试验设计不佳。
–动物模型无法复制人类病情。
–无特定病原体(SPF)动物的不当使用。
–临床前研究中存在缺陷的单节点靶向做法。
许多研究、研讨会、指南、评论、系统综述和社论都讨论了动物到人类转化成功的持续问题(Kochanek等,2020;Choudhry等,2007;Lowenstein和Castro,2009;Lee,2018;Seyhan,2019;Mauvais-Jarvis等,2020;Hart,2021;Ivan等,2023;Carmody等,2022;Fogel,2018;Lapchak等,2013;Ten,2022)。动物研究内部和之间的研究严谨性与可重复性不足、动物选择不当、品系差异以及实验设计欠佳,都可能导致关于药物安全性和治疗效果的结论出现错误(Kochanek等,2020;Choudhry等,2007;Lowenstein和Castro,2009;Lee,2018;Seyhan,2019;Mauvais-Jarvis等,2020;Hart,2021;Ivan等,2023;Carmody等,2022;Fogel,2018;Lapchak等,2013;Ten,2022;Ramirez等,2017;Schubert等,2010;Dobson,2014)。即使一种药物显示出前景,也只有不到5%能转化应用于人类(Ineichen等,2024),而在那些获得FDA批准的药物中,约30%存在上市后不良反应(Downing等,2017)。这些结果令人担忧。临床试验本身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包括试验设计不佳、药物缺乏疗效、安全性问题、未能维持良好的生产规范、未遵守监管指导、资金不足、公众对患者选择的参与度低,以及招募、入组和 retention问题(Fogel,2018)。潜在有效的药物在人类中未能显示出疗效的其他原因还包括两个很少被讨论的问题:1)转化研究中使用无特定病原体(SPF)动物;2)存在缺陷的单节点靶向做法(Dobson等,2024)(图8)。
图8. 中重度创伤性脑损伤(TBI)缺乏新型有效治疗药物的可能原因示意图。多种因素包括:1)动物模型无法复制人类病情;2)人体试验设计欠佳且忽视年龄和性别特异性差异;3)无特定病原体(SPF)动物的不当使用;4)临床前研究中存在缺陷的单节点靶向做法。几乎所有临床前动物模型均使用经抗生素处理的SPF动物,这些动物无法模拟人类病情,且单节点靶向是以牺牲整体系统为代价的(详见正文)。要更好地理解人体对TBI的反应、识别其进展的新型全身性标志物、发现新型全身性作用治疗药物,就必须进行变革。SPF:无特定病原体;TBI:创伤性脑损伤。
无特定病原体动物:对PubMed的快速检索显示,几乎所有TBI动物研究均使用SPF动物(图8)。SPF动物是指经培育和饲养后不含某些肠道病原体的动物(Dobson等,2019)。商业和机构动物饲养设施会提供认证,证明某一群体不含野外常见的特定病原体,且不同设施排除的病原体可能不同(Dobson等,2019)。SPF动物于20世纪60年代被引入,旨在减少疾病和感染对生物医学研究的干扰(Dobson等,2019)。当时未被认识到的问题是,使用抗生素去除“肠道病原体清单”上的病原体,会改变动物的肠道微生物组和免疫系统(Dobson等,2024)。这种做法忽视了动物和人类均进化出两套基因组这一事实——自身基因组和微生物组,二者通过双向回路协同作用,共同决定个体健康(Dobson等,2021)。相比之下,常规培育和饲养的动物生理结构更完整,更能模拟人类病情。不同的SPF动物、无菌动物和转基因品系或许非常适合机制研究,但如果其微生物组和免疫系统与野生型差异过大,转化潜力可能有限。
例如,Beura及其同事发现,与野生小鼠相比,SPF成年小鼠的免疫系统处于“未成熟”状态,更易受感染(Beura等,2016)。将SPF动物与宠物店的“非清洁”小鼠共同饲养,可使其免疫系统更接近成年人类,从而解决这一问题(Beura等,2016)。同样,Rosshart及其同事表明,重构自然微生物群的SPF型小鼠在感染流感病毒后炎症减轻、存活率提高,且结直肠肿瘤发生率降低(Rosshart等,2017;Rosshart等,2019)。这两个独立研究团队均警示,SPF动物不适合转化研究。最近,Letson及其同事发现,SPF大鼠对创伤应激的反应不同。与常规培育和饲养的动物相比,SPF动物在麻醉和小手术后出现异常血流动力学、出血增加、心律失常及血液学状态改变(Letson等,2019;Dobson等,2020)。因此,Letson等人回归使用常规培育和饲养的动物来完成转化创伤研究(Letson等,2019;Dobson等,202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20世纪60年代初引入以来,SPF状态本身可能已成为影响向人类转化的干扰因素(Kochanek等,2020;Dobson等,2020)。如果最终目标是向人类转化,全球资助机构需进一步审慎审视SPF动物在临床前研究中的不当使用问题。我们至少提议,为保证透明度,应在每篇科学出版物末尾的数据可用性声明中注明SPF状态(Dobson等,2019)。
临床前研究中存在缺陷的单节点靶向做法:转化研究失败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临床前研究中的单节点靶向问题。单节点靶向是一种研究理念或治疗策略,专注于单一环节、通路或症状以减缓继发性损伤进展。它构成了当前医学中“逐步治疗”方法的基础,即逐一识别并治疗单一缺陷,而这往往导致美国外科医生威廉·C·休梅克(William C. Shoemaker)所认为的“不协调且有时相互矛盾的治疗结果”(Shoemaker和Beez,2010)。靶向单一环节治疗TBI或其他创伤状态(如靶向促炎细胞因子(如IL-1)(Lindblad等,2023)或经典信号通路(如核因子κB(NF-κB)通路)(Guo等,2024))至今收效甚微。我们预测,许多新兴的TBI药物(如抗兴奋性毒性药物、TNF-α抑制剂、钙通道阻滞剂、他汀类药物、重组促红细胞生成素、内源性神经保护剂、抗炎剂和间充质基质细胞(Yan等,2024;Pordel等,2024))也可能无法成功转化,因为它们忽视了系统的复杂性。我们认为,基于系统的药物研发方法更有可能提高动物到人类的转化成功率(见下文)。
数十年来,科学家和医务人员接受的训练是将复杂的生命系统分解为更简单的部分,以便更易于研究(Dobson,2016)。通过这种方法,人们获得了大量机制性知识和见解。然而,基因或分子数据与整体机体的关联研究却未能同步跟进(Dobson等,2024;Dobson等,2022;Dobson等,2020)。正如巴塞洛缪(Bartholomew)所言,我们未能将“矮胖子”重新拼凑起来(Bartholomew,1986)。探究病理过程的潜在机制,或药物如何影响细胞或组织培养,只是理解它们在活体内行为的一小步(Dobson等,2019)。这种脱节似乎是上世纪分子革命的产物,该革命专注于机制研究,却以牺牲完整系统为代价(Dobson等,2024)。20世纪6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弗朗西斯·克里克(Sir Francis Crick)曾鼓励这种做法,他写道:“现代生物学运动的最终目标是用物理和化学术语解释所有生物学现象”(Crick,1966)。2000年左右,布鲁姆(Bloom)将这种“单向”方法称为解决谜题的仅有的一块拼图(Bloom,2001;Van Regenmortel,2004;Strange,2005),这也适用于当前的TBI研究。科学还原论在将系统分解为组成部分并对其进行研究方面很重要,但它并不能取代系统本身。
20年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预见了动物到人类转化的问题,提出了“关键路径计划”(Critical Path Initiative),建议:“有必要加强和重建生理学、药理学和临床药理学学科,以具备开发和评估新生物标志物以及衔接动物和人类研究的能力”(FDA,2004;Mahajan和Gupta,2010)。然而,这一关键路径在TBI和其他重大创伤治疗中似乎已被遗忘。重要的是,我们并非主张停止当前的还原论实践,因为它们在设计治疗癌症、遗传性疾病、传染病和中枢神经系统致残性疾病的新药物和疗法方面持续取得成果。但这种方法在创伤治疗中并未奏效。我们提议,国家和国际主要资助机构应重新审视FDA的关键路径计划,并投入同等资金以更好地理解整体系统,开发治疗TBI和其他创伤状态的新型全身性作用药物。
12.未来:21世纪从症状到系统的转变
重度TBI的新型神经保护疗法尚未从临床前研究成功转化为临床应用(Kochanek等,2020,第2353页)。
将TBI研究从基于症状的方法转向基于系统的方法,可能会催生改善患者预后的新药(Dobson等,2024)。这一转变将包括重新关注开展高质量临床前研究,比较SPF(排除特定病原体)和非SPF动物在TBI后的多系统、全身反应,而非像过去那样仅汇总该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全身性作用药物应具备哪些特性?理想情况下,全身性作用药物应能初步靶向早期免疫驱动的中枢神经系统应激反应、促进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偶联、保护内皮–糖萼、减轻免疫功能障碍、预防过度炎症、纠正凝血功能障碍、维持或降低代谢需求,并提供充足氧气以维持线粒体ATP生成(Dobson等,2022;Dobson等,2024)。据我们所知,目前尚无针对TBI(Kochanek等,2020)或其他任何创伤的此类药物。
我们一直在开发一种由腺苷、利多卡因和镁(ALM)组成的全身性作用药物,利用大鼠和猪模型研究其在失血性休克(Dobson等,2024;Dobson和Letson,2020;Dobson等,2023)、烧伤(Dobson等,2024;Davenport等,2023)、骨科创伤(Morris等,2021;Morris等,2023)、手术创伤(Davenport等,2017)和脓毒症(Dobson等,2024;Griffin等,2016)中的应用。有趣的是,ALM疗法似乎能将早期交感神经亢进转变为副交感神经主导(Letson等,2022)、减少内出血并恢复心输出量(Letson和Dobson,2017)、防止内皮糖萼脱落并实现97%的快速修复(Torres Filho等,2017),以及预防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Letson等,2019)。失血性休克后,ALM在47 mmHg的低平均动脉压下仍具有神经保护作用,这可能对TBI治疗具有重要意义(Dobson等,2024;Letson等,2020)。另有研究表明,ALM疗法对缺血性卒中也有显著保护作用(Wang等,2022)。
在采用大鼠中度侧向液压冲击损伤模型开展的早期TBI实验中,静脉推注小剂量3%氯化钠ALM后,再持续4小时静脉滴注0.9%氯化钠ALM,存活率得到改善(100% vs 生理盐水对照组75%)(Letson和Dobson,2018)(补充文件:图9)。与生理盐水对照组相比,ALM还能减轻脑水肿、减少局灶性出血、在50-60 mmHg的较低平均动脉压下使脑血流量显著增加2.5倍、纠正凝血功能障碍、维持血小板功能并降低血乳酸水平(Letson和Dobson,2018)(补充文件:图9)。此外,ALM处理的大鼠血浆中危险信号分子高迁移率族蛋白1(HMGB1)水平下降30%,脑损伤标志物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下降73%。HMGB1是一种新兴的神经元损伤标志物,其高水平反映损伤更严重且炎症反应更强烈(Parker等,2017;Yang等,2021)。ALM的存活表型还与促炎介质IL-1β、TNF-α和正常T细胞表达和分泌调节因子(RANTES)减少70-80%相关(de Souza等,2024)(补充文件:图9)。IL-1β水平降低可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一种标志性细胞因子,会加剧神经炎症(McKee和Lukens,2016)。最后,与生理盐水对照组相比,ALM可预防TBI诱发的神经源性心功能障碍和衰竭(Letson和Dobson,2018)。这项早期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动物在整个实验期间(约5小时)均处于麻醉和通气状态,而未来的研究将使用清醒动物,监测多天并进行认知和运动功能测试。这些研究将包括传统静脉给药与经鼻给药(绕过血脑屏障)的比较。尽管早期概念验证结果看似前景良好,但考虑到从动物到人类转化的复杂性和监管路径(见上文),前路依然漫长(Seyhan,2019)。
13.结论
重度TBI会诱发中枢神经系统驱动的应激反应,影响几乎全身所有器官。原发性损伤释放的大量损伤相关分子模式(DAMPs)信号迅速且持续地放大损伤表型,导致局部继发性脑损伤及全身性免疫功能障碍、炎症、内皮病变、凝血功能障碍和多器官功能障碍。需要新型全身性作用药物将TBI表型转变为“恢复性”存活表型,具体通过减轻中枢神经系统交感神经放电、改善心血管偶联、减少内皮激活、恢复炎症平衡、纠正凝血功能障碍以及为组织线粒体提供充足氧气来实现。21世纪的药物研发要求制药公司和资助机构共同投资于更基于系统的TBI研究方法。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小容量、全身性作用的ALM液体疗法,用于治疗重度TBI,可能适用于院前和院内环境。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