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三月,春韵漫过庭院的篱笆,神州大地正铺开新绿,万紫千红里都裹着春风的轻唤。清晨,住宅楼近旁的小学忽然飘出一片童声——像一群刚破壳的雀儿振翅,脆生生撞进耳里。那是我因时感怀,借《两只老虎》的老调子重新填的《决胜到底》。这曲调太古老,也太响亮,老得能牵出几代人的记忆褶皱:我唱过,父亲年轻时也唱过;它裹着童真的甜,带着岁月的暖,竟悄悄被邻里与学子们记了去,在晨光里轻轻传唱: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忒流氓,忒流氓。
决战决胜到底,决战决胜到底,
中国赢,中国赢!
战疫,本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诗是壮行的酒,歌是冲锋的号,文是搏击的枪。当健康与生命的保卫战骤然打响,艺心便跟着滚烫的脉搏跳动,诗文如潮奔涌,丹青映亮长夜。“文艺抗疫”“艺心战疫”的平台次第生长,登上《人民日报》的版面,跃入“学习强国”的荧屏,漫过千万人的微信对话框,成了特殊时期里一道鲜活的光。此刻人们才懂,文学艺术的力量从不是纸上的墨迹,而是能在人心里敲出鼓点、唤起勇气的星火。
庚子三月,春韵漫过庭院的篱笆,神州大地正铺开新绿,万紫千红里都裹着春风的轻唤。清晨,住宅楼近旁的小学忽然飘出一片童声——像一群刚破壳的雀儿振翅,脆生生撞进耳里。那是我因时感怀,借《两只老虎》的老调子重新填的《决胜到底》。这曲调太古老,也太响亮,老得能牵出几代人的记忆褶皱:我唱过,父亲年轻时也唱过;它裹着童真的甜,带着岁月的暖,竟悄悄被邻里与学子们记了去,在晨光里轻轻传唱: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
忒流氓,忒流氓。
决战决胜到底,决战决胜到底,
中国赢,中国赢!
战疫,本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诗是壮行的酒,歌是冲锋的号,文是搏击的枪。当健康与生命的保卫战骤然打响,艺心便跟着滚烫的脉搏跳动,诗文如潮奔涌,丹青映亮长夜。“文艺抗疫”“艺心战疫”的平台次第生长,登上《人民日报》的版面,跃入“学习强国”的荧屏,漫过千万人的微信对话框,成了特殊时期里一道鲜活的光。此刻人们才懂,文学艺术的力量从不是纸上的墨迹,而是能在人心里敲出鼓点、唤起勇气的星火。
也许是这调子太讨喜,轻快得让人忍不住跟着唱,有人便借它填了新词,《两只老虎》才算真正有了名字。歌声里的欢脱,原是从故事的泪痕里长出来的,素净得像是块未经雕琢的璞玉。它乘着风漂洋过海,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落进东方中国的土壤。相传蒋氏长子蒋经国曾偏爱这支歌,随口哼唱间,便让它悄悄传遍街巷;只是好多人唱了几年、十几年、几十年,都没察觉那“真奇怪”里,裹着一段西方神话里破碎的爱情。
谁能料到,这外来的调子,竟在中国现代史的舞台上,一次次换了“词”的衣裳,成了响当当的战歌、民歌,红极一时,影响深广。它像件轻巧却锋利的武器,在历史的书页里留下了清晰的辙痕——这般“一调传百年,一词映时代”的奇遇,怕是中国音乐史上独一无二的。
北伐的号角吹响时,它成了无形的“枪炮”。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邝鄘,盯着这熟悉的调子,一笔一画填了新词,经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与副主任郭沫若首肯,《国民革命歌》便横空出世。那呐喊撞在城墙砖上,碎成千万片,又被将士们一一拾起,通过高昂的喉咙吼出,震得山河都跟着颤: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
除军阀,除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
齐奋斗,齐奋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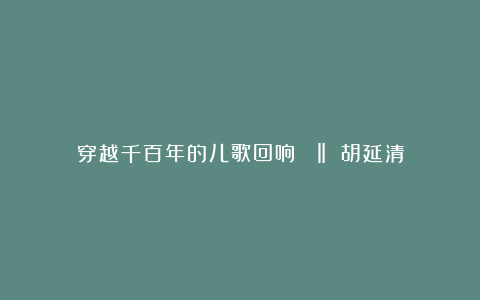
1930年,中原大战骤起。阎锡山联盟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等人,挥师向蒋介石发难。旧调又换了新歌,《打倒老蒋》便在军营里回荡起来,每一个音符都裹着枪刀的寒光,唱得人热血沸腾:
打倒老蒋,打倒老蒋,
除军阀,除军阀!
革命一定成功,革命一定成功,
齐欢唱,齐欢唱!
历史翻页,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依着斗争的需要,再为它填上新词,《土地革命歌》便在田埂上、山村里生了根。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冬子和伙伴们举着小拳头唱它时,眼里亮着星星——像是把夜空里的星光揉碎了,拌在歌声里,甜又有力量: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分田地,分田地。
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
真欢喜,真欢喜。
悠悠百五十年流转,到了近些年,一些地方的人又给它换了“衣裳”。《苍蝇老虎》一开口,人们便心照不宣——那是指贪腐的官:大贪为“虎”,小贪为“蝇”。调子还是老调子,却唱出了新世道的人心向背:
苍蝇老虎,苍蝇老虎,
实在多,实在多。
为何越打越多,为何越打越多,
真奇怪,真奇怪!
不止中国,欧美、日本,还有港台地区,这调子也都换过各式各样的“衣裳”:唱过童谣里的趣事,也唱过民生里的期盼;哼过街头的热闹,也叹过生活的细碎。它像个浪迹天涯的行者,揣着同一副“调子”的骨架,却穿遍了世间不同的“词”的衣裳,在每个时代都活出了新模样。
人们难免惊叹:《两只老虎》,怎么就有这般顽强的生命力?连同它的“前身”《雅克兄弟》,竟真的穿越了千百年,从法兰西的晨钟里,唱到中国的战鼓旁,又落在庚子年春天的童声里——每一次换词,都是一次与时代的对话;每一次传唱,都是一段记忆的延续。
2020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