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藏书辞卜骨新探
——兼谈甲骨书辞的著录问题
冯立昇 清华大学图书馆 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
王雪迎 清华大学图书馆 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
摘要:清华大学藏甲骨中包含数片有毛笔书迹的书辞卜骨,其中见于著录的有5片,先后被著录于胡厚宣、陈梦家等先生的著作和《甲骨文合集》及《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对清华藏5片卜骨的书辞著录信息进行勘误的基础上,给出了更为全面和准确的说明,并探析了另外2片清华藏卜骨上新发现的朱书文字。此外还探讨了甲骨书辞著录存在的问题,对一些不完整的信息做了补充,并且重新统计了目前所见书辞甲骨的总数。
关键词:清华大学藏甲骨 甲骨书辞 书辞著录 朱书 墨书
殷商时期毛笔已成为主要的书写工具,甲骨文中有“聿”字,字形作以手抓笔状,为“笔”之初文。在现存甲骨文字中有一类是用毛笔书写的,且未经契刻,被称为“书辞”。“书辞”是十分特殊的一类文字资料,多出现在甲骨的背面,是研究殷商时期书写方式和书法不可多得的直接史料。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进行的科学发掘中,除了在大量甲骨上发现了刻辞外,在少部分甲骨上也发现了用毛笔写的朱书和墨书,特别是卜甲上的一些书辞,文字相当清晰、美观。甲骨书辞很早就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参加殷墟发掘的董作宾与胡厚宣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对甲骨书辞及相关问题进行过研究。五十年代,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中又对甲骨书辞问题作了更全面的著录和概括性的论述。他们的工作,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被广泛引用。此后甲骨书辞也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刘一曼先生在1991年撰写的《试论殷墟甲骨书辞》一文,对甲骨书辞作了更全面的考察,为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打下了基础。
在清华大学所藏甲骨中,有数片卜骨上被发现有朱书和墨书文字,先后被著录于胡厚宣、陈梦家与刘一曼等先生的著述和《甲骨文合集》及《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受到学界的关注。我们在整理清华大学藏甲骨过程中发现,以往关于清华藏甲骨之书辞的著录,普遍存在著录信息缺漏或讹误的情况。此外,我们还在两片卜骨上新发现了朱书文字,并进行了辨识。本文试图在对以往关于清华大学藏5片卜骨的书辞著录信息进行勘误的基础上,给出更全面和准确的说明,并对新发现的的朱书文字作进一步的探析。此外,我们还将对甲骨书辞著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订正甲骨著录书某些不确切的信息,并根据一些新出史料对目前所见甲骨书辞的数量重新做出统计。为叙述方便,我们将带有笔书文字的甲骨统称为书辞甲骨,而将其中的卜骨和卜甲分别称为书辞卜骨和书辞卜甲。
一、清华所藏5片书辞卜骨及其著录问题
清华所藏书辞甲骨中,见于著录的有5片,均为胡厚宣旧藏,包括1片墨书卜骨和4片朱书卜骨。其中的墨书卜骨,清华甲骨编号65-1251,为2片卜骨缀合后的甲骨编号。《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著录此片甲骨时误给了两个编号,其正、反面分别编号。其正面有契刻文字,收入了缀合后的拓片,《合集》号4284;其反面为书辞,《合集》收入了一幅占据整版篇幅的原大黑白照片,编号35257(图1)。图2是笔者拍摄的这片卜骨的反面彩色照片(局部),清楚地显示文字为墨书,且可辨识“癸酉”两字。
此甲骨的最早著录,见于1951年胡厚宣编著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以下简称《宁沪》)[1]。因缀合前为2片卜骨,最初著录为两片。《宁沪》给出了2片的摹本。其中一片编号为2.52,因反面无字,只摹了正面刻辞(见图3)。另一片包括正面刻辞的摹本(见图4)编号2.55和反面书辞的摹本编号2.56(见图5),卜骨反面只摹写了可辨识的“癸酉”两字和钻凿部分。 “癸酉”二字为倒书,其字形比正面刻辞要大许多。胡厚宣先生在《宁沪》序中称其著录的5片甲骨都是“为毛笔濡朱所书”。胡先生记述不是十分准确,虽然其余4片字迹均呈红褐色,但此片甲骨上的书写文字为墨书。
陈梦家先生在1956年出版《殷虚卜辞综述》中,对这片卜骨做了著录,给出了更明确的信息:“宁沪2.56 骨 正面(宁沪2.55)刻卜辞 武丁朱书(倒书)。”[2]他也将这一书辞误为“朱书”。
裘锡圭先生在《论“历组卜辞”的时代》一文中对此片卜骨的书辞给予了特别关注。他写道:“《宁沪》2.56的’酉’字,《宁沪》2.56是2.55的反面,这一片卜骨的正面刻有宾组卜人殻的卜辞,反面有朱书的’癸酉’二字,’酉’字作,写法与历组父丁类卜辞全同。这充分说明认为这种写法到第三期才出现是错误的。”[3]受《宁沪》影响,他也误认为这一书辞是“朱书”。
刘一曼先生的《试论殷墟甲骨书辞》一文,承袭了陈梦家的“朱书”之误,但对书辞的年代提出了不同看法。她指出[4];
“正面的卜辞为’辛亥卜,㱿贞:乎?’、’贞:羽甲申步?’、’贞:勿隹甲申步?’(甲字缺横画),属武丁宾组卜辞。值得注意的是此版反面朱书’癸酉’二字,字粗大,酉字的写法似康丁、武乙时的书体。”
她认为卜骨反面记干支,多见于三、四期卜骨。并以《小屯南地甲骨》中的康丁、武乙时期反面“倒刻”干支的十多个实例分析,说明“此版书辞时代大概也应属康丁、武乙时期。”
刘一曼先生还对二十多片卜骨书辞进行了考察,认为在正面有刻辞的卜骨中,书辞与正面刻辞的内容毫无联系,且书辞字大笔肥,与刻辞相差甚远,因此“卜骨上的书辞与刻辞大概不是同时所作,两者性质是不同的”。
清华卜骨上的“癸酉”二字,陈梦家认为是为武丁书辞,新出版的《甲骨文摹本大系》(编号50346)则归为师历间类书体。由图2照片可知,其书体与师历间类或宾组卜辞书体明显不同,但与历组二类卜辞一致。如合集34777(历组二类,图6)卜骨刻辞中的“癸酉”二字,与墨书“癸酉”在书体上相当一致。而合集32387(历组二类,图7)“乙酉”中的“酉”字,与墨书之“酉”字极为相似。刘一先生推定其为康丁、武乙时的书体,因与正面刻辞时间相距太久,也不尽合理。我们认为,推定为武丁晚期至祖庚、祖甲时期更为合适。这大概也是裘先生认为此片甲骨可为其主张提供证据的原因。
编辑《合集》时,清华两片藏骨(即《宁沪》2.52与2.55 )已经完成缀合。《合集》收录了两片甲骨缀合后的正面拓片和反面照片,反映了缀合新成果。但《合集》将拓片和照片分别编号,收在不同的分册中,且未加说明,容易引起误解,给研究者带来不便。《甲骨文合集释文》在《合集》35257释文“癸酉”后标注了“墨书、大字”,著录信息是准确的。
《宁沪》还著录另外4片书辞卜骨,它们是《宁沪》1.217、1.219、1.250和1.579(图8-11)。
这4片如 《宁沪》 序所称,确为朱书。《宁沪》给出了此4片书辞的摹本。4片卜骨中,1.219 、1.250正面无字,所以仅摹反面书辞。编号1.579的卜骨正面有刻辞,《宁沪》也给出了摹本(编号1.578)(图12)。但1.217正面有刻辞,却没有给出摹本。
陈梦家所著《殷虚卜辞综述》对这4片卜骨也进行了著录,内容如下:
清华藏骨(宁沪1.217) 正面刻卜辞 康丁墨书(倒书) 失摹正面
清华藏骨(宁沪1.219 ) 残片 武文墨书
清华藏骨(宁沪1.250) 残片 武文墨书
清华藏骨(宁沪1.579) 正面( 宁沪1.578)刻卜辞 武文墨书[5]
陈梦家先生指出《宁沪》1.217“失摹正面”,经核实物,是确切的。这片甲骨清华编号为72-1317,其反面朱书的三个字“乙五牢”都较大(图13),“乙”和“牢”的字长都在2厘米左右,而其正面的契刻文字却很小,刻在左侧上面边缘处,有的字还模糊不清,不易发现。大概这样的原因,胡厚宣先生当初没有发现正面存在刻辞。经辨识,正面的文字为“其又羌(?),又正。”(图14)为无名组卜辞。陈梦家先生根据书体推断此书辞的年代为康丁时期,此说可从。
《宁沪》1.250和1.219两片甲骨,清华甲骨编号为72-1315(图15)和72-1316(图16),文字均为朱书,正面没有刻辞。陈梦家推定其书辞年代均为武乙、文丁时期。清华72-1315(《宁沪》1.250),《合集》著录号为35258,收入了一张反面的黑白照片,后又重见《合集》41389,收录了文字的摹本。《甲骨文合集释文》在《合集》35258条没有给出释文,但注出“墨书,字跡不清”。《甲骨文合集释文》在41389条下给出释文:“……牛二。才四月。王……”。与《宁沪》1.250摹本内容一致。《试论殷墟甲骨书辞》一文根据《宁沪》著录该书辞释文后,又补充说明其“正面有卜辞,但原书未收录”,这一说法有误,应是笔误。刘先生所说正面有卜辞的卜骨,当为陈梦家先生所称“失摹正面”的《宁沪》1.217。
有研究著作在著录《宁沪》1.217时采用了陈梦家所称“失摹正面”的说明,而著录《宁沪》1.250(即《合集》41389)时给出的说明是“属乙辛黄组卜辞,正面有卜辞,原书未录” [6]。称《宁沪》1.250“正面有卜辞”,则采用了刘文的错误说法。
清华甲骨72-1316(《宁沪》1.219),《合集》号为35259,收录了此卜骨的一张反面的黑白照片。《甲骨文合集释文》在35259条下给出书辞释文和说明:“妣庚(墨書、大字)”。《宁沪》1.579,清华甲骨编号为64-1223,正面刻辞《宁沪》1.578只残存一“用”字(见图12)。反面朱书一“三”字,意义不明。《合集》没有著录。
值得注意的是,《甲骨文合集释文》注明《合集》收录的清华4片卜骨均为“墨书”,与《宁沪》序称其著录的5片卜骨书辞均“为毛笔濡朱所书”形成鲜明对照。《殷虚卜辞综述》也注明4片清华藏骨为“墨书”,却称另一片宁沪2.56 骨为“朱书”,而实际上4片清华藏骨均为朱书,另一片为“墨书”。陈梦家先生可能发现了5片卜骨书辞中,既有朱书又有墨书,但将二者记颠倒了,导致了不该出现的错误。
以上我们对清华所藏五片书辞卜骨及其著录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并对以往的一些著录内容做了校勘,为了便于读者更易于了解整体信息,表1对相关著录与校勘内容做了汇总。
表1 五片书辞甲骨著录内容及勘误
二、两片卜骨中新发现的毛笔书迹及其文字辨识
我们最近在整理清华藏甲骨过程中,又发现2片卜骨上有毛笔书迹。这2片清华藏甲骨编号分别为49-1014和72-1318。其中,清华甲骨49-1014,也是胡厚宣先生旧藏,《宁沪》编号为1.79(正)、1.80(反),图17和图18是《宁沪》收录的正、反面的摹本。这片卜骨正、反两面都有刻辞,为历无类卜辞。正面的刻辞为:“其又岁于小丁”,“父戊岁,王。”反面的刻辞为:“辛□卜:王□不冓(遘)雨。”《合集》著录了这片甲骨,编号为27331,收入正反两面的拓片。《甲骨文合集释文》给出的《合集》27331正释文,与《宁沪》1.79相同,其给出《合集》27331反释文为“辛□卜,王□不冓□。”“雨”字因拓片模糊不清没有释出。但观察实物,“雨”字清晰可见,《宁沪》1.80摹本无误。
在这片扇骨反面的骨边上,我们发现有倒写的两个朱笔大字。(图19) 这两个朱书文字为“岁匚丁”,写得圆润流畅,内容与祭祀商先公报丁有关。图20是其文字的摹写。其中“岁”的字体和写法,与《小屯南地甲骨》编号2011的朱书卜骨书辞“岁”字(图21)[7]非常相似。
此片卜骨反面上的朱书字长度约2-3厘米,而同一面的刻辞“不”等字长度只有0.2-0.6厘米。由于正反面均有刻辞,而反面又有倒书的书辞,这在现存甲骨中是非常少见的。
关于“岁匚丁”二字年代,当为武乙、文丁时期朱书。其“岁”字与《合集》36978(黄组)刻辞中的“岁”字(图22)一致,“匚丁”与《合集》35465(黄组)刻辞中的“匚丁”(图23)十分相似。
清华藏甲骨72-1318,未曾被著录,正面有两个“吉”字(残)刻辞(图24),为无名组卜辞。卜骨反面有倒书的朱笔大字(图25)。可以辨识的两字为“彡
二(乞)”(图26是其文字的摹写),书辞内容涉及到祭祀。
这2片卜骨的书辞,与前面5片卜骨书辞具有相同的特点,即它们都书于卜骨反面骨扇的边上,且均为倒书。书辞方向均以骨臼为下,而且与刻辞方向相反。这与刘一曼先生文章介绍的绝大多数书辞卜骨的特点,是一致的。
三、甲骨书辞的著录及相关问题探讨
甲骨书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很早就受到考古学家和古文字专家的关注。但甲骨上书辞的数量远不如刻辞多,长期以来,研究者主要关注的还是甲骨刻辞。对于甲骨书辞的研究,重点在探讨书辞与刻辞的关系,缺乏对书辞内容、性质和自身特点的研究。与甲骨刻辞相比,书辞保存更难,有的已完全褪色,有的字迹模糊,清晰可辨的书辞数量十分有限。除了甲骨书辞的数量少、残片多和字迹不清等客观因素外,未能妥善著录、资料不易获得也是造成书辞研究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目前甲骨书辞的著录,存在的问题较多。前面我们已经有所涉及,这里作进一步的讨论。甲骨著录的重要手段是传拓,但甲骨书辞在拓片中难以显示。早期出版的甲骨著录书一般只发表甲骨刻辞拓本,很少收录甲骨书辞。有的著录书在发表拓本的同时,虽也收录了书辞照片,因照相或制版技术欠佳,且以黑白照片为主,也造成甲骨书辞不易辨识,影响了进一步利用。摹本和文字说明是比较有效的著录方式,但摹本无法反映出书辞是朱书还是墨书,文字描述又常常不够全面和准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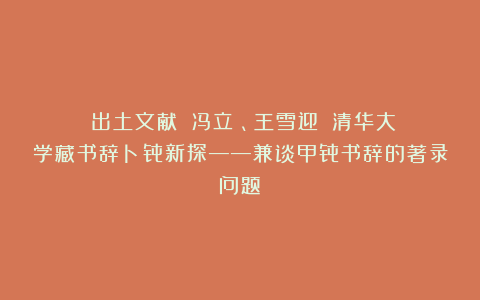
甲骨收藏单位和整理者以往对甲骨书辞的关注或重视也不够,在整理所藏甲骨或编著甲骨著录书时,或书辞失收,或书辞信息有误。下面以两个例子说明。
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收录的一片卜甲,包括正、反面摹本(编号1、2),其反面为书辞摹本(编号2),已包含了书辞的信息。但《殷契拾掇二编》(简称《掇二》)(编号1)和《合集》12628均只收录了正面刻辞的拓片,而未收其反面书辞。该龟板其反面右侧甲桥位置有一条书辞“畫來卅”,笔画圆润。书辞包含了较重要的信息,其内容属于署辞,记录了部族畫向商王进贡龟甲三十版。
又如《掇二》收录的一片卜骨,包括正面拓片(编号78ABC)和反面局部摹本(编号78C),其正面为刻辞,反面为书辞(图27)。《合集》28089收录了其正面拓片和反面摹本。《甲骨文合集释文》28089反面书辞释文为:“……夕[岁]妣庚中 ……(墨書)”,同样包含了重要的信息,内容涉及对妣庚等先人的祭祀。《掇二》和《甲骨文合集释文》均标注书辞为“墨书”。这片甲骨现藏上海博物馆,2009 年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以下简称《上博》)编号为2426.3。这部重要著录书出版时,仅收录了这片卜骨正面刻辞的拓片和片形部位释文[8],反面的书辞不仅没有给出照片,连摹本和释文也失收。这或许与《上博》的编写体例有关,但也反映了编者当时对甲骨书辞重视不够。
2014年,濮茅左先生编著的《殷商甲骨文》一书出版。该书为《先秦书法艺术丛刊》的一种,特意收录了两片书辞甲骨,包括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一片卜甲的“甲骨文朱书”(即《合集》18903)和上海博物馆卜骨“甲骨文墨书”[9]。
《殷商甲骨文》收入了《上博》2426.3反面书辞的彩色照片(图28)[10],给出了书辞的摹本和释文,信息较完整,弥补了《上海博物館藏甲骨文字》的不足。《殷商甲骨文》著录时采用了前人的说法,将这片卜骨的书辞著录为“墨书”,但从这片卜骨书辞的彩色照片看,字迹呈褐色,应属朱书,而不是“甲骨文墨书”。
由于甲骨书辞非常少见,收藏单位也认识到甲骨书辞的重要价值,开始重视甲骨书辞资料的发掘和展示。2022年3月1日至9月4日,上海博物馆举办了“盛世芳华——上海博物馆受赠文物展”,其中《上博》2426.3的甲骨书辞是此次展览重点推荐的内容。上博的展览说明称:“上海博物馆藏甲骨中还有罕见的人头骨刻辞、墨书文字,为学界所重视。”对卜骨书辞彩色照片及其摹本的文字说明是“上博藏甲骨上的毛笔墨书”。说明中的“墨书文字”和“毛笔墨书”,都不确切,将朱书误为“墨书”。
目前甲骨书辞的著录存在的各种问题,也给甲骨书辞的数量统计工作带来了困难。刘一曼先生在《试论殷墟甲骨书辞》一文指出:“很难精确统计出甲骨书辞的数目。这里只能根据已发表的及本人所能收集到的书辞资料作一粗略的统计与扼要的论述。”[11]该文统计的结果是:见于著录的书辞甲骨74片,其中卜骨26片、卜甲48片。经我们重新核对,26片中的一片书辞卜骨(《殷虚文字甲编》3586)被统计了两次,实际应为25片,因此当时统计的书辞甲骨数目实为73片。刘文仅统计了《掇二》的400和401两片书辞卜骨,遗漏了《掇二》78C。因此,当时能够掌握的书辞甲骨数量实为74片,数量十分有限。
近些年来,又有少量甲骨书辞被公布。2012年《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出版,公布了三片书辞卜骨,其编号分别为436、471、488号。《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也为甲骨书辞著录提供了新的范例,为编撰甲骨著录书和整理工作提供了借鉴。著录内容包括拓本图版、摹本图版、清晰彩色照片图版、释文和文字说明等。为了清晰反映书辞的文字内容,471、488两片卜骨还收入局部放大照片。下面是编号436的卜骨书辞著录的文字内容:
436 02H55:61反卜骨 拓本图版122 摹本图版122 照片图版137。一期卜辞。
骨面呈浅黄色。牛肩胛骨下部残片。质地稍差。残长 14.5 厘米,残宽6.5 厘米。
戊申卜:。
此片为朱书文字。字体较甲骨刻辞粗大,笔风圆润流畅。字的行款,与骨臼方向相反,为倒书。[12]
这片卜骨的书辞出现了“卜”字,表明卜骨书辞中也存在卜辞,不都是记事书辞。
近年甲骨书辞受到收藏单位重视,还可举出一例。为庆祝甲骨文发现120周年,2019年天津博物馆遴选出馆藏120片甲骨精品,举办了“殷契重光——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特展”。天津博物馆在藏品中特意选出一件较小的书辞卜甲,与另一片其上有“册”和“畫”字的刻辞卜骨一同展出。《殷契重光——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特展》对此片卜骨的说明如下:
甲骨 120商祖庚、祖甲 朱书卜甲
纵5.8、横3.2厘米
此卜甲背面,留有毛笔蘸朱砂所写出的字迹。朱书文字虽然已经难以识别,但却直接证明了商代毛笔书写的存在。王襄旧藏、王襄家属捐赠。[13]
从这片卜甲的正反面照片(图29、图30)看,卜甲背面的朱书文字,比正面的刻辞要大不少。朱书文字虽难以全部识别,但其中三字应是“甲寅卜”,可以辨识。“卜”字虽已残缺,只有上半部分,但也比较清楚。这一版卜甲正面上半部分刻辞为:“甲寅卜,王曰,贞翌乙卯其田,亡灾。于谷。”,可知反面书辞是与刻辞相关联的卜辞,也是正向书写,与刻辞方向相同。
《试论殷墟甲骨书辞》在概括卜甲书辞特点时称:“这48片卜甲书辞,全部书于卜甲之反面,字的方向与卜甲正面及反面的刻辞相同,即均为正书。书辞的位置多在甲桥和中缝之两侧。它们的时代都属于武丁时期。”[14]天津博物馆的这片朱书卜甲,与刘一曼先生的概括基本一致,但有一点不同,即它的年代是“祖庚、祖甲”时期,而不是武丁时期。因此也具有独特的价值。
结语:期待发现更多的甲骨书辞
根据新见书辞资料,我们可对目前所见书辞甲骨的数量重新做出统计。之前学界统计掌握的书辞甲骨数量为74片,其中书辞卜骨26片,书辞卜甲48片。现清华藏甲骨中新发现书辞卜骨2片,加上已公布考古发掘的小屯村中村南书辞卜骨3片,目前所见书辞卜骨数量达31片。原统计书辞卜甲数量为48片,可增加天津博物馆藏朱书卜甲1片,最近马尚在台湾历史博物馆所藏一片卜甲(河南博物馆旧藏)的反面发现有毛笔墨书“子”字,又补充一书辞卜甲。[15]这样,书辞卜甲共计50片。因此可以确定,目前所见书辞甲骨的总数不少于81片。
天津博物馆所藏朱书文字卜甲的正面刻辞,已被《合集》著录,编号为24471,但展览之前外界并不知其反面还有书辞。于镇洲等于2001年编纂的《河南省运台古物甲骨文专集》也未关注到那片写有“子”字的卜甲书辞。因此,在目前已著录和未整理的甲骨中,应当还存在未发现的书辞。如果收藏单位的整理者,进一步核对和仔细观察,可能会发现新的甲骨书辞。随着收藏单位和学界对书辞甲骨关注和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新科技手段在整理工作的进一步应用,发现更多的书辞甲骨、著录和获取更全面的书辞信息,也是值得期待的。
附记:本文初稿完成后,承蒙黄德宽先生、沈建华先生审阅指正,谨致谢忱!
注 释
* 本文为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规划项目“清华大学藏甲骨整理” (G3018)阶段性成果。
[1] 胡厚宣:《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北京:来薰阁书店,1951年,下册,第113—114页。
[2]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4页。
[3] 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中华书局出版社,1981年,第270页。
[4] 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考古》1991年第6期,第547页。
[5]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14页。
[6] 郝文勉,王建军:《甲骨文书法风格》,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39页。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小屯南地甲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上册第一分册,第316页。
[8] 上海博物馆编,濮茅左编著,谢海元裱拓:《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文字》,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上册,第8—9页。
[9] 濮茅左:《殷商甲骨文》,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259—260页。
[10] 濮茅左:《殷商甲骨文》,第260页。
[11] 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考古》1991年第6期,第546页。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下册,第722页。
[13] 天津博物馆编:《殷契重光——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特展》,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年,第130页。
[14] 刘一曼:《试论殷墟甲骨书辞》,《考古》1991年第6期,第548页。
[15] 马尚:《河南博物馆旧藏甲骨新缀新见》,《文献》2024年第1期,第21—21页。
原载《出土文献》2025年第3期,引用请据原文。本刊文章已收入“中国知网”,欢迎各位读者下载阅读。
排版丨朱超
审核丨张官鑫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