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9-24 09:49
她出生于“中国最牛的家族”中,受家庭的影响,她成为了我国“女物理学家”之一,并且还被后人称之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然而,她却命运多舛,在美国留学后,回国时却遭到了美方两年的故意遏制和阻拦。
回到祖国后,她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祖国的人才培养上,结果却被囚禁6年,在她出狱时自己的家族已经“家破人亡”。
那么这位“中国的居里夫人”究竟是谁呢?她的家族又究竟有多牛呢?她为何又会被囚禁6年呢?
她叫王明贞。1906年的冬天,江苏常州,一个讲究门第的大家庭添了个女娃。许多年后,人们提起她,总爱往她身上贴两个标签:学物理的女人、骨子里倔。其实这两个词,正好把她的一辈子串起来了。
先说家门。她从小在一屋子匾额、家训、旧书里长大。长辈们闲下来,嘴里常念到好几位“祖上”的名字:明代那位进辅内阁的王鏊,清末军机处里当差的王颂蔚——还教过蔡元培;还有一位不太“按规矩来”的祖母谢长达,创办女子学校,主张女人读书,并不肯把女儿们赶进闺阁。这些故事听多了,孩子耳朵里塞满了“学问”两个字。
她的父亲王季同,是个典型的“手巧脑快”的人,既做学问也爱摆弄机器,折腾出了转动式变压器。家里男孩多,气氛有点像小型理工科俱乐部。饭桌上不聊菜好不好吃,常常是“这一题你想过没有”。母亲去世得早,家里慢慢多了规矩,但也多了一种不言的坚忍。小姑娘王明贞被练出来的,不爱吵,只爱琢磨。
这一支家族往后做学问的人像打出的竹节,一个接一个。她的几位兄弟里,有的去做理论物理,有的扎在半导体器件里,还有在微电子领域深耕多年的人;亲眷里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钱三强。旁人听得眼花缭乱,觉得这家门风“太盛”,其实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这种盛大有时也是压力,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小就把她往上推,推到一个“不许失误”的位置上。
她读书很能坐得住。1923年一家搬到上海,她进了晏摩氏女中。教会学校的课严,她更严,书本翻得起毛边。理科题对她像谜语,一道一道拆开来,拆完了还能转过身去给同学讲个明白。高二期末,化学老师让她上台收个尾,她站在讲台上一口气讲清楚了那学期的脉络,台下的同学半是佩服半是发愣,给她起了个外号,意思就是“这人像个小老师”。
转机和阻力,总是一起来。中学毕业,她想去读大学,父亲有他的执拗——他少年也靠自学出头,便盼着孩子们也能自修成才。继母更直接,打算给她定亲,把“人生”先安排好。那会儿她还年轻,嘴上不善辩,心里却拎得清:订婚礼物照收,戒指没戴,心里更没松口。幸好对方不着急成亲,先去了德国求学。她就挤出了一个气口,等到了最可靠的援手——姐姐回家了。
姐姐一回来,像一盏灯。她得到了家里的松口,进了金陵女子大学。可人一旦有了判断,就不肯将就。她在金陵碰上不公平的对待,索性转去北平,进了燕京大学物理系。北方的冬天冷,实验室里也不甚宽裕,她却也不急,三年级开始就帮着教护士预科的数学课,粉笔在手上熟了,讲题的口齿也越练越利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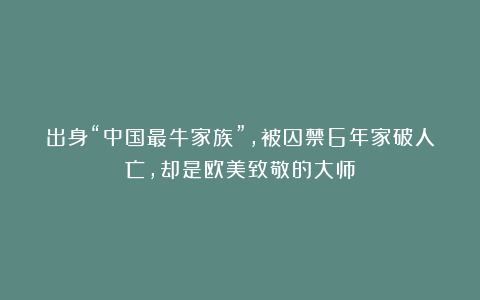
话说回来,许多年轻人的难处不在心气,而在钱。她申请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机会,对方痛快,许诺四年全额奖学金,唯独路费得自己想办法。她不抱怨,边做助教边读研究生,两年里攒下些钱,也拿了燕京的硕士学位,但那点钱放到船票上,还是差口气。这时候,金陵女大的校长吴贻芳向她伸了手:来教书吧,数学、物理都要你。六年,黑板上写满了公式,存折上也慢慢有了数,她终于把路费一块块凑齐。
跨过太平洋,密歇根大学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个学生:亚洲来的女孩,年纪不大,眼神定。那一班学生里,外国人就她一个,女生也就她一个。异样的眼光是难免的,可她没有绕着走,她对付别人的方式,就是把题做对,把论文写好。第一个学年过去,成绩单像一把刀把,握在手里有分量;老师们记住了这个名字,她也慢慢被领进了更高的屋子。
她的天线,很快接上了当时理论物理界的两根主干——古德斯密特、乌伦贝克。那些年里,她和老师合作写文章,往《应用物理》这样的刊物投;校内外给她的褒奖也接连不断,“金钥匙”拿了又拿。到了第三年,她开始收拢精力写博士论文,绕着玻尔兹曼方程打转,把许多难啃的地方一口口咬开。战火未平的1945年,她和导师把“布朗运动的理论”系统梳理,发在《近代物理评论》上。这文章并不花俏,像把一条河的水路铺给后来者,谁过河都要踩她铺的那几块石头。
毕业后,她得到重磅推荐,进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做理论物理组的副研究员。那是战后科学界的风口之地,雷达、信号、算法、元件,忙得连日光都觉得短。她在里面做了几年,心里却始终装着一件事:要回去。1953年,她递出离职,盘算着半年内启程。谁知这一路并不由她。雷达相关的工作被扣上“保密”的印子,人卡在波士顿,箱子都收拾好了,船票却迟迟下不来。她蜗在出租的小屋里,日复一日地等,等到第二年的秋天,也没个准信。
她不是没想过退路,但心里拴着的那根绳子更紧——她要回中国。两年之后,局面终于松动,消息来得很短:可以走了。她把钥匙往屋主桌上一放,提着不多的家当上路。能让这扇门打开的,是远方几封来回奔走的信,也是那时的一位总理的关照。1955年,她落地的那刻,心里有一种“终于到家”的静。
回国后,清华向她伸出了手。她在那儿站上讲台,写下“力学”“统计”“热学”,把自己在国外装进脑袋里的那点硬货,一点点掰给学生。那几年全国百废待兴,科研设备紧、资料缺,她没有抱怨“我施展不开”,而是把重心往教学上压,想着多培养几个有手有脚、有脑有心的年轻人。她的课堂,没有高高在上的口气。学生敢提问,她就笑眯眯地说:“问得好,咱们一起算。”
生活本来也该这样平稳延下去。可在某个年份,风向突变。1968年,一个平常的上课日,门忽然被推开,一群人冲进来,把一脸惊讶的她带走。她没来得及把粉笔放回原处,黑板上还留着半截公式。从那天起,她从讲台掉进了一个黑暗的坑里。罪名来得轻巧,解释没有用。她被关了起来,窗子小,日子长。她知道自己没有对不起这片土地,于是把心收紧,像在做一场漫长的计算,扣掉恐惧、扣掉愤怒,剩下的,就是活下去。
六年,足够让一个家破碎成不认得的样子。等到1974年重见天日,她走出那扇门,才知道许多亲人已不在,屋檐散了,人也散了。她没有四处讲自己的委屈,也没有把余生交给抱怨。她提着那只旧提包,回到清华,照旧写板书、给作业、催论文,日子像是一条缝被她一点点缝合起来。
她的学生后来提起来这个老师,总说她不苛、不软,且有耐心。她最喜欢的,是讲到一个关键处,停顿一下,抬眼望着全班:“这一步别偷懒,你们自己算。”有时候讲到兴起,她会丢出一个小故事:年轻时在美国宿舍里抠着手指算到深夜,手上沾的粉笔灰怎么也洗不干净。学生们爱笑,她也笑,两颊淡淡的皱纹像两条温柔的水纹。
岁月给她的是漫长。2010年8月的一个日子,她在北京合上了眼,活了一百零四岁。这个数字听起来像个奇迹,但更大的奇迹,是她在那些拧巴的关口都没失掉自己。她的文章仍被后人翻检,课堂里的话在别的教室里被重复。她的家族曾经风光,后来风雨俱来;她自己从巅峰走进暗夜,又从暗夜里走回教室。
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命运像被时代牵着走。她这一生,也确实如此。可我总觉得,在被牵着走的同时,她仍悄悄抓住了一截属于自己的缰绳。她坚持回国,选择教书,承受了不应承受的苦难,却没用苦难给自己立碑。她像在黑板上做题那样,认真、干净,不多一句。故事讲到这里,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如果没有那六年,她会不会在科研上走得更远?但也许,她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把光分给后人,自己就不必站在灯下了。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