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脉鉴今
青铜兵器溯源:吴越匠人的楚地西迁
一一越王勾践剑在楚:一部技术移民的文化融合启示录之一
文/张卫平
编者小语 2025年5月15日出版的《荆州日报》“文化荆州”专版,持续推出“楚脉鉴今”,刊发了“郢都故事”的《越王勾践剑在楚:一部技术移民的文化融合启示录》。现分三期转发。
在荆州,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越王勾践剑”,无论是荆州博物馆里陈列的四把越王刽,还是执荆州文创产品之牛耳的高仿真越王勾践剑,都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甚至,在征集荆州文化标识物时,“越王勾践剑”的呼声也很高。
其实,“越王勾践剑”对于荆州的意义,早已超出了青铜宝剑的本身,而成为楚国技术移民史的见证者。
1965年冬天,在荆州望山楚墓群的考古发掘现场,一把沉睡千年的宝剑破土而出,震撼了整个中国考古学界。
“越王勾践剑”的横空出世,不仅披露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传奇,更是揭开了吴越青铜兵器制造技术的神秘面纱,牵出了楚国与吴越技术移民融合这一隐匿于岁月长河中的精彩篇章。
青铜兵器溯源:吴越匠人的楚地西迁
在中国古代,一件兵器的发明与创新,往往决定着一场战争的胜与负。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周朝各诸侯国君王们一直期望着手中的刀剑更加锋利。越王剑,就是其中最具杀伤力的神兵利器,是青铜剑发展到极致的最高表现形态。
经过科学检测,荆州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是用复合金属工艺铸造而成,在剑身的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是复合剑的典型代表。
冶炼专家认为,这种剑身与剑刃硬度完全不同、刚柔并济的青铜剑,是古代青铜铸造的巅峰之作。
春秋时期,楚国的青铜兵器制造水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远远落后于吴越地区。彼时的吴越,青铜剑以其精良工艺闻名于世,剑刃削铁如泥,剑身纹饰精美绝伦。
与之相比,楚国早期的青铜剑就显得粗糙简陋了,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荆州望山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历经 2400 年的岁月洗礼,依旧寒光逼人,其剑身的菱形暗格纹、独特的铜锡配比等工艺,与当阳赵家湖楚墓出土的早期楚剑粗糙形制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照。
越王勾践剑
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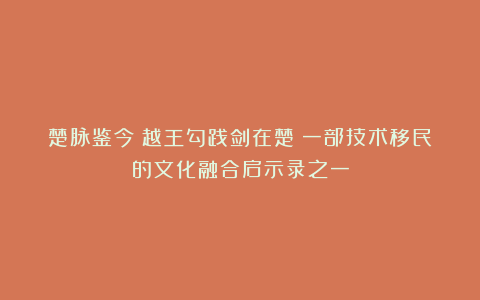
长55.6厘米
1965年荆州望山一号楚墓出土
湖北省博物馆藏
剑身近格处刻有二行八字错金鸟篆铭文:“越王鸠浅(自乍用剑。”“鸠浅”,即越王勾践,为春秋时期越国君主勾践所佩之剑。剑身向外翻卷作圆箍形,内铸有11道同心圆。剑格宽4.6厘米,正面用蓝色琉璃,背面用绿松石镶嵌成美丽花纹,满饰黑色菱形几何纹饰。
此剑历经2400余年,刃部仍锋利无比,试之能将16层白纸划破,有着“天下第一剑”的美誉。
图源:湖北文物
文史资料显示,“吴越兵器制造技术空前绝后”。用古代兵器史学家的话来说,在荆州等地出土的吴越君王宝剑与矛证明,吴越生产的青铜兵器“是世界青铜文化史登峰造极之作”。
因此,春秋时期,上至天子,下至诸侯,无一不以拥有一把吴越青铜宝剑为荣。楚人尚武,是楚文化中最为显著的特点之一。
爱剑,就是楚人尚武精神的具体体现。公元前333年,当楚国大军的铁蹄踏上吴越大地时,楚人在吴越之地大肆搜罗铸剑名师和名剑。于是,楚人将吴越两国的青铜兵器抢劫一空。
荆州古城东门(宾阳楼)夜景
从荆州出土的五代越王剑与吴王夫差矛,就用实物证实了历史文献的记载。楚人对吴越宝剑的渴求,实际上是对吴越工匠铸剑工艺的渴求。
楚国强虏吴越工匠之事,犹如二战时期美国用武力“招揽德国工程师一样。正是在德国工程师帮助下,美国的导弹技术才得以突飞猛进,并且催生了原子弹。
楚国也一样,在用武力吞并吴越后,也冶铸出一大批“陆斩犀兕,水截蛟龙”的名剑,成为春秋末期的产剑名地。
考古研究表明,楚国早期的青铜剑,非常明显地模仿了吴越“扁茎无格”的形制,由于刃部易折,在实战性方面大打折扣。
直到楚国以“拿来主义”为技术路线,才一举突破技术瓶颈,生产出独特的“楚式剑”。
对此,清华简《系年》揭示,楚国通过“迁其重器,俘其巧工”的策略,将绍兴的越人铸剑师迁至荆州纪南城西南的“冶父”作坊区。
这些铸剑师,怀揣着精湛的技艺与宝贵的经验,在异国他乡继续传承和发展铸剑技术,从而使军事工业得到突破性发展。
考古学家发现,楚惠王灭越(前 334 年)后,湖北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铜剑已普遍采用越式复合铸造法。
在论及楚国青铜器制造业发展时,楚学大师张正明先生曾以“外求诸人而博采众长,内求于已而独创一格”予以概括。楚国的青铜剑乃至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就是这样后来居上,使之成为支撑美仑美奂楚文化高崇邃宇的六大支柱之一。
因此,楚国这一兵器制造技术创新的巨大飞跃,其实就是一段残酷而充满智慧的人才争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