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药三年,病情反而加重了!”这句来自患者家属的控诉,折射出阿尔茨海默病(AD)治疗领域的深层困境。不同于其他疾病的治疗逻辑,AD这种进行性恶化的疾病特性,使得“有效”的定义始终笼罩在争议迷雾之中——究竟是该追求症状的改善,还是病程的延缓甚至逆转?
传统药物:有限缓解与潜在风险
用于治疗AD的传统药物,如胆碱酯酶抑制剂(ChEIs,例如多奈哌齐、卡巴拉汀等)和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拮抗剂(例如美金刚),只能缓解症状,无法阻止疾病的发展,使得开发能够改变疾病进程的治疗药物(DMTs)成为了迫切的临床需求。【1】
其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腹泻、恶心、睡眠障碍等,严重者可出现心动过缓,心脏功能较差的老年人群需谨慎使用该类药物。
另外,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贾建平教授团队2025年的一项关于ChEIs的研究发现,轻度认知障碍(MCI)患者服用ChEIs不仅没起到保护作用,反而让发展成AD的风险飙升。该研究纳入了558例患者,结果表明,服药组患者发展成AD的风险比未服药组高77%,其认知衰退速度更快,记忆力、思考能力下降得更明显。MCI是唯一可能逆转的阶段,但逆转的关键不是盲目吃药,而是科学管理。这次研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对抗AD,需要更聪明的策略。
新型药物:希望曙光与争议迷雾
近年来,以Aβ单抗和脑肠轴调节剂为代表的新型AD治疗药物相继涌现,为临床治疗带来了突破性希望,但其作用机制、疗效与安全性仍引发学界广泛争议。
1.Aβ单抗
(1)Aβ因果地位不明:目前尚无证据证明Aβ是AD发病的原因还是疾病过程的伴随结果。
(2)Aβ单抗治疗的微弱临床获益:尽管Aβ单抗药物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一定的延缓病程发展的能力,但无法完全阻止病程发展。近30年来,针对Aβ的治疗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即使斑块显著减少甚至清除,这一极具前景的药物最近在Ⅲ期临床试验中表现出来的临床效益仍旧微弱甚至缺失,表现为难以察觉的认知功能改善。【2】
图1 Aβ清除与微弱或无临床获益
(3)安全性风险:一项为期18个月的多中心、双盲、3期临床试验表明,在18个月时,Aβ单抗组患者认知和功能指标的下降幅度较小,但与不良事件相关,其不良事件包括脑出血/脑水肿、脑萎缩等安全性风险,尤其是在ApoEε4携带者中风险更高。此外,Aβ单抗类药物(如Lacanemab)导致26.4%的参与者出现输液相关反应,12.6%的参与者出现与淀粉样蛋白相关的影像学异常,伴有水肿或积液。【3】
表1 Lacanemab VS安慰剂的不良事件
(4)给药方式的入侵性:大多数临床前和临床研究都指出了针对Aβ的免疫疗法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组织穿透力不足、分布不均、快速清除以及剂量相关的不良反应。面对诸多挑战,目前Aβ单抗类药物的给药方式以静脉注射为主,用药剂量需滴定,且用药期间需进行心电图、血常规、肝肾功能、头部MRI等监测,避免剂量相关不良反应。【4】这使得患者不得不接受定期的住院静脉注射治疗。以仑卡奈单抗为例,该药物需长期使用,每2周进行一次静脉注射,给患者带来了极大不便。
2.脑肠轴机制
(1)脑肠轴机制的复杂性:肠道菌群失调会极大地促进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发病。肠道菌群组成的改变会导致肠道屏障的通透性增加和免疫激活,从而导致全身性炎症,继而可能损害血脑屏障并促进神经炎症、神经损伤,最终导致神经变性。【5】外周Aβ,包括肠道中的Aβ,可能促进大脑中Aβ斑块的形成,从而通过肠-脑轴对AD产生影响。【6】
图2 脑肠轴机制
(2)多靶点干预效果评估:在临床试验中,多靶点干预面临准确评估各环节贡献及整体治疗效果归因分析的难题。肠道微生物群可能通过调节免疫系统来影响CNS的稳态,更直接地,调节影响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分子和代谢物的产生,使其成为潜在的治疗靶标。【7】
图3 肠道潜在靶点的探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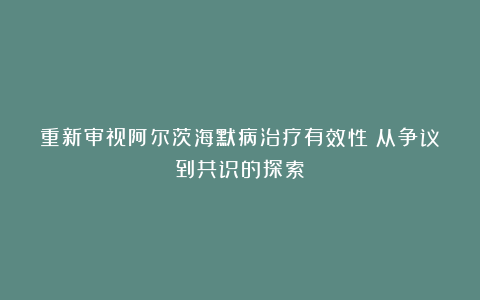
Aβ单抗与脑肠轴机制的研究仍在不断推进,学术界与临床实践正在逐步探索多维度、综合性的治疗策略,并形成共识方向,这不仅为未来AD治疗的研究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也为AD治疗有效性的界定提供更清晰的路径。
疗效评价标准:从单一生物标志物到多维综合评估
单一的生物学指标(如Aβ清除率)已无法满足AD“有效”的定义需求。当前学界认为,疗效评估需融合生理指标、功能维持与生活质量。一项为期36周的Ⅲ期临床试验表明,GV-971在改善认知能力方面效果显著。【8】
表2 GV-971临床有效性结果分析
图4 ADAS-Cog12评分曲线
FDA等机构明确提出,临床试验需纳入患者报告结局(PROs),认知功能改善需与日常能力维持并重。GV-971上市后,一项涵盖3300例患者为期2年的大规模临床研究显示,总体有效率为60%,初治(首次用药且未联合其他传统AD药物)患者有31%呈逆转趋势,经治患者的疾病进展延缓率为71%。这些研究结果印证GV-971具备“缓解症状+改变病程”的双重潜力。【9】
治疗策略:多靶点协同的必要性
AD是一个发病机制非常复杂的疾病,Kai-Hei Tse等学者曾以盲人摸象来形容对AD病理机制的了解局限性,除传统关注的Aβ斑块、tau蛋白过度磷酸化等主流学说之外,还有众多病理生理过程参与AD的发病。Bengisu Turgutalp和Caghan Kizil等专家认为,“由于AD的复杂性、多因素性,需要同时靶向各种疾病机制才能取得临床成功”。而GV-971与近期AD新药研发开始更加重视多途径、多靶点的系统性干预不谋而合。作为靶向脑肠轴的AD治疗药物,它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降低外周炎症、降低神经炎症、减少Aβ聚集,多环节发挥治疗AD的作用,被《柳叶刀》归类为靶向神经炎症的疾病修饰治疗手段。
治疗可及性:中国方案的现实落地
“有效”的最终落点需回归患者真实需求。当前共识强调,药物的有效性需兼顾可负担性与可及性:Aβ单抗虽已获批,但疗效仅限于症状改善,且存在安全性风险,并且其年均20万美元的高昂费用(国内未纳入医保)限制了普及;而GV-971通过医保谈判将年自付费用降至约5000元。此外,GV-971作为口服药,无需住院静脉滴注、无需影像监控、无脑水肿风险,其口服便利性、对共病患者的安全性(48周不良反应率19.7%)更贴合患者需求。
AD治疗有效性的科学界定,本质上是一场对“有效”内涵的重新校准——它既非简单等同于生物标志物的短期波动,亦非孤立追求症状的瞬时改善,而是在疾病复杂性中构建多维、动态、可感知的评价体系。
比起单纯的标志物降低,更应关注以“功能维持”为核心的患者临床结局,如通过认知量表(如MMSE)、日常生活能力评估及患者报告综合衡量用药后独立生活、社交参与等关键维度的长久改善。同时需纳入“风险-获益”的动态平衡——既要关注Aβ单抗的脑出血风险,也要考量传统药物的胃肠道反应。此外,需要从用药人群的实际情况(包括共病状态、依从性、经济水平等)出发,评估长期用药对患者整体生活质量的影响。
总之,在AD治疗有效性的争议中,我们既要看到创新药物带来的希望和挑战,也要充分认识到传统药物的特点与价值。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努力和探索,才能在争议中达成科学共识,为AD患者提供更优质、更有效的治疗方案,让他们在与疾病的抗争中拥有更多尊严和希望。
1.Orrego F, Villanueva S: The chemical nature of the main central excitatory transmitter: a critical appraisal based upon release studies and synaptic vesicle localization. Neuroscience. 1993, 56:539-55. 10.1016/0306-4522(93)90355-j
2.Vaz, M., & Silvestre, S. (2020). Alzheimer’s disease: Recent treatment strateg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887, 173554.
3.van Dyck, C. H., Swanson, C. J., Aisen, P., Bateman, R. J., Chen, C., Gee, M., Kanekiyo, M., Li, D., Reyderman, L., Cohen, S., Froelich, L., Katayama, S., Sabbagh, M., Vellas, B., Watson, D., Dhadda, S., Irizarry, M., Kramer, L. D., & Iwatsubo, T. (2023). Lecanemab in Early Alzheimer’s Disease.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88(1), 9–21.
4.王刚,李彬寅,任汝静,肖金雯,陈生弟,陈晓春。《关于抗 Aβ 单克隆抗体的临床应用建议(2024 版)》
5.Kowalski, K., & Mulak, A. (2019). Brain-Gut-Microbiota Axis in Alzheimer’s Disease. Journal of 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 25(1), 48–60.
6.Jin, J., Xu, Z., Zhang, L., Zhang, C., Zhao, X., Mao, Y., Zhang, H., Liang, X., Wu, J., Yang, Y., & Zhang, J. (2023). Gut-derived β-amyloid: Likely a centerpiece of the gut-brain axis contributing to Alzheimer’s pathogenesis. Gut microbes, 15(1), 2167172.
7.Zheng, Y., Bonfili, L., Wei, T., & Eleuteri, A. M. (2023). Understanding the Gut-Brain Axis and Its Therapeutic Implications for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Nutrients, 15(21), 4631.
8.Xiao, S., Chan, P., Wang, T., Hong, Z., Wang, S., Kuang, W., He, J., Pan, X., Zhou, Y., Ji, Y., Wang, L., Cheng, Y., Peng, Y., Ye, Q., Wang, X., Wu, Y., Qu, Q., Chen, S., Li, S., Chen, W., … Zhang, Z. (2021). A 36-week multicenter, randomized,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parallel-group, phase 3 clinical trial of sodium oligomannate for mild-to-moderate Alzheimer’s dementia. Alzheimer’s research & therapy, 13(1), 62.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