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兆君
回溯半生,最痴傻的那段时日,像旧胶片里泛着暖雾的帧。昏黄的光裹着细碎的颗粒,一帧帧都浸着不自知的灼热,哪怕如今再看,都能从记忆的褶皱里,摸出当时烫人的温度。
那是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我在南方小城的书店做店员。玻璃门每天推开又合上,带进巷口的风,也带进了你的身影。你总穿件浅灰色的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手里攥着本翻到卷边的诗集,每次来都径直走向靠窗的位置,一坐就是一下午。阳光斜斜地落在你身上,把书页的影子映在你手腕上,晃得我连整理书架的手都慢了半拍。
记得第一次和你说话,是个雨天。你没带伞,站在书店门口望着雨帘发呆。我攥着把刚买的、还没拆封的伞,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磨蹭了半天才走过去,声音细得像蚊子叫:“这把伞……你先用吧。”你转过头,眼里带着点惊讶,随即笑了,露出两颗浅浅的梨涡:“那怎么好意思?我下次来还你。”就是这声“下次”,让我把那把伞的品牌、颜色,甚至伞柄上的纹路,都记了好多年。
从那以后,我们的交集渐渐多了起来。你会在我整理诗集时,凑过来念一句聂鲁达的“爱情太短,遗忘太长”;会在我值晚班时,买杯热奶茶放在收银台上,说“天凉,暖暖手”;会在周末约我去巷尾的面馆,点两碗阳春面,加双倍的葱花——你记得我不吃香菜,却爱极了葱花。
那时,心里像燃着一蓬松明,光焰跳着,把胸腔烘得发烫。那光太烈,漫过眼底时,连天地万物都裹着层薄如蝉翼的辉煌金边。你也在这光里,轮廓模糊却格外耀眼。我错把这眼底的幻象,当作命运递来的霞光,捧着满心的热,连呼吸都带着甜。我开始攒钱买你喜欢的作家的新书,在扉页上写满没敢说出口的心事;开始学着画简笔画,把你看书、喝咖啡的样子,偷偷画在便签纸上,夹在你常翻的那本诗里;开始盼着每天下雨,盼着你能再借我的伞,盼着我们之间能有更多“下次”。
人说情深不寿,我那时偏要赌这“不寿”是妄言。我把真心熨得平展,像递上张泛着米香的宣纸,满心盼着能被题上“见字如面”的诗行。你说要去北方闯一闯,我连夜织了条围巾,针脚歪歪扭扭,却把所有的牵挂都织了进去;你说喜欢我写的文字,我便每天写一篇短文给你,从春日的花开写到冬日的雪落;你说“等我稳定了,就回来接你”,我便把这句话当作信仰,每天对着日历画圈,算着你回来的日子。你说的每句话,我都当作信徒捧着经卷般信奉;那些裹着暖意的誓言,落在耳里,便成了刻在心上的律令。如今再想,那时的自己,是把天真当铠甲,连脆弱都露得坦荡,可笑又可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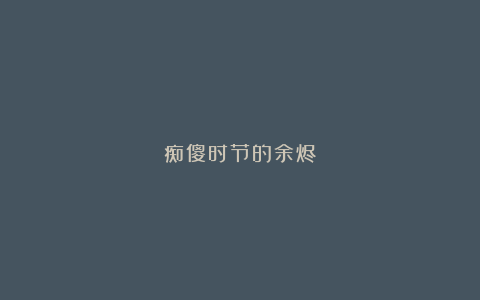
你去北方的第一个月,每天都会给我发消息。说北方的雪下得很大,说出租屋的暖气很足,说想念巷尾面馆的阳春面。我抱着手机,看着那些文字,能傻笑半天,连梦里都是你回来的场景。可第二个月,消息渐渐少了。从每天一条,变成三天一条,再到一周一条。我安慰自己,你只是太忙了,却忍不住对着手机等消息到深夜,手指反复刷新聊天界面,连电量从满格掉到百分之十都没察觉。
后来的日子,像浸在冰水里的凌迟,无声却刺骨。那层金边终于被生活磨褪,露出的是粗粝的、带着毛刺的底色。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是个周末的晚上。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你那边很吵,有音乐声和笑声。我问你在忙吗,你说“和朋友聚会呢,没什么事就先挂了”,语气里满是不耐烦。我还没来得及说“我想你了”,电话就被挂断了,听筒里只剩下“嘟嘟”的忙音,像针一样扎在心上。
从那以后,你的话从裹着暖意的絮语,渐渐凝成扎人的冷钉;你的神情从春日的软风,换成了冬日的寒霜。我生日那天,特意买了个小蛋糕,对着蜡烛许愿,希望能收到你的祝福。可直到凌晨,手机都没动静。我忍不住给你发消息,问你是不是忘了我的生日,你隔了很久才回复:“最近太忙,忘了。”没有道歉,没有解释,只有冷冰冰的五个字。我的那张真心,你接过去时连眼都没抬,随手揉成一团扔在角落——一次又一次。它软得像被揉过的棉纸,沾了尘埃,再也展不开当初的平整。
有一次,我在你朋友圈看到一张照片。你和一个女孩站在雪地里,笑得灿烂,女孩脖子上围着的围巾,和我当初织给你的那条,一模一样。我手抖着给你发消息,问那是谁,你很久才回复:“一个朋友,围巾是她自己买的,别多想。”可我怎么能不多想?那条围巾的针脚,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那天晚上,我抱着那条没送出去的、和你朋友圈里一样的围巾,哭了一整夜。眼泪把围巾浸湿,干了之后,留下一圈圈软塌塌的印子,像我心上的伤疤。
痛是浸骨的。不是骤雨般的锐痛,是梅雨季浸在骨缝里的旧伤,钝重却挥之不去。深夜里这痛会突然拔尖,像针往心口扎,我便在黑暗里狠狠责问自己,当初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要把真心给一个不珍惜的人,仿佛这样的自我鞭笞,能换片刻清醒。可没用,痛只是痛,没让我多一分聪明,反倒让那痛感像浸了墨的针,一针针缝进骨血里——爱过你这一回,这痛大抵要跟着我一辈子了。这是我这辈子,最错、也最悔的一桩事。
我总忍不住痴想:倘若从未开始多好。倘若那天没有把伞递给你,倘若没有在你念诗时心动,倘若没有把你的誓言当作信仰,是不是就不会有后来的痛?
你还是人群里那个遥远的、带着薄雾的影子,不会有机会把淬了冷的刀,一寸寸扎进我心里。我的世界还是完整的,没这道渗着血的、愈合不了的裂痕。我还会在书店里,安安静静地整理书架,迎着巷口的风,看着阳光落在书页上,过着平淡却安稳的日子。你也没法用虚妄的承诺,骗走我攥得发紧的信任、烫在眼眶的眼泪,还有那些为你起落的欢欣与悲戚。我为你哭了多少回,连枕头都记不清,而你始终站在光里,冷得像深山里的寒石,自私得坦然。
去年冬天,我回了趟那个南方小城。书店还在,巷尾的面馆也还在。我走进面馆,点了碗阳春面,加了双倍的葱花。老板问我:“好久没来了,要不要等你朋友一起?”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老板还记得当初总跟我一起来的你。我摇摇头,说“就我一个”,然后低头吃面,眼泪掉进碗里,混着汤的热气,模糊了视线。
我甚至想,哪怕只有一次,你能看见我藏在笑里的挣扎、落在暗处的遍体鳞伤,对我生出半分带温度的怜惜——那么我今日,也不会是这般连呼吸都带着碎感的模样。哪怕你在说“忘了”我的生日时,能加一句“抱歉”;哪怕你在挂断我电话时,能多问一句“你有没有事”;哪怕你在朋友圈发那张照片时,能顾及一下我的感受。可没有,一次都没有。
那蓬松明早烧尽了,只剩满地凉透的灰。风一掠,连这点灰都卷得没影,仿佛我们之间那点炽热,从来只是我一个人的幻觉。如今再想起那段痴傻的日子,心里已经没有当初的痛了,只剩一种空落落的麻木。就像冬天的湖面,结了层厚厚的冰,底下的波澜,再也掀不起任何涟漪。只是偶尔在整理旧物时,看到那把没还回来的伞、那些画满你的便签纸、那条软塌塌的围巾,还是会愣神很久。原来有些记忆,哪怕烧成了灰,也会在心里留下痕迹,一辈子都抹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