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祭(西)王母于石室”
陈颖
(中国国家博物馆)
对西汉祭祀西王母场所的记载,见卫宏《汉旧仪》:“祭(西)王母于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长奉祠。” 这句话有两种解读的可能性。
第一种解读可能,是祭祀西王母的石室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这一推测基于书中的这一整卷对祭祀场所的记载都是明确地点,如“祭天于云阳宫甘泉坛”“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 等,以此推之,“西王母石室”可能也是个具体地点。
第二种解读可能,是在各地的石室里,由所在地的二千石、令、长祭祀西王母 。这一推测基于“在所”一词仅指称所在地,并不特指,如《史记·平准书》:“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便属在所县。”具有含糊性。此外,“皆”字或也能辅证祭祀西王母的石室不止一处。
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汉旧仪》中“祭(西)王母于石室”这一表述的真正含义,我们需要结合更多史料,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时间与空间——“西王母石室”由地名向建筑的演变
已有研究中,王兴芬对“西王母石室”的考证提供了见解。她根据汉魏六朝的文献,对西部地区“西王母石室”的来源进行了考证,兹摘录其结论如下:
一方面是甘肃河西走廊、青海以及西南川滇一带古羌戎族多以石头堆砌而成的民居特点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来自汉末魏晋动乱时期西北边塞军民用土石堆砌的坞壁亭障,是民间传说对特定历史时期广大民众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
在论文中,她也指出了这一结论的依据:
西王母居于石室的记载主要集中在西汉魏晋时期古丝绸之路的甘肃、青海一带以及西南的四川、云南等地区。
这一推论过程将研究焦点集中在“西王母居于石室”这一问题上。这一结论虽为理解西王母石室的性质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但居住场所和祭祀场所不一定是同一个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西王母石室位置和规模的记载也在发生变化。
“西王母石室”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出现在文献中,是今青海湟源的一个地名。见《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 在这句话中,西王母石室与仙海、盐池两个地名并列,说明在汉代,“西王母石室”首先是一处地名。汉平帝元始四年(4),西王母石室被卑禾首领良愿献给汉室,此事见《论衡》:
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贤,辅以周公,越常献一,平帝得三。后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桥桥种良愿等,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
这段话中,“西王母石室”作为金城郡塞外的地名出现,即《汉书·地理志》中提到的“西北至塞外”的西王母石室。在元始四年,西王母石室这块地域被纳入汉代版图,成为西海郡。
魏晋时期,对“西王母石室”的记录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被视为地名,而被描述为山中的堂室建筑,见《十六国春秋》:
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山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在此山,山中有石室、玉室(一作“王母堂”),珠玑镂室,焕若神宫。《禹贡》:昆仑在临羌(一作’江’)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禆朝廷无疆之福。
《十六国春秋》是北魏崔鸿撰写的、关于西晋末年至北魏统一北方之前(304—439)十六国政权兴衰的纪传体史书。酒泉南山为昆仑山支脉。前凉酒泉太守马岌将西王母石室的情况报告给了当时的统治者张骏,张骏下令在酒泉南山建造了西王母祠。书中的这一记载将西王母石室和穆王见西王母的传说联系在了一起。“石室”“王母堂”可以看成是“西王母石室”的别称,它位于山中,“珠玑镂室,焕若神宫”是对华美、庄严的石室建筑的形容。
又见《列仙传》:
赤松子者,神农时雨师也。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上下。
《列仙传》是一部系统叙述神仙系统的传记。在《赤松子》一篇中,将“西王母石室”与昆仑山、赤松子联系到了一起,提到赤松子常到昆仑山上的“西王母石室”中,这句话中的西王母石室是昆仑山上的一处“石室”,“中”字意味着这是一个空间大小有限的“石室”。
隋唐以后,有“西王母石窟”,见《隋书》:
西海郡。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浑国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盐池。
《后汉书》李贤注中提到了“王母台”:
昆仑山名,因以为塞,在今肃州酒泉县西南。山有昆仑之体,故名之。周穆王见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台。
西海郡在今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在这一记载中,“西王母石室”变成了“西王母石窟”。而在李贤的注中,指出昆仑山上有“石室,王母台”,是为“西王母石室”的演变。
综上所述,西王母石室最初起源自今青海湟源的一处不明确的地名,在魏晋以后,从地名演变成了堂室、石窟、楼台形式的建筑。这也意味着,在魏晋以后,专门祭祀西王母的祠堂或许才开始建立。就目前所见,“西王母石室”的所在,在汉代更像是一个虚指,它只在一个大致的位置,没有具体的所在地。对作为地名的“西王母”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如王煜所说,西王母“由早期的不确定或较近的西方向更远的西域国家逐渐西移……它随着人们对西域认识的逐渐扩展而不断西移,总在当时认识的最西国家之西。”虽然目前学界有一些猜测,如西王母石室位于“在祁连山脉之大通山南麓、青海湖西北天峻县境内的二郎洞与青海湖东南的湟源县宗家沟石洞”,但这一推论缺乏更多有力证据。在这一背景下,汉代对作为神灵的西王母的祭祀情况,仍需要进一步讨论。
二、不同建筑制式的石室
“祭西王母于石室”一句中的“石室”,是否等同于史料中记载的“西王母石室”?“皆在所二千石令长奉祠”一句中的“在所”是指西王母石室,还是全国各地的石室,仍需考虑“石室”一词在当时的使用。石室在文献中有多种含义,如古代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函;藏图书档案的地方等。作为建筑制式存在的石室,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石窟、洞穴;另一类是墓室、祠堂。
(一)作为石窟、岩洞含义的石室
作为“岩洞、石窟”含义的石室,多以此来比喻坚固的洞穴,衍生出“坚固的防守设施”之义,如:
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春秋繁露》)
上天之诛也,虽在旷虚幽间,辽远隐匿,重袭石室,界障险阻,无所逃之亦明矣。(《淮南子》)
吴王知范蠡不可得为臣,谓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复置子于石室之中。”(《吴越春秋》)
近刘氏据三关之险,守重山之固,可谓金城石室,万世之业,任授失贤,一朝丧没,君臣系颈,共为羁仆。(《三国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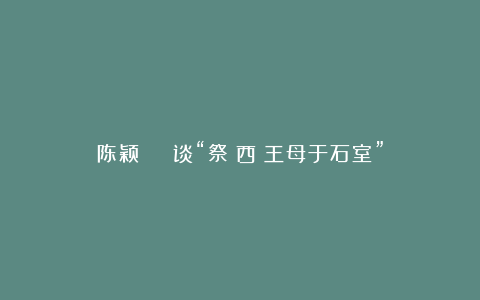
《春秋繁露》中提到的“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以及《淮南子》中提到的“上天之诛也……重袭石室”,指的是一处牢固的防御性空间,寓意即便躲藏在这样坚固的场所,仍无法逃脱天命或灾难的降临。而后两个文献中吴王话里的“石室”以及三国时期蜀国刘氏的“金城石室”,为石窟、洞穴的引申含义,象征着极度稳固、难以攻破的场所,用于比喻防御工事的牢不可破,但这些文献中所说的“石室”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虚指,并不指具体的某一处石室。
石室与石窟之间存在差别。石室更接近于天然形成的洞穴;石窟是佛教徒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通常是山崖上开凿出的洞穴,也称石窟寺。目前普遍认为最早的石窟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的三仙洞,凿于峭壁之上,洞内残有一些壁画遗迹和造像遗迹。关于三仙洞开凿年代的各种说法中,时间最早的是在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 。即便如此,这个时间也晚于“祭西王母于石室”这句话所在的西汉时期。这意味着“祭西王母于石室”中的“石室”很可能不是佛教石窟的形制,而是指西汉时期存在的天然洞穴。
因此,在西部地区可能存在用于祭祀西王母的石室,但其具体位置尚未确定。更为客观的表述是:西域的石室可能是祭祀西王母的地点之一。
(二)作为墓室、祠堂的人造石室
石室一词的另一种用法,是用来指代墓室、祠堂。西汉末年的东部地区,有许多祠堂被称为“石室”。《宋书》中提到:“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 武利华在《徐州汉碑刻石通论》中指出,“祠堂是陵园中祭奠死者的地方,汉代陵园祠堂有多种称谓,如庙祠、食堂、斋祠、食斋祠、石室等。”“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祠堂题记皆称祠堂为’石室’,山东画像习惯将祠堂称为’食堂’。” 王子今认为,“石室”是“汉代祠堂的文物实证”,“有关“石室”作为“神仙”居所和“学仙”场地的故事,暗示汉代冢墓的“石室”遗存,有可能与当时人们的神仙崇拜与升仙追求有关。”
学界对“石室墓”所指的建筑制式存在争议。周保平引用地区发现的“东汉元和三年画像石题记”中的“石室”二字,将其解释为墓葬的附属建筑,而墓室则称之为“冢” 。杨爱国认为,汉代人也将墓室称为“室” 。尽管这些说法存在分歧,但它们都有助理解“石室”这一概念,表明“石室”通常是与墓葬和祭祀相关,并以石材堆砌而成的纪念性建筑,而不同于石窟或洞穴的样子。
作为墓室的石室的建造过程,可见《后汉书》李贤注引晋书《地道记》:
县多山,所治名金山。山北有凿石为冢,深十余丈,隧长三十丈,傍却入为堂三方,云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凿而得金,故曰金山。故冢今在。或云汉昌邑所作,或云秦时。
《地道记》中的“县”指金乡县,始置于东汉,属山阳郡,隶属于今山东省济宁市。金山属今泰沂山脉,其中“凿石为冢”,指依山凿石而建的墓冢。这一记载也提到了墓室“深十余丈”,隧道“长三十丈”,为堂三方,指“内外堂为一,并左右两室计之” ,可见墓室的规模。
作为祠堂的石室,史料中也有记载:
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墓前有庙,庙前有碑。永嘉四年,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大其功德,遂建石室,立碑树桓。(《水经注》)
《水经注》中提到,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汉阳太守殷济为司马迁建了石室,作为祠堂。这表明石室不仅被作为墓葬、家族祭祀的建筑,也用于纪念和祭祀重要人物。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对西王母的祭祀,是否也可能在类似的石室祠堂中完成?虽然现存文献对祭祀西王母的具体场所多含混不清,但石室祠堂的祭祀用途,为推测石室祠堂成为西王母的祭祀场所提供了可能性。
综上所述,“石室”在不同文献中有展现了多样化的含义,因此需要进一步考量其在具体祭祀语境中的实际指代。特别是对西王母的祭祀,是否仅限于某个固定的石室,还是扩展到全国各地的“石室”?“西王母石室”在记载中更像是石窟、洞穴等天然形成的石室,与山东地区广泛存在的人造石室并不相同。这表明,石室并非一个专指的称谓。基于此,除了西部的石窟,对西王母的祭祀是否也有可能在石祠堂里,由当地的行政长官完成?
三、“室”内的西王母祭祀——在汉画像石中的刻画
“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 在《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中,均记载了祭祀鬼神的演变。“秦人祀所包括’神祠’与’先祠’。汉并天下,继承了秦的信仰体系。” 虽然在两汉时期,原始宗教的力量减弱,但祠庙的数量依然众多。对西汉末年的宗教改革的记载中,统计了祠庙的数量。成帝时期,匡衡、张谭的奏文中提到,“长安厨官县官给祠郡国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又有:“哀帝即位,寝疾,博征方术士,京师诸县皆有侍祠使者,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 到了王莽时期,“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 无论是成帝时期的683所,或是哀帝时期的700余所,一年3.7万次祭祀,或是王莽时期的1700所,这些数字都反映了祠庙数量的庞大。
在汉代,同一个神祇可以拥有多个祠庙。以杜主信仰为例,根据《封禅书》,杜主祭祀的是“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鬼神者。”“(杜)、亳有三社主之祠……而雍菅庙亦有杜主。” “杜”原作“社”,据《汉书·郊祀志》改。在汉初由“秦巫祠杜主” ,在西汉末年宗教改革中,杜主的祠庙几经变更,成帝时期“杜主有五祠,置其一” ,在王莽时期,“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 。无论具体数量为何,作为关中地区普遍的信仰,杜主拥有多座祠庙,皆被官方认可并祭祀。
西王母是汉代遍布全国的信仰。关于西王母信仰的器物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铜镜等,在全国各地都大量出土。传世史料中,也有西王母信仰在全国传播的记载。在《汉书》中的《哀帝纪》《五行志》及《天文志》 中,皆记载了“行西王母诏筹”一事。事件始于哀帝建平四年(前3)正月,大旱。关东的民众惊惶奔走,手上互相传递一枚稾或棷,称之为“行诏筹”,又称“西王母筹”。他们向西一路经过二十六郡国(有说称三十六),去往京师长安,在路上他们喧哗、奔走、传筹祠西王母。因此,在有西王母信仰的地区,为西王母立祠祭祀,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西王母画像的主题大多关于对西王母的祭祀、朝拜。虽然全国各地出土的画像石中均有西王母的图像刻画,但不同地区的图像构图和周围场景各不相同。 对祭祀西王母的石室的样子,学界有过一些猜想。有一类猜想是基于对当地建筑形制特点的考虑。如王兴芬认为,“有关西王母石室的大量记载,也是道教徒受佛教文化中与石相关的民间传说、大量佛教石窟以及石室等的影响,模仿佛教石窟、石室对西王母’穴居’居所改造的结果。” 这是基于西域建筑特点,对西王母石室的假设,但对于其他地区的西王母石室,也可能存在不同的建筑形制。
另一类猜想是对“西王母石室”象征意义上的考虑。如小南一郎认为: “在四川画像砖中所见西王母坐在两侧支起的华盖之下,可能表示她在石室里。还有人指出这种石室作壶形。” 如高文引四川新繁县出土的一块画像砖(图1),认为“此砖上面正中刻一瓶形之龛,龛上有盖,龛的左右有云气围绕。此系象征传说中的西王母的石室” 。持这一说法的还有周静 。
图1 新繁县出土的西王母画像砖
“祭西王母于石室”这句话中的“祭”,指的是具体的祭祀行为。由“二千石、令、长奉祠”的祭祀,至少应在一个具体的场所举行。对于这样的场所,本文在汉代的画像石中找到了能描述这一祭祀场景的画像,以此对可能用于祭祀西王母的石室做进行进一步的推论。
在判定画像中是否描绘西王母时,鲁惟一(Michael Loewe)提出汉代西王母身边常见的十个特征元素,包括捣药之玉兔、神龟、三足乌、执兵器之侍卫、祈福者、九尾狐等等 。在大部分西王母主题的画像整体构图中,西王母的画像几乎都处在建筑以外的户外空间中,如象征昆仑山的山形座、龙虎座、神树的顶上等 。而室内所刻画的女性人物往往被认为是女墓主,从而与西王母的形象区分开来。
在一些画像石中,西王母的形象被刻画在了室内。这样的图像相对较为少见,例如西汉末年到王莽时期的江苏沛县栖山一号石椁墓中的西王母形象(见图2)。
图2 江苏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中棺东壁摹本、拓本
该墓的考古简报认为“此组图像应为诸神朝拜西王母之图像” ,信立祥认为,“在迄今发现的大量汉代西王母图像中,坐在仙阁上的西王母图像这是仅见的一幅” 。
在画像中的形象是西王母还是女墓主的问题上,学界有过讨论。刘辉认为这是女墓主升入仙界中的生活描述。理由有二,一是就东汉画像石墓习俗而言,多数刻画的主要人物为男、女墓主,而此棺椁的画像中缺少女墓主形象;二是西王母为神仙,而该人物面前的几上所摆鼎和盘,似与神仙的生活不符。 石红艳、牛天伟对此作出回应,认为在夫妻合葬墓中,男女墓主形象一般刻画在共有的墓门和主室顶板上,而非在棺椁上。又举四川新都新龙乡出土画像砖中西王母前也有三足盘与樽为例反驳。 本文则认为,考虑到该女性形象位于楼阁之中,并且楼阁右侧有衔食的青鸟、九尾狐以及四位前来拜见的神灵等细节,这更符合西王母的图像特征。因此,可以推测该女性形象为西王母。
在解读这幅画像时,王建中认为这是“神庙图”,并指出“此楼阁非一般第宅、厅堂建筑,当为祭祀帝女西王母之神庙” 。蒋英炬、杨爱国基于“仙人好楼居”的推断,认为该图描绘了天国仙人形象 。本文认为,在汉代,西王母的图像被描绘在室内,尤其是在具有宗教或祭祀性质的建筑中,体现了对西王母的崇拜和祭祀。因此,这种“室内”西王母图像很可能描绘的是祭祀西王母的“石室”。
图2中, 西王母所处的建筑为二层结构,建筑的左侧有一排踏道,与汉代的祠堂相似。在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出土的画像石中,也有一副描绘祠堂的画像(图3)。画面中的祠堂同样为两层阁楼,一侧配有踏道。院落内除中间的建筑以外,没有其它房屋,这表明该建筑很可能是祠堂。刘尊志指出,祠堂的室外场地“主要是配合祠堂开展规模大、人员多的祭祀典礼活动,亦或作他用。” 而图2中的祠堂右侧的画面里,也有一片空地,用于开展祭祀。空地的前排有并排跪坐的两人,后方则站着前来祭祀的人和神灵,这显示了画面上正在进行祭祀活动。
图2的画面中,阁楼后方有两棵松柏。松柏通常栽种于墓地、祠堂。《汉书·龚胜传》中记载,龚胜在嘱咐自己后事的时候曾提到,“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颜师古注:“若葬多设器备,则恐被掘,故云动吾冢也。亦不得种柏及作祠堂,皆不随俗。” 这表明,在汉代民俗中,栽种松柏、建造祠堂是常见习俗。因此可以确定,图2画面上描绘的是西王母在石室祠堂中接受祭拜的场景。
“室内”的西王母主题,在出土画像石中并不多见。除了江苏沛县栖山汉画像石墓外,陕西米脂县党家沟墓门面五石组合也有类似的主题(见图4)。
图3 米脂县出土的祠堂画像石
图4 陕西米脂县党家沟墓门
二层阁楼中的两位仙人背生翅膀,明确显示了他们的神仙身份。而阁楼外的蟾蜍、九尾狐、青鸟、捣药的玉兔等典型的西王母随侍,进一步支持了这两位仙人分别是西王母和东王公的结论。这一祠堂中的祭祀场景在整个图像的正中央,表明了西王母和东王公在当时的祭祀活动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一主题的图像的构成,以“石室”为载体,完成了对神灵的祭祀仪式。
作为一种纪念性建筑,以祠堂形式呈现的“石室”不仅仅用于祭祀神仙,还是沟通神灵与人类的场所。因此,“室内”的西王母主题图像体现了石室中祭祀西王母的场景,这一发现强化了“石室”作为祭祀仪式场所的神圣意义。
结语
本文从传世文献中“西王母石室”与“石室”的记载出发,辅以汉画像石中对西王母的刻画,对《汉旧仪》中“祭(西)王母于石室”一句尝试进一步讨论。关于“西王母石室”的记载,由汉代塞外一处模糊地名,到魏晋时期转变为堂室建筑;而作为建筑制式的“石室”,则有着洞穴和祠堂两个截然不同的载体。本文认为,最先存在特定地址的西王母石室,但是随着西王母信仰的全国传播,对西王母的祭祀有可能是在不同地区的石室里完成。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4年冬之卷(总第32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编辑: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