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林》2025年第2期,注释从略
作者:陈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全球化时代的知识旅行
——以马戛尔尼使团测算的清代疆域面积为例
陈 兴
摘 要
古代国家习惯使用纵横里程表示疆域范围,很少采用具体的面积数据。启蒙运动时期,随着欧洲科学技术发展、行政能力改进,测算区域面积逐渐成为习惯做法。同时,由来华耶稣会士绘制的《皇舆全览图》在欧洲流传。马戛尔尼使团在访华期间,利用该图计算出中国长城以内各省的面积。此后一百多年里,这组面积数据在欧美世界广泛传播,并不断得到修正。鸦片战争以后,很多中国和日本学者也采用它们,并进行本土化的单位换算。民国时期,甚至有零星换算后的数据被编入《清史稿·地理志》。上述曲折辗转的流传过程,是近代西方建立世界殖民体系,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竞争、构建民族国家的缩影,也生动展现了这一全球化时代跨国知识交流的面貌。
关键词
疆域面积;《皇舆全览图》;马戛尔尼使团;全球化;知识流动
构成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包括领土、人民、政府、主权等。其中,“人民”和“领土”适合做量化考察。关于中国古代“土地面积”的统计,特别是针对史料丰富的明清以降的土地面积,前辈学者已有丰富的研究。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里的“土地”都是指“耕地”,而非“领土”。古代文献本身就缺乏表示“领土面积”的数据,从事相关研究自然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步入近代,随着大量各级行政区面积数据的涌现,进行相关研究便成为可能。当然,这些数据的质量良莠不齐,今人完全可以利用现代绘制的高精度地图,不必参考前人的数据。
本文无意于追求有关领土面积的“真理”,而是关注这些尚未达到“真理”层次的“一般性知识”从创造到传播的历程。以往的地理学史研究,勾勒了宏观的“西学东渐”和“近代知识转型”的线索,没有对具体面积数据作专门讨论。本文将聚焦近代流传甚广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测算的清代内陆各省疆域面积,捋清这些数据产生、流变、传播的历程,呈现走向“全球化”过程中知识交流的生动面貌。
一 19世纪之前疆域范围的数学表达
现代人在描述某一事物的面积时,通常使用“平方+长度单位”作为计量单位。古人则使用边长来反映面积,王引之总结说:“古人言地之广狭,皆云方几里,或云广纵几里。”
先秦秦汉时期,在“天圆地方”观念支配下,人们倾向于以“方若干里”描述区域面积,通过简单的边长相乘,就能算出正方形面积。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区域形状并不呈正方形,所以需要作“取长补短”的预先处理。比如《礼记·王制》计算理想化的周天子统治范围:“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
秦汉以后,当作为政治统一体的“天下型中国”成为既成事实,“方万里”成为对中国疆域的程式化描述。在泛称的“万里”之上,出现更精细的数字和表述方式,代表是《汉书·地理志》:“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除了东西、南北两个方向的纵横跨度,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提封田”,这是《汉志》给出的西汉郡国疆域总面积,按照汉代尺度约合今600多万平方公里,而实际数字约为400万平方公里。遗憾的是,后世许多王朝正史的《地理志》虽然列有疆域的纵横跨度,但是都缺乏类似“提封”的疆域面积。
古代西方学者也采用边长表示区域范围。例如,希罗多德(Herodotus)计算斯奇提亚(Scythia)的面积:这片土地是“四面相等的一个正方形”,边长是4 000斯塔迪昂(约合740公里)。进入中世纪,由于古典传统的中断,欧洲人关于中国地理的知识陷入长期停顿。此刻,阿拉伯人扮演着东西文化交流者、古典传统继承者的角色。他们同样主要采用纵横里程呈现地理范围。马苏第(Al Masūdi)《黄金草原》记载世界各国领土,均为“长若干里,宽若干里”的表述方式,但是数值可信度参差不齐,关于中国的数据为“长3.1万、宽1.1万古里”,明显偏大。
13世纪的蒙古西征,15—16世纪的新航路开辟,在陆地、海洋两条道路上拉近了欧亚大陆的两端,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相互认知程度随之提高。基于探索新世界的热情,通过对古希腊罗马传统的“再发现”,对阿拉伯人地理学知识的学习,以及数学、天文学等基础科学的进步,欧洲人逐渐建立起近代的地理科学体系。
明清之际,漂洋而来的外国传教士,在传统的纵横里程之外,创新性地添加了经纬跨度。后者既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地理学发展的重要表现,也是人们更加精准地测算疆域面积的凭据。只在福建活动过的西班牙人拉达(Martín de Rada)根据经验推测:“大明国必定有差不多一千里格长,四百里格宽,四周将近两千五百里格”,并希望后人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中国疆域的“实际情况”。而后,利玛窦(Matteo Ricci)通过实地测算,取得一些重要地点的经纬坐标,但是受限于足迹,数据不够完整。
进入18世纪,白晋(Joachim Bouvet)、雷孝思(Jean Baptiste R gis)等耶稣会传教士奉康熙帝旨意,花费十年时间,系统测定中国内陆的地理坐标,绘制完成《皇舆全览图》。法国学者唐维尔(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以此为底本,制成当时欧洲最精确的中国地图,于1735年伴随杜赫德主编的巨著《中华帝国全志》一同问世。遗憾的是,由于康熙朝以后中西交流受阻,日后完成对广大边疆地区测绘的《乾隆十三排图》未能及时传播到欧洲,这使得西方学者对长城之外广大地区的认知长期停留在清初水平。
在描述中国疆域广阔程度这件事上,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依旧沿袭着传统范式,只有搭配经纬度的纵横里程,而没有依照精细地图,计算“精确”的面积数字。这并非他的保守,而是当时欧洲世界的普遍做法。直到18世纪后期,狄德罗(Denis Diderot)主编的《百科全书》在介绍各国疆域时,也基本只采用纵横里程,部分会补充或者代之以经纬度。比如,法国南北长230法里,东西宽220法里,缺经纬度;英格兰在东经12—19度、北纬50—56度之间,缺里程;德国长240法里、宽200法里,在东经23—37度和北纬46—55度之间,两者俱全。
不过,在启蒙运动的浪潮中,欧洲的地理学正在悄然变化。在法国,随着民族国家意识的高涨、国家治理能力的扩张,区域面积、人口规模、交通里程等地理数据成为必需品。于是,在伏尔泰(Voltaire)的笔下,虽然主要还是纵横里程,但面积数据已经偶尔出现:查理大帝统治着“一个一百二十万平方古里的基督教国度”。“平方法里”(lieues quarrées)一词也零星出现在《百科全书》里,尽管频率相当低,而且存在低级失误。如“法国”词条称:假定法国的边长取平均值220法里,那么它的面积就是400平方法里。
而在英文世界里,“平方英里”(square mile)出现的频率和精度也在提高。1776年,历史学家吉本(Edward Gibbon)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出版,他在开篇指出:“一位现代史学家的气质和知识却要求他必须使用一种更为清醒和准确的语言”,“为了更准确地说明罗马的伟大”,他会说罗马帝国“面积估计不少于160万平方英里”。10年后,正在北美抗击英军的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也使用面积数字对疆域范围进行“准确描述”,并与英国敌人相比较:“(弗吉尼亚州)面积为121 525平方英里……这个州比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群岛大三分之一,后者面积为88 357平方英里。”
以上所述都是西方区域。迟至法国大革命前夕,欧洲人仍旧对东亚世界的面积缺乏认识。法国传教士格鲁贤(JeanBaptiste Grosier )1785年出版的《中国通志》,依旧使用传统的表述方式:由皇帝统治的整个国家,从海南岛到鞑靼北端,南北跨900多法里,从东海到准噶尔,东西跨1 200多法里。海峡对岸的英国情况类似。早期《大英百科全书》的“中国”词条,仍然只有经纬度和几组不尽相同的纵横里程。
就技术条件而言,19世纪末的欧洲人已经具备测算中国疆域面积的“能力”,但是要促成这一工作的开展,还需要一定的“必要性”加以推动——在试图将中国纳入欧洲主导的全球体系内之前,这种需求还不够旺盛。
二 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内陆面积的测算
到18世纪后期,对于一些常见西方区域的面积,欧美知识界已经具备初步认知。而伴随欧洲的殖民扩张,获取东方地域的面积数据的必要性也逐渐增加。正如《权力的地理学》所言:“权力的战略使它对这些资料能够加以利用。……17世纪的旅行家和19世纪的地理学家都是情报收集者,收集信息和绘制地图,然后直接为殖民权力、战略家、商人和工业家利用。”
谈到18世纪末英国人对中国的考察,自然要讨论马戛尔尼使团。此前,欧洲人有关中国的知识渠道,主要由法国控制。曾任港督的戴维斯(John Francis Davis)曾说:马戛尔尼访华“使英国人对那个庞大而奇特的国家的语言、文学、制度及风俗逐渐展开了研究。迄今为止,这个领域几乎完全被法国人独占”。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绝非单纯的外交活动,明显带有考察中国国情、搜罗各类情报的意图,整个使团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东方考察团。
最早用现代计量方式表示中国内陆各省面积,正是产生于马戛尔尼使华期间。测量中国疆域面积数字,并非马戛尔尼等人的首要目标,而是服务于他们的人口考察目的。尽管使团成员相信东方帝国拥有稠密的人口,但是传教士刊布的各种信息却相差悬殊。马戛尔尼说,在人口问题上,“外国人因不全懂语言,因误会或误解,因缺乏官方的门路,或因小道消息不足或不正确,往往容易陷入盲目和错误的争论,有时以假为真,有时又以真为假”。为了获得更准确的数据,马戛尔尼向接待使团的天津道台乔人杰求助。乔人杰依据清代官方的赋税账册,提供了中国内陆各省的人口、税收数据。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赋税账册上的人口数字常常是虚应故事,而非真实统计。使团成员对此也有疑虑,他们虽然相信乔人杰不会虚构账册,但是无法断言账册的内容是否属实。因此,马戛尔尼称之为“一个据说千真万确的数字”。可能是为了给人口数据提供参照,使团成员才会测算疆域面积。马戛尔尼和巴罗都表示:他们的测算依据是康熙皇帝命令耶稣会传教士编绘的中国地图,即《皇舆全览图》。巴罗(John Barrow)宣称,虽然使团成员计算出的数字未必精确,但是他们依据的地图足够准确:各省面积数字“采自由耶稣会士花10年时间辛苦绘制,而且据我们有机会把它们和地方上相比较,认为是十分准确的地图”。
马戛尔尼认为中国的疆域总面积相当辽阔,可能与俄罗斯差不多,约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十二分之一。折合成具体数字接近1 300万平方公里。不过,由于乔人杰只提供内陆省份的人口,而且康熙朝《皇舆全览图》实测范围未及全国,所以使团成员“只能”亦“只需”计算内陆各省。马戛尔尼说:“至于中国鞑靼地区的人口,得不到任何消息。……在推测和真实之间有很大差异。”最终,取材于中国官员提供的人口账册,以及法国传教士绘制的地图,英国外交官制成了一组记载中国内陆各省人口、面积数据的表格。
以上数据的真实性如何呢?首先,人口统计表疑点颇多,与现存的乾隆朝户口账册以及相关人口史研究成果对照,总数3.33亿的误差倒不算太大,分省数据则颇为悬殊。使团访华之前数年的《户部汇题各省民数谷数清册》显示,内陆十八省的总人口数维持在3亿左右,但直隶只有2 300余万人,四川更只有900多万人,江苏与安徽合计则超过6 000万人。根据研究,乾隆后期的江苏省人口确实超过3 000万,相当于表中苏皖两省的总和,四川省则只有1 000万左右,只及表中所示的1/3强。因此,这份人口数据的可信度相当有限。至于这些错误是如何造成的——是乔人杰提供的账册有误,还是使团成员转抄时出错,抑或是乔人杰编造假的户籍资料,甚至使团成员杜撰故事而自行虚构数据,由于这与本文主题相去较远,所以暂且不论。
那么,土地面积的数据质量又如何呢?可以发现,上述数据同样存在不少缺陷。最直观的是,由于地图和户口账册的限制,使团成员并未测算边疆地区的面积,无法获悉整个“中华帝国”总面积的精细数字——虽然他们粗略地了解,中国全境约占全球陆地总面积的1/12。其次,在刻画内陆行省时,根据康熙朝地图分为15省,其中的陕甘、湖广、江南三大省已经不太符合19世纪的现实,更细微的区划调整也没有被考虑到。戴维斯在鸦片战争前夕谈到中国地理,首先就说:“从耶稣会士们的测绘时代到现在,中国的行政区划已经发生了变化。”至于计算误差更是明显。韩昭庆等人利用ArcGIS技术对《中华帝国全志》所附长城以南各省地图的面积进行了细致计算,这为本文的检验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
从表2可以看出,面积数据存在不小的误差:有9个省区的误差率超过5%,特别是贵州被夸大近1/4,山西被压缩近1/6。河南、山东两省面积实际相差近1.5万平方公里,但使团给出了完全相同的数值(65 104),这一巧合让很多读者难以置信。《美国东方学会会刊》就指出:“虽然很可能接近事实,但河南和山东的惊人巧合很难增加它的可信度。”不过,总面积的误差率相对较小(仅略少2.4%)。而且,即便存在最大23.6%的误差率,相比于人口统计,这份面积数据的可信度也相当高。
使团成员还试图通过比较中国与欧洲的人口密度,来检验乔人杰提供的数据是否合理。马戛尔尼测算:法国面积约为16.2万平方英里,中国内陆面积约为此数的8倍,法国人口约为2 700万,假设两国人口密度相当,则中国约有2 700万×8=2.16亿人。他又根据自己在两国的生活经历,判断中国内陆的人口密度应该高于法国,所以3.33亿的数据可信。老斯当东(George Staunton)同样认为:中国内陆拥有广袤而高产的耕地,人口密度比欧洲人口最集中的国家还高1/3,应当是可信的。
就这样,马戛尔尼使团收获了一份涉及中国最基本地理信息且可信度较高的资料。单单这一份资料的价值就不逊于清政府赏赐的数千件礼品——它满足了使团考察中国国情的初衷。就像英王国书所说:“要把各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
三 马戛尔尼数据在欧美世界的传播与修正
上述关于中国内陆疆域面积的数据(以下通称“马戛尔尼数据”),伴随使团返程,尤其是各类游记的出版,在欧美世界广泛传播。它们作为最“新潮”和“精准”的中国知识,被各国学者频繁征引。
这些信息的固有特性,以及19世纪西方知识传播形式的变化,有助于我们考察它们的流传状况。就前者而言,相比于一些文学性描述或简单数据,上述十几个万级至百万级的数字,就像“密码”一样,具有极高的辨识度。一个从未接触使团游记的西方人,或许可以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乾隆皇帝的样貌,或者中国有15—18个省,但是,他绝对不可能“脑补”出山东省的面积为“65 104平方英里”。即使同样依据唐维尔地图,他也不可能恰好复制使团成员的测算误差。因此,当一份文献里出现“山东省面积65 104平方英里”时,即便它没有标注来源,我们依旧可以将其追溯到马戛尔尼使团。而且,西方文献中对“参考资料”的标识逐渐走向规范化,也为我们缕析“引用”与“被引用”关系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例如,1803年,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原理》第2版问世。他引用了斯当东的材料,获知中国的人口(3.33亿)和面积(约为法国的8倍)。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过于稠密的判断正是基于这些知识作出的。1805年,首名进行环球航行的俄国人里相斯基(Yury Lisyansky),在广州写作的见闻录中提到,自己就是通过巴罗游记了解中国的领土和人口数字的。
有趣的是,使团的初衷是获取人口信息,疆域面积只是副产品,但是后者的质量明显更高。在西方世界的传播过程中,读者群体也对人口数据抱有更多的怀疑,而对面积数据基本采信。与里相斯基同时期的俄国航海家克鲁森什特恩(Adam Johann von Krusenstern)就表示:直隶省人口密度是644人/平方英里,而土地肥沃的江南省仅为300人/平方英里,“这一比较使我有理由怀疑那些统计数字的准确性并推测直隶省的人口统计做得不可靠”。随着时间推移,具有时效性的人口数据,价值贬值。而在19世纪前期,由于中国疆域基本稳定(特别是与拿破仑战争时期欧洲版图的剧烈变动相比),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多外国人都认为,马戛尔尼提供的领土数据已经能够满足需要。正如阿美士德使团的成员埃利斯(Henry Ellis)所说:斯当东、巴罗、小德经(Chrstien de Guignes)等人的作品,“已经满足了他们各自使团那个时代公众的好奇心。由于中国几个世纪的变化还不如欧洲几十年的变化大,所以现在也不会有多少改变”。
当然,马戛尔尼数据也存在不少缺陷,人们亦着手开展修正工作。一方面,基于认知惯性,很多人在整体沿用的基础上展开调整,比如拆分三大省面积,修正山东、河南等特殊数据,或者计算完整的中国疆域总面积。更有人“另起炉灶”,自行利用其他地图,重新进行计算。由于他们使用的地图版本、测算方法不尽相同,再考虑误差因素,于是各种相异的数字接踵而现。19世纪3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布戎(Conrad Malte Brun)根据新绘制的地图,测算出中国总面积约为67万平方法里;在人口方面,沿袭使团提供的3.33亿。1841年,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John Ramasy McCulloch)编辑出版《世界各国地理、统计、历史词典》第1卷,其中有关中国的词条称:在马戛尔尼开风气之后,又有布戎等人开展新的测算,但他们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有鉴于此,他依据奥格尔比(John Ogilby,17世纪苏格兰地图学家)和杜赫德等人的地图,进行重新计算,得出中国总面积约为530万平方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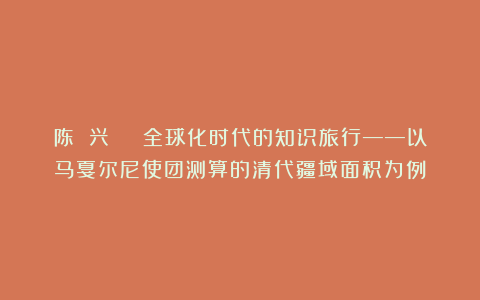
再回到马戛尔尼数据。鸦片战争前后,马戛尔尼数据被《中国丛报》广泛引用。1832年,《中国丛报》在介绍中国人李明徹绘制的《大清万年一统经纬舆图》时,鉴于总图比较粗糙,难以测算,所以直接取用西方既有的数据:中国内陆各省面积约为1 298 000平方英里,而整个国家的面积“比欧洲的总面积还要大”。“1 298 000”这个数据,可以判定为马戛尔尼数据的约数。
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丛报》在十年间断断续续地连载“中国分省地形”,省域面积数据完全取自马戛尔尼使团。最早刊登的《浙江省地形》称:“根据马戛尔尼的计算,这个省有39 150平方英里(25 056 000英亩)。”紧随其后的江苏、安徽两省,由于使团计算的是江南省,所以作者模糊地表示:“关于这个省(安徽)和邻近省(江苏)的计算有些不确定,因为它们各自的区域无法确切划定。根据巴罗的说法,江南省有92 961平方英里。”其后连载的其他分省介绍,除了两湖、陕甘是估测值以外,其他均引自使团。
随着中国的国门被打开,领土边界日渐清晰,西方人对中国地理的考察工作不断深入,这片土地的神秘外衣逐渐褪去,“欧洲和美国的公众不再相信少数被允许进入中国疆界的旅行者和传教士们那些有趣和夸张的报告中提供的有关中国问题的信息了”。按照常理来说,凭借更精密的地图、更高超的技术,地理学者有能力测算出更准确的面积数据。但是,基于常用数据的惯性,并非十分准确的马戛尔尼数据仍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而且,经过某些晚出著作的转引,相当多缺乏“史源”意识的读者,还会将马戛尔尼数据误认为19世纪的“新知识”。1858年,英国作家乔治·赖特(George Wright)在为画家阿洛姆的中国绘画撰写文字介绍、补充地理信息时,虽然宣称取自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的新著,并称作“最新的权威”“可以安全地作为指导”,但分省面积分明还是马戛尔尼数据。
在马戛尔尼数据的传播链条上,美国汉学家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编辑的《中国丛报》、个人著作《中国总论》里面,汇集了内容丰富且相对权威的中国人口数据,而领土面积一直沿用马戛尔尼提供的资料。除此之外,卫三畏还谈到一些其他资料来源。总结性的《中华帝国各省地形》一文说:“整个中华帝国的面积估计为530万平方英里。”《中国总论》除了将马戛尔尼数据视为“一般估算”外,也介绍了其他学者(布戎、麦克库洛赫)的计算结果。
19世纪的西方世界在讨论中国人口问题时,往往会直接取材于卫三畏的作品,附带的面积数据也被广泛采信。《中国丛报》问世后不久,瑞典学者龙思泰(Anders Ljungstedt)的《早期澳门史》就取材于此。19世纪50年代编写的《大英百科全书》第8版,也通过引用《中国总论》收集的中国人口统计表,附带写入面积数字。
上承卫三畏《中国总论》、下启东亚知识界的代表性文献,莫过于时政资料集《政治家年鉴》(以下简称《年鉴》)。1864年,英国学者弗德立克·马丁(Frederick Martin)主编的《政治家年鉴》第1卷出版。在“亚洲”卷“中国”章“人口”节,编者采用的是原汁原味的马戛尔尼数据。而在它的参考文献里,《中国总论》赫然在列,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
最初十几年里的《年鉴》,内陆分省面积基本遵照原始记载,此外,又新增各种版本的边疆地区数据,形成完整中国的总面积。1880年,《年鉴》对湖广、江南、陕甘三大省的数据进行拆分,形成广为流传的18省面积。此后二十余年的《年鉴》在基本沿用既有数据之外,对部分省份进行调整,例如山东、河南的数字巧合被修正;甲午战争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所以福建(含台湾)由53 480减少为38 500。
直到1903年,《年鉴》才完全放弃这些陈年数据,取而代之一套全新的数据。新版《年鉴》很快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地理的重要渠道。丁韪良(W. A. P. Martin)1907年出版的《中国觉醒》里的内陆各省面积,便是由基督教内陆会(China Inland Mission)报告转引的新版《年鉴》数据。无独有偶,同一年,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的汉学著作《中国振拔》也是采用《年鉴》里的同一套数据。不过,凭借卫三畏《中国总论》持续性的影响力,马戛尔尼数据始终占据一席之地。
四 马戛尔尼数据在东亚世界的传播与换算
(一)英制单位
经由鸦片战争前后开启的又一轮“西学东渐”浪潮,马戛尔尼数据也逐渐传回东方。在通过西学书籍了解外国地理的同时,一些中国士人对本国地理的认识也得到深化,他们不自觉地使用一些零碎的信息残片。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组织翻译的《澳门新闻纸》中,有一篇称“若论人民之多,即无一国可以与中国比较”,列举俄、英、法等国面积、人口数字,与中国一省相对照,称:“在中国只湖广地方,宽不过十四万四百七十七方里,即已有户口四千五百零二万。……而江南地方宽九万二千九百六十一方里,户口即有七千二百万名。”将湖广、江南各视为一省,正是马戛尔尼使团的做法,而且数值也吻合。而后,《海国图志》又引述这段译文,只是数据取了约数。
此外,林译《华事夷言录要》又称:“按秧马礼逊之数(马礼逊,官名,非人名也。父子世习汉文,其子曰秧马礼逊。秧者,小也)中国幅员一百三十万方里,户口三万六千四十四万三千人,其地之辽阔,人之蕃盛,自古鲜有。”核查原文,可知“一百三十万”正是1 297 999的约数:“根据乔治·斯当东爵士的说法,中华帝国的面积可能是130万平方英里”,“根据他(马戛尔尼)的说法,帝国的人口达到333 000 000人,最新的统计数据可能略高于此”。这次翻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把马礼逊父子的人名误读为“官名”;二是沿袭外文报刊原文的错误,将“一百三十万方里”这个描述内陆十八省的数据,错误地视为整个中国的幅员。
由于早期的《政治家年鉴》中译本删去中国部分,而日译本保留了相关内容,所以日本读者更早接触到完整的马戛尔尼数据。明治初年,一些日本学者选取《年鉴》部分内容,汇合其他资料,编译为日文,但因为是节译本,所以还没有呈现马戛尔尼数据。此后,日本正院翻译局多次试图翻译《年鉴》,总是“不毕功而止”,直到1877年,统计寮终于以1874年《年鉴》为底本,编译出版《万国年鉴》。为了便于日本读者理解,统计寮将原书中的英制单位折算为日制单位,比例为1平方英里=0.1672平方日里。日方翻译“忠于原作”与“肆意歪曲”并存:一方面,遵照原书框架,没有进行大的删节,单位换算也基本准确;但是,在细节处又暴露了针对中国的政治图谋,例如,故意删去原著归入中国的部分属地(朝鲜、琉球)。此后,日本官方或个人还多次翻译《年鉴》。每年春季《年鉴》在伦敦出版,到当年末或次年初,日译本基本就能问世。因此,在甲午战争以前,由马戛尔尼搜集的中国地理信息,得以在日本而非中国广为流传。
甲午战争以后,经由日本作为中转,或者直接从《中国丛报》《中国总论》《政治家年鉴》等西文文献中取材,完整的马戛尔尼分省数据终于在中国广为流传。但是,由于使团数据问世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它们在欧洲、美洲、亚洲之间游走,除了确有实据的修正外,每一次转引和单位换算都可能造成讹误。因此,在清末中文文献里,很难看到一组完全符合原貌的数据。以下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1900年,孙中山亲自绘制的《支那现势地图》,右下角附有《支那国势一斑》,记载中国全境与各省区的面积、人口。内陆18省中,13省数据与马戛尔尼完全一致,山西稍有出入,鲁、豫、闽、甘等四省偏差较大。这些数字,恰恰与1896—1900年的《政治家年鉴》分毫不差。孙中山从何处获取这份材料,是他蒙难伦敦期间看到的英文原书,还是日本获得的《政家年鉴》,或其他未知渠道,则不得而知了。
次年,白作霖等人从日文本转译的《新译列国岁计政要》问世,日文译者自称:“所采取之书,多择其最近者,内如英国之司投特门伊雅书。”所谓“英国之司投特门伊雅书”即The Statesman’s Year Book。核查书中数据,正与最新的1901年《年鉴》完全吻合,“最近”的确名符其实。由于20世纪的《年鉴》已经基本放弃马戛尔尼数据,因此,该书只保留一个“广东(海南在内),七九四五六方里”的老旧数字。
再看一些地理学专著。谢洪赉《瀛寰全志》收录内陆21省与蒙、藏地区的面积,其中一半的内陆省份面积与马戛尔尼数据吻合,另有个别数据可能是编写中的讹误,或者取近似值的结果。
(二)华制单位
对于1 297 999、65 104等近似“密码”的精确数字,可以直观推定源自马戛尔尼。但是,省略程度过大的130万,在没有旁证的情况下就难以断言,比如麦克库洛赫计算的1 348 870,近似值同样是130万。反之,有些数字虽然数值与马戛尔尼不合,但是考虑单位换算之后,还是可以缕清源流,譬如日译《万国年鉴》。同样的运算也出现在英制与华制之间。
1909年,《皇舆全览图》测绘工程开启二百年之后,一向被视为守旧派文人的王先谦,在家乡长沙完成《五洲地理志略》。其中“大清国”各省“疆域”条,给出了全国绝大多数省区的纵横里程和区域面积。前者基本采自《大清一统志》,只是稍有变动。后者仅缺数据不详的黑龙江、外蒙古。本来,王先谦并没有说明数据来源,但是,山东、河南两省完全一致的数字(544 319)为我们提供了灵感。通过对比两份数据,可以发现彼此之间存在相当的契合度,大多数都存在几乎完全一致的换算比例。由此可以推测,王先谦提供的面积数据,主要是由马戛尔尼数据经过单位换算而来。
偏差最大的是直隶,这是由于两人定义的“直隶”范围不同:马戛尔尼依据康熙朝《皇舆全览图》,此时直隶东、北面基本以长城为界,从雍正朝开始,大量口外地区被划入直隶,王先谦所举资料是“面积合口外计之”,比值自然相应扩大。福建、山西稍大的偏差,暂时无法获得合理解释,可能是王先谦利用了马戛尔尼以外的其他资料。编写过《东华录》的王先谦,肯定了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经历,但是他应当没有直接阅读他们的英文著作。这些数据可能是从西学书报里采编的,他也弄不清来源,正如其序言自陈:“泛览诸志,叙述歧分,译音互殊,难可推究。”
至此,《五洲地理志略》还留有一个关键问题:8.361和8.381的比值究竟有何含义?英国使团的计量单位是平方英里,王先谦使用的面积单位为“平方华里”,但是,这种“华里”的具体长度并未言明。将两者的比值开平方根,可得边长比值,再用英里的长度(1英里合1 609.344米),可以计算出“华里”的具体长度。又清制1里等于1 800尺,可以推算王先谦所用“尺”的长度为:
清末度量衡制度混乱,清廷、列强、学界、民间等各有若干套计量单位。与上述比值接近、且在地理学领域常用的单位,当属邹代钧所制“舆地尺”,1尺合0.308642米。或许,王先谦使用的计量单位就是邹代钧的“舆地尺”,甚至不排除相关数据就是来自邹氏的可能。
根据上述求比值的方法,可以发现晚清流传的不少分省面积,都是来自马戛尔尼。例如,与《五洲地理志略》同年问世的贺尹东《中国地理教科书》,收录全国内陆省份的面积,其中大部分与马戛尔尼数据的比值都是7.78左右。而7.78同样蕴含着一种换算比例:根据上述方法,可知此处1“里”约为577米,与清末“营造制”华里(1里=576米)极为接近。
以王先谦的数据为线索,继续向后考察,还会有新的发现。前文已述,二十四史里只有《汉书·地理志》以“提封田”形式呈现疆域面积,此后便消声觅迹。而中国最后一部王朝正史《清史稿》,其《地理志》成于众手,草率编成,体例不一,往往不同年代的资料相混杂。比较系统的《清国史·地理志》,还是传统的“四至八道”“广纵若干”,偶尔加入新式的经纬度,还没有具体面积。到《清史稿·地理志》,则有少数几个省份标有明确面积,最关键的是,这几个数字都与《五洲地理志略》一致。这可能是王树枏在汇编前人成果时“略加删并润色”的结果。
表5虽然无法证明《清史稿》直接承袭《五洲地理志略》,但是可以确定:两者均来自同一数据系统。其中,内蒙古、青海的数据应另有来源;江苏、湖北两省,则出自西方人对马戛尔尼数据的拆分——此时距离英国使团访华已经过去130多年,距离康熙朝《皇舆全览图》问世也已超过200年。《清史稿》编者在抄录这几个数字的时候,大概并不清楚它们背后的历史。
到《清史稿》初步完成的时代,陈旧的马戛尔尼数据早已失去科学效力。但是,民国地理学者在测算领土面积时,还是将它们作为参考。1930年,北平地质调查所的杨曾威,奉上级翁文灏之命,利用新版地图测算土地面积,其间曾注意到卫三畏等前人的成果,但不知其资料来源:“按Williams之面积数目,曾载于其所著之The Middle Kingdom中,但未说明其所根据之地图。……读者如有考得上列三人之著作及其所根据之地图见示者,无任欣感。” Williams的The Middle Kingdom,即卫三畏《中国总论》。1932年,利用《中华民国新地图》测算土地面积的曾世英也有相同举动。他的参照对象除了卫三畏,还有“翁文灏抄示P. S. Popoff一千八百八十八年推算数值”,查看相关数字,可知也是来自马戛尔尼使团。
结 语
疆域面积这类数字知识的存在,在近代国际体系和民族国家建设中具有重大意义。对于马戛尔尼和其他西方殖民者而言,中国的疆域面积数据,是构建整个世界殖民体系的重要知识基础之一。各项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参考这个关键数据。正如孙中山在编绘《支那现势地图》时说:“中国舆图,以俄人所测绘者为精审。盖俄人早具萧何之智,久已视此中华土地为彼囊中之物矣。故其考察支那之山川、险要、城郭、人民,较之他国舆地家尤为留意。”这种现实政策的需要,是马戛尔尼数据在近代西方广泛传播的外在驱动力。也正是这种需要的日趋强烈,特别是对数据精度和时效性的追求,促使西方学者对马戛尔尼数据不断作出修正,直至最终放弃。
对于中国人来说,本国的疆域面积数字,不仅是参与国际竞争、优化国家治理的基础信息,也是承载民族情感的关键纽带。身处“万国竞争”时代的近代中国,了解中国与其他国家疆域面积、人口规模这类“基本国情”,是投身国际竞争的必要前提,也是酝酿和落实救国之道的出发点。当旧中国的统治精英和广大民众,对自身和他国的土地大小、人口多少缺乏清晰的认知,就会陷入盲目的自负或自卑(前者通常更强烈),难以正确处理中外关系,也难以改变贫弱的现状。鸦片战争时期道光皇帝对英国地理的一系列疑问,就是典型案例。
此外,在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建构民族国家意识的过程中,国土面积也是一项被广泛运用的关键信息。通过中国巨大的面积数字,尤其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人们可以直观感受中华的“地大物博”。以上种种,是马戛尔尼数据得以在近代中国被不断引用、流传的原因所在。
而从知识流变的角度看,本文关注的一组反映中国地理范围的数字,从诞生于北京的《皇舆全览图》出发,在巴黎、伦敦、天津、澳门、纽约、东京、上海、长沙等地,进行了跨越四大洲、历时上百年的辗转,最后又回到北京的清史编修馆。这场特殊的“知识旅行”,实在是“全球化”时代文化交流热潮的一个缩影。
在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知识流变的轨迹,并不是简单的“西学东渐”或者“东学西渐”,而是东方与西方各种思想资源,在一个网络体系之内交互流动、相互借鉴。清朝皇帝委任法国传教士测绘中国地图,外国使节通过清廷官僚获取土地、人口数据,而世界各地的知识精英,也能够利用这些数据,并且根据自身的现实需要,进行修正、翻译乃至再传递。
更进一步说,当不同国家、地域的学术主体共同参与这项知识的实践活动,这项知识本身,即超越了狭义的“中学”或者“西学”范围。马戛尔尼使团测算的中国土地面积,就研究对象(中国土地)而言,自然应该归属于“中学”,就研究主体(英国使团)而言,当然可以纳入“西学”体系。然而,当我们不再局限于这一知识诞生的节点,而是放眼它产生、流变的全过程,随着众多主体的广泛参与,似乎很难将其界定为纯粹的“西学”产物,而更应该视为人类共有的知识成果。在近代世界,类似的知识流动案例应该不在少数。本文所展开的个案研究,或许可以呈现某种普遍性的意义。
责任编辑:李 乐
初 审:施恬逸
复 审:徐 涛
终 审:王 健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