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的第一份职业是务农——下农村做知识青年,那么接下去的第二份职业是务工——进作场做柯桥豆腐干。
1969年2月8日,18虚岁的我与小镇上的一批“知识青年”一起,懵懵懂懂的踏着积雪去了湖塘公社支农。
1971年12月22日,我荣幸返回小镇支了工,在一家叫食品工场的作坊里做起了一个比窃贼出门还早的豆腐师傅。虽说这个职业听起来有点不雅,但那时想谋求一个全民企业的职工堪比中状元。因此我成了小镇上一个让人刮目相看的人,这距我代表全镇知识青年上台表决心的时间不到3年。
食品工场,是供销社副食品商店下属的一个部门,位于柯桥东官塘上岸一个原仁让堰人所开的仁泰南货行旧址内。
工场直出过街路是个过楼,出过楼有个属于工场的水塔。过水塔是轮船码头(柯桥人称其为“大沙滩头”),即现在的柯东桥西南堍。
站于狭窄街路上向工场望去,光线暗淡的走道往内是个小天井,小天井的东侧置一个豆腐渣池,小天井的西侧为原材料仓库。小天井后面是以做豆腐为主的水作工场白货组,里面几近漆黑。定神细看,才发现工场里幽幽地放着一些木制或石制的工具,像是刚出土不久。木制的工具如旋桶、弯斗、灶筒、榨杆,表面都已经发了黄,显示着自己的资历;石制的工具如压石、榨石、面板石,表层泛出了一层油光,昭示着自己的历史。看到这里我吃惊不小:这哪里是一个现实中的生产车间——这分明是原始社会遗留下来的实物展示处。
穿过白货组的一扇小木门,又是个小天井。天井上搭着一些木架子,供翻晾豆腐干之用。小天井后面是个3间打通了的、单一生产柯桥豆腐干(五香茶干)的水作工场黑货组,那里面照样也是一些木制或石制的工具,只是数量要比白货组多一些,因为制作豆腐干的工序繁琐而且复杂。
过黑货组,后面是茶食(糕饼)工场,生产场地是一幢3间打通的单层平房。进车间门的右首有个大炉子,供烘烤糕饼所用,也成为融化油料物的加热处,甚至是车间职工的取暖地。在茶食车间的西侧,有一块面积硕大的空地,曾一度成为副食品商店的水产腌制池。
工场内除了上述车间,还有一个单独的磨豆间和一个职工食堂。在工场外,有一家豆制品门市部和一个制面工场。豆制品门市部设在碑牌头老街的运河边,对外出售豆腐干、豆腐、千张、油豆腐之类。每天天不亮,就有人在门市部前排起长队,或以篮子之类的乘具代人排队等候营业,成为小镇上的一条早风景。
由于受文革的荒废,致一度停招职工,食品工场人员处在青黄不接,于是我成了第一个文革后出现的青年。此前工场的人员,都是一些从老作坊里过来的,缺少文化知识,加上对外接触不多,不仅人老而且观念也老。在他们的眼里,我这个徒弟该有徒弟的样子,有徒弟的规矩。虽说已经是“新社会”了,但在他们的心里却固守着自己当年做学徒的模式,所以一候机遇,也要求我这么去照搬照套,比喻干一些为他们洗碗筷、抱小孩、倒夜壶之类的杂活。
记得报到的那天上午领导跟我说,明天早上你第一天上班可以迟一点:4点钟起床吧。虽说是照顾我了,但没有思想准备的我还是吃惊不小:迟一点4点钟,那正常上班的时间会是几点呢?
其实这个时候,他们早已在水作工场的楼上——一个杂物间里给我腾出了一张“床位”,要求我上班期间必须睡在那里,以便有事随叫随到。不仅如此,甚至在下班后的时间里,他们也希望我继续留在工场干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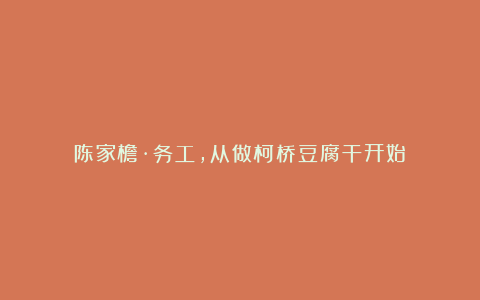
第一天上班,还在四更时分,睡梦中的我突然被一阵刺耳的鼓风机声吵醒,接着就有一阵烟雾直扑鼻孔。闻着那雾之味由轻到重,最后造成呼吸困难;看着那雾之色由淡到浓,熏得让人睁不开眼。不多时,肆无忌惮的烟雾就将整个楼层吞没。见到这样的实景,我又吃惊不小,心中猛然升起一阵恐怖感……
无奈,我只得蒙住被子睡,但依旧没有多大的作用。于是我只好在烟雾层中穿衣下楼,想快速逃离这个恐怖的环境。但是当我走入黑货组,里面的情景却是如同一辙,原来烟雾的发源地就在这个车间的灶肚里,浓浓的烟雾在鼓风机的作用下直往上蹿。抬眼望去,几个穿着灰暗、与车间色彩相当匹配的人在充满烟雾与水雾的车间里晃动:荡浆烧浆、点花上箱、包裹香干、上榨卸榨。而我的工作,是暂时帮助一位姓王的师傅剥豆腐干。
站在王师傅的斜对面,见他低着头、侧着身,飞快地顾自己剥豆腐干,似乎根本没有我的存在。只见他利索的拎住襆布的一角三下五除二,一块呈鸡油黄的豆腐干就在他的手中落了下来。这一过程,只在2秒钟内完成,我看得起惊,心想“行行出状元”一点不假,我从心里暗暗地佩服起他来。
但当我再次抬头看向王师傅的脸面时,却又让我吃一大惊:面色蜡黄,双眼暴凸,眼睛周围布着一圈黑斑。他斜着看我一眼,却没有说话,只是莫名其妙的裂开白牙红唇一笑,看得我心惊肉跳。这时坐在身后包豆腐干的一位师傅告诉我:“他是个聋哑人,大名叫王百泉,是我们这里剥豆腐干的‘大师傅’。”
居然是这样。难道从此以后我就要与王师傅搭班工作?
事实就是如此,除了夜间的正常上班工作外,白天,我们还得背船运而来的柴草,翻晒赤水的白豆腐干等。所幸的是,与他相处比较合得来,虽然语言沟通不是很方便,但彼此却是十分的信任。
后来在接触中我还了解到,这个40岁里外的单身汉先天带疾,耳朵失聪,几成全聋,虽常戴助听器助听,但作用甚微,你须吼着嗓门跟他说话;他声带受阻,发音模糊,只能说一些“哎、哎”之类的简单词。而他有他的多技之长,除了剥豆腐干无人能匹敌以外,还有一种识字的绝活。与他交谈,你只需站在他的对面,用手指在自己的掌心上画字,不管速度多快捷、字迹多潦草,他都能看得懂你画的是什么字。待你画完,他或点头赞同、或摇头“哎哎”、或脸现笑容、或手做动作,或“咿咿呀呀”说一些让你听不太明白的话,这情形让你见了乐不可支。
后来随着剥豆腐干技巧的逐渐掌握,我开始与师傅们一起一字儿坐定包豆腐干,边包边海阔天空的聊一些五花八门的旧事怪事稀奇事,也算是苦中一乐。而拿在手中的“豆腐干”,其实是经过一整套程序:浸豆、磨豆、荡浆、煮沸、出淘、点花、上箱、挤压、划块后比豆腐坚挺一点的产物。这呈粒状的豆腐包在一张小襆布中,然后整整齐齐的在横板上排进去压榨机压榨。
其实看似简单的一包,除了有统一的包法。要求豆腐干包得方正无翼膀,不能为求速度而走野路,这是对豆腐干的外观要求。在包的过程中,要手眼联动,做到手巧眼尖,除了双手的熟练,还须带看放在一旁的小襆布。因为这襆布是从压榨机里取出来的,拧在一处、皱成一团。所以你必须在包的过程中快速而准确的看出襆布的角,然后拿角轻轻一甩,这样既展平了襆布,又缩短了寻角的时间。
说起甩襆布,又是一件不太乐意干的活。身穿一套带着满是浆汁的“工作服”,脚踏一双湿漉漉的半通靴,浑身散发着豆腥味的我,一手拎着满弯桶的襆布、一手拿一块横板招摇过街去河埠头掼襆布。到了那里,先拿襆布在河水中摇动几下,然后开始掼襆布。掼时,一手拿横板挡住下半身,一手拎住襆布的一端向踏道掼去。掼的难点是到地面的襆布要缩成一团,倘使掼成一条线,会致出水面积增大而沾及他人之身。
就这样日复一日,我或是在夏夜的12点钟起床上班,或是在冬夜的1、2点钟哆嗦着起床,恍恍惚惚又战战兢兢的与豆与水与烟与雾与豆腥打交道。这样的营生持续了2年(期间我还到过白货组、茶食工场及代理仓库保管员)。此后的我却是义无反顾地去了新建的副食品大楼做起筹备工作……
至此,我终于花了5年时间,游走到了旧时三大苦职业“打铁摇船磨豆腐”的边缘甚至中心:初中一毕业与邻居哥去了一个村子,跟着瞎子、跷子、聋子磨铁砂;继而在农村随农民兄弟摇着船去捞草、割草、摸草;最后在水作作坊里做豆腐干、豆腐、油豆腐。这“三苦”不仅让我长了见识,而且让我体验了生活。虽说当时确实有点苦相、有点怨言,但过后嚼起来还是有点味道、有点值得——命中注定,难得一遇。
于是至今,那薄薄的、软软的劳什子外呈赭色,富有光泽,内有线孔,裹藏鲜水,香气浓郁,味道鲜美;质地柔软,富有弹性,韧而不硬,软而不脆,对角相拗,不致断裂…… 于是至今,一说起这江南名特产——柯桥豆腐干,就会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在我的喉间翻滚。这味道,与我做柯桥豆腐干有着密切的关系。
正中(远处)有座水塔,水塔下面是轮船码头,有人在等船。轮船码头的南首就是食品工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