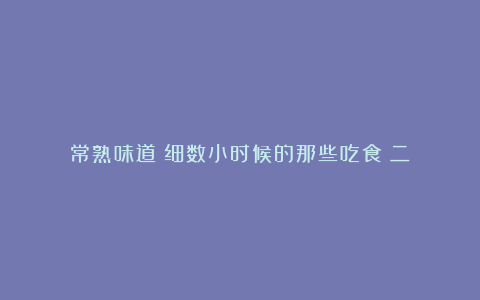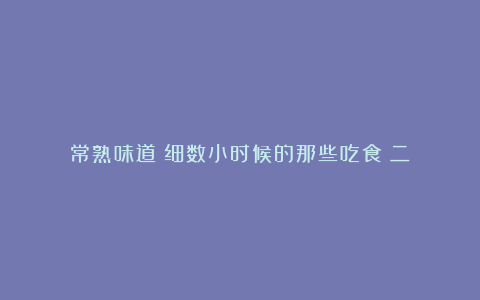海外游子最想念的常熟味道
——细数小时候的那些吃食(二)
文 / 黄仁彬
点入名片👇关注并查阅往期
常熟与江南其他城市一样,早点十分丰富,品种繁多,价廉物美。常熟人最喜爱的就是面,它基本上是属于苏式面,但没有苏州面(包括浇头)那么甜,是咸鲜口,但稍有点偏咸。
城内有众多面馆,比较大一点的,在城中有寺前街北赵弄口的聚兴面馆,以什锦面为最有名,里面有肉片、鱼片、火腿片、肚子、肫肝、蹄筋、虾仁、笋丁等等,属于白汤面,汤头浓郁,其味极鲜,价格也最贵,每碗一角三分。上海二表姐来常熟写生时请我们吃过这一最貴的面,但仅此一次,却终生难忘。
对面是同兴面馆(也叫老同兴),主打大肉面,不同于苏州的焖肉面,实际上就是红烧大片五花肉,浓油赤酱,肉质肥嫰,卤汁鲜甜。
北赵弄北端寺后街口是四时居面食店,主要经营北方口味的各色煨面,面条都是自擀的阔面,还有烫面饺、牛肉锅贴、牛肉煎包等。
在北寺心有瑞丰面馆,最有名的是虾仁面,都是当天手剥的新鲜河虾仁,用现代语是“Q弹”,红汤面,表面飘了一层虾油,鲜香无比。
在县西街老县场口是同丰面馆,它的爆鱼面最有名,都用青鱼熬煮,外酥里嫰,卤汁饱满。
南门平桥街上有全家福菜馆,早市也买汤面。北门新公园的肉丝面及虾仁肉丝面也相当有名,吃茶的茶客常叫到茶桌上当早点。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小面馆散布于常熟城内的各个角落。
常熟人喜欢吃面的传统已有较长的历史,这也把常熟人的嘴巴吃刁了,他们的味蕾能迅速辨别各家面馆的高低、特点,面馆老板也深知忽悠不了这些刁嘴的食客,不管面馆大小,各家都秘制自家的汤头,绝无一家仅以猪油加酱油味精用开水冲料。再加上食材每天新鲜,古法酿造的酱油,老师傅的精巧烧煮,这样的一碗面怎能不好吃?!
有些小店比大面馆的面更鲜美更有特色,如一家叫张三的小面馆,经几个老饕的推荐,人们纷纷去尝试,赞不绝口,以致后来张三搬到较偏的西门湾去开店,这些老吃客不怕路远起早,像苍蝇一样嗡着过去吃,真是“食客跟着掌勺走”!
我们小时候好像常熟没有什么冰箱之类的储存器,所以至今也弄不懂,这些面馆当天卖不完的浇头是怎么处理的?
此外,那时没有味精一说,后来大概是从日本进口“味の素”,日文中的“の”意思是“的”,所以,那时常熟人把味精叫“味之素”。早期饭菜館和普通家庭都不用“味之素”的。
常熟其他的点心有大馄饨、绉纱馄饨、汤团、葱煎馒头、锅贴、烫面饺、馒头、大包子、油斗、大饼油条粢饭糕、蟹壳黄,老虎脚爪、粢饭团、粽子、洋糖糕等等。
那时,常熟的馄饨都是红汤的,馄饨加两只汤团是早点的绝配。常熟馄饨汤团店很多,但都是小店,有名的如北赵弄的五芳斋(?记得好像还有一家)、方桥头的方桥,但县东街口的一家馄饨汤团店最有名气,用的是糯米水挂粉,有鲜肉、豆沙、芝麻、玫瑰各色品种,后三种芯都放猪油丁,吃口软糯甜滑,一口下去,汤汁饱满、馅沙直流,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常熟的绉纱馄饨类似于苏州的泡泡小馄饨,但其肉芯较多,如果说泡泡馄饨像飘浮在水面上的一个个气球的话,那么绉纱馄饨就是水面上的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花,皮薄爽滑,肉感充足。
葱煎馒头类似于苏沪的生煎,但它的面皮是发酵的,个头也稍大,表面是密集的葱段,底部属软煎,有点像北方的水煎包,吃起来较松软,葱香浓郁,一般是下午的点心。
烫面饺用的是热水拌和的面,有水煮和蒸煮的,类似于现在的水饺和蒸饺。
馒头是最大众化的点心了,有肉的、菜的、豆沙的、玫瑰的、萝卜丝肉的等等,由于那时食材新鲜,所以吃起来感觉更加鲜香。
大包子是指像炮弹头样的无芯馒头,常熟人也叫高脚馒头(南方人一般将有芯的叫馒头,无芯的叫包子;而北方人的叫法恰恰相反,为避免误解,常熟人来个折中,如大包子也叫大包子馒头)。
馒头、大包子以北赵弄南端西侧的那一家最好,大包子馒头买回来后,一般醮点甜酱配白粥吃最佳。
油斗,常熟人也叫煎团、油癞团(常熟人叫癞蛤蟆为“癞团”,大概油斗形状像癞蛤蟆,故此得名),是用糯米粉包的鲜肉团子,但做成像短颈葫芦状,再放入油中汆或煎至通体金黄,类似于苏州红火的油汆团子,一般就在大饼油条粢饭糕的摊店上卖,是常熟极为普通的一种小吃。
我们上学来不及吃早饭或者下午放学后就买一只油斗或一块粢饭糕吃吃,记得好像一只油斗三分,一块秶饭糕两分,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油汆(油煎)的东西。
洋糖糕也是一种油炸糯米食小吃,它是用糯米粉做成一条条长圆形有点绞花状的短条,放油中汆,冷却后外面再滾上白色的糖粉,属于一种甜食,吃上去又糯又油又甜,如今已见不到了。
常熟还有一种十分有名的小吃,叫石梅盘香饼,它是用油酥面加猪油丁、葱花揉成一长条,然后将其圏绕成圆形或长圆形,洒上芝麻烘烤,层层酥皮,粒粒掉渣,葱香扑鼻,是一种高级的烧饼。
由于此饼仅在石梅茶馆制作,供茶客一边喝茶、一边吃点心,故名“石梅盘香饼”。石梅茶馆关门后,一度消失,直至改革开放后各地挖掘名小吃,才重新登场,然而不知已否还是原来的味道,並未尝过,因为原来的老师傅早已不在,我也不信如今众多真假难辨的商业化宣传。
早上我们一般吃粥,买些大饼油条或大包子馒头搭吃。粥菜为酱瓜、乳腐、炒酱、雪里蕻炒毛豆子等。
我们买油盐酱醋及酱菜都到最近的顾源盛酱油店,它也是那种前店后坊的店铺,位于西门大街书院弄口,离会元坊很近。一般居民家庭常自带容器去零拷,很少有买原瓶头的。母亲烧菜时常差我们跑一趟去,因为孩子跑得快,一会儿就买回来了。
店里有大小不同容量的吊勺,这种吊勺是圆柱形容器上面带一根长长的把,有木制的、洋铅皮做的,买的時候将漏斗放上你的容器,然后按不同份量的吊勺拷上。
那时的酱油浓郁芳香,完全用黄豆土法酿制,所以有时吃饭无汤,冲一只荤油酱油汤或麻油酱油汤也十分鲜美。后来又出現了一种“帕来品”,叫白酱油,其味更鲜,但不知是一种化学制剂,还是常熟“排外”,不久就从市场消失。
买糖盐等固体调料,则店家预先用纸袋装好,买酱菜则用黄山草纸或油纸,甚至荷叶给你包上(那时还没有塑料袋),乳腐则需自带容器。
酱菜中最便宜的是淮片老卜,大概是苏北运来,死咸死咸的,掰一小块下来可应付一顿早餐,有时我们放学回来没什么吃,就掰一点吃吃,但实在太咸,吃得喉咙发齁。
五十年代中,街头还有叫卖香大头菜的,都是外地来的小贩,他们背着一只笆斗,吆喝着:“香……大头菜!”“香”字特别拖长音,有时也坐在街头巷口的街沿砖上,这种香大头菜,用大头菜切成一片一片的,但不切断,上面还连着大头菜叶,经土法腌制,咸菜色,咸中带甜,奇香无比,极其鲜美。
买时不称,撕片,可多可少,我们放学时常买一点放口袋内当零食,不时拿一点出来咬咬品尝。现在这种东西好像也已见不到了,十分怀念。
糕团也是普通民众喜爱的食品之一,它有许多品种。我记忆中好像没有一家专卖店,大部分是点心店、早点摊兼售及流动摊贩叫卖(小时候,松盛糕团店、新雅点心店还沒有),如庙弄口西侧就有一小吃摊买油条、粢饭糕、煎团、南瓜饼(常熟人叫番瓜饼)、各色糕团等,在城隍庙口也有一老太经营的小吃摊,也是卖差不多的点心,她家的南瓜饼特别好吃,油汪汪的南瓜饼,又黄又亮,经煎热后一口下去豆沙加透明的猪油丁直冒。
这些店做早市及午时,为上学的学生及上班的职工提供早点,还有就是下午的小点心。
我们住在会元坊时,有一个卖糕团的癞痢头长子是我们熟悉的流动小贩,差不多每天挽着竹盘篮直冲到我们灶间兜售,篮子中间镶嵌有一只小平底铁锅,周围放着各种糕团,有黄松糕、猪油赤豆糕、人条糕(即苏州人说的条头糕)、蜜糕、桂花血糯糕、方糕、定胜糕、鸡团、糯米粢毛团、南瓜饼等等,各种色调各种形态,让你眼花缭乱,不知挑何为好。碰到特殊需要时,父母常向他预订定胜糕之类的品种。
此外,像苏州的桂香村一样,在益泰丰及莉莉公司等大的茶食店早市也有方糕,现蒸现卖,有鲜肉、豆沙、薄荷、玫瑰等多个品种,皮薄馅多,甜的里面都有猪油丁。
那时的糕团用全糯米或糯米粉比例高,所以又糯又甜,即使如今有名的苏州糕团也略逊一筹,大概是都渗入太多粳米粉之故。
有一种糕团叫黄尚,是常熟特色的品种,它是用熟的糯米粉团中间夹豆沙揉成一长条,外面滚满黄色的松花粉,然后滚刀块切成一段一段整齐码放在布上,像一只只金元宝,边上露出白色的糯米团,中间翻出滿滿的豆沙,十分诱人,它有点像北京的驴打滾。如今还有得买,以松盛糕团店的为最有名。
常熟的烧熟店,现代人叫卤菜店,最有名气的就是马詠斋了。位于寺前街中段,座南朝北,单开间门面,长长的红框玻璃窗内摆满了各种卤菜,走近店堂,老远就香味扑鼻,它也是传统的前店后坊。就地取材,食物新鲜,秘方卤煮,其味独特。
它的每种卤食都与众不同,最有名的有酱鸡、酱肉、酱蛋、肉松、爊鸟、熏鱼、熏蛋、脆鳝等等。酱鸡皮色酱红,油光锃亮,卤料入肉透骨,斩开后,不像现在的白斩鸡,肉质白色不入味。
采用的都是放养肥壮土鸡(那时的鸡都是土鸡,后来才引进洋鸡,即养殖鸡,常熟人叫白洛克鸡,常熟人一般不吃的),所以肉质肥嫩鲜美;酱肉呈深红色,与苏州玫瑰红的酱汁肉与樱桃红的樱桃肉不同,也不同于苏州的酱肉,它的颜色较红亮。
用黑毛猪烧煮(以前常熟都吃黑毛猪,白毛猪叫洋猪),肉烂肥嫰,香味浓郁;用肉汁卤煮的酱蛋也很入味,别具一格。所以常熟人也特称它们为“马鸡、马肉、马蛋”。
父母每次去上海,外婆总是嘱咐带“马鸡、马肉”。而每次外婆从上海来常熟,也总要带她自己烧的红烧牛肉,非常香,这种味道常熟吃不到,我们总是抢着空口先尝一块。
马詠斋的肉松也不同于一般的肉松,比如,太仓肉松颜色淡黄,咸鲜,吃口有些棉絮状,而马詠斋的肉松颜色深黄,咸中带甜,絮中伴酥,余味久存。一般为倒棱台形黄纸包装,上附一红色招牌广告纸,也有用硬纸板巻成的大小不同的圆筒装,分一斤、半斤、二两装的,是送礼佳品。
很小的时候我在上海,最喜欢吃福建肉松,实际上可能就是現在的台湾肉松,那时只会向母亲叫:“松!松!”这种肉松呈酱红色小颗粒状,鲜甜可口,酥脆无渣,特别适合缺牙的老人和幼童,后来在常熟的广州食品店也有卖。
马詠斋的爊鸟为将虞山中的山雀用素油麻油爊制而成,香味扑鼻,肉鲜骨酥,连头带骨可一起咀嚼,是下酒的佳馔,为山珍野味。
在1958年“除四害”运动中,马詠斋也应时推出爊麻雀新品。现在也常能看到常熟的爊鸡、爊鹅等,一次我经过一个制作爊品的工场,那种味道感觉爊味过头,且死咸的,反而成了一种“齁”味。
马詠斋也卖熏鱼、熏蛋等,真正是用松针、木屑熏制,有一种特殊的清香熏味,如今只剩回忆了。它的脆鳝外形坚挺,乌黑发亮,吸滿卤汁,鲜甜松脆,与无锡的梁溪脆鳝有得一比,但比无锡的少甜些。
我们每次经过马詠斋总要隔窗看看,闻闻香味,偶而买两分一块最便宜的肉汁豆腐干,一小角一小角的慢慢享受。
2022年3月下旬举办的《漫画中的上海风情》中,看到了著名连环画家贺友直的关于馬詠齋的回忆文字,还配上了漫画,感觉特别亲切,因为馬詠齋是创始于常熟的百年老字号。
上世纪八十年代寺前街拓宽改造,常熟人钟爱的百年老店马詠斋被拆,一度消失,后来在县后街琴川桥附近又重现,但已“物是人非”,里面的卤菜已沦落为一般熟菜店的水平,过去那种特色风味再也尝不到了,甚至有的觉得有些难吃,店员也变了外地打工口音,不变的只有那块黑色金字招牌。
记得当时,寺前街上还有两爿熟食店,龙詠斋和大詠斋,都是座北朝南,一家在天然池隔壁,一家在临近北市心处,他们的爆鱼、爆鳝、酱排骨也比较好吃。
还有一家设于同兴面馆门口的熟食摊,卖自制各色卤菜和时令菜,从菜花甲鱼到汆小鱼,从酱鸡酱鸭到猪头肉,什么都有,味道也还不错。荷叶粉蒸肉一卷巻包好迭放,荷叶经蒸煮后呈紫黑色,渗透出浓浓的油脂,打开后肉香、粉蒸料香、荷叶香汇集一起散发开来,直让人流涎。他家卤菜价格较为低廉,颇受一般平民青唻,特别是那些喝小酒的。
这里还需要提到儒英坊的方块肉,常熟口碑甚好,是在儒英坊口的一家庭作坊,没有店面,仅家门口放一大锅,里面是红烧大方块肉,有点像如今的东坡肉、稻草扎肉,皮红油亮,肥嫰酥烂,香飘四方。他家的鸡笃面筋也很鲜美,附近居民家中来客时,常差孩子自带容器去那儿买几块方块肉和鸡笃面筋汤招待客人,远道而来城里办事的也往往带几块肉回去品尝。
解放前后,常熟城内比较有名且大的菜馆饭店有山景园和鸿运楼,山景园在书院弄、吉翠园弄口,座西朝东,一幢两层木结构小楼房,外面有霓虹招牌广告,门面很小,有点像旧时的家庭旅馆,进门是帐房间,楼上楼下都有小厅和小间,红色蜿蜒而上的木楼梯很有历史年代感。
食材都采用当地的新鲜货,经有精湛厨艺的老师傅烹饪(记得有一个叫炳师的大方脸师傅),创造出许多美味佳肴,如油鸡、爊山鸟、樱桃肉、乳腐肉、栗子鸡、栗子烧肉、雪烩,清炒河虾仁、煨鸽蛋蹄筋、清蒸火腿鲥鱼、草头刀鱼、腌笃鲜、一品锅、冰葫芦、炒桂花血糯、桂花栗子羮,各色炒面等等,当然也有最出名的叫化鸡(也叫煨鸡)。
山景园的油鸡是最有名的冷盆,几乎每个食客必点,它用的是常熟本地农家鸡,鸡皮黄亮肥脆,肉质细嫩鲜香,再淋上秘制的爊油和酱油,满桌喷香,让你筷子停不下来。爊山鸟也是冷盆,取自虞山山林中之野雀。
在秋天盛产栗子时,用虞山的新鲜白壳桂花栗子加入鸡或肉中烧煮,就是栗子鸡和栗子烧肉,酱红色的鸡、肉中点缀着黄澄澄的栗子,鲜甜中渗透了阵阵桂花香,吸饱了肉汁的栗子甜糯酥烂,肉中又渗透了阵阵桂花栗子香味,达到了完美结合。
雪烩是将鲜美的雪里蕻加入到走油肉中,加优质酱油和白糖烧煮,雪里蕻鲜甜油润,走油肉鲜香甜嫩,特别是上面吸满了卤汁的虎皮,是最先被扫光的对象。
一品鍋实际上是各种食材的蒸菜汤锅,集各味之精华,喝一口汤真是有眉毛要掉下来的感觉。冰葫芦是用网络油包裹猪油丁外挂面糊做成葫芦状,再油炸,最后外面滾上绵白糖,是一道甜菜。
炒血糯也是常熟特有的一种烹调方式的甜点,外地血糯一般做成八宝饭蒸煮,再淋上冰糖汁,而常熟是用地产血糯米蒸熟后,下油锅加猪油白糖翻炒,最后洒上桂花,滾烫香甜,油润滑糯,别有风味。
另一家有名且大的饭店叫鸿运楼,位于寺后街培纶公寓隔壁,与山景园相距仅百余米。鸿运楼为民国中西建筑,前面为一门院,进入门院是一圆柱大厅,花岗石花纹磨光地面,周围有彩色玻璃廂房,楼上也有大厅、迴廊、包廂、房间,建筑气派,所以一般富贵人家喜庆筵席大都在这里举办,我们小时候跟父母参加过多次,记得堂叔黄应辰的婚礼就是在此举行的,新郎新娘西装婚纱,军乐队伴奏,亲朋好友齐来贺喜,楼上楼下摆滿喜桌,热闹非凡!我们是跟着吃、看排场。
解放后,1950年左右我们因参加市文教局组织的赈灾义演,结束后市政府在鸿运楼设宴招待慰问所有演职人员,那天菜肴十分丰盛,已记不清有哪些菜了,只感觉吃得“昏天黑地”,直到太饱想吐!
鸿运楼平时也接待客人居住,所以是旅店兼饭店。上海舅舅他们来常,常住鸿运楼及附近的几家高级公寓,如培纶公寓、吉翠园公寓等。记得有一次他住鸿运楼,叫了山景园的叫化鸡及其他的许多菜,让送过来。店员挑了竹圆笼,当打开荷叶包裹的叫化鸡时,那香味立即迷漫整屋。
叫化鸡肚内塞了火腿丁、肉丁、香菇丁、虾仁、笋丁,各种食材香味汇集一起,直把人迷倒,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並尝到了叫化鸡。几十年后再一次吃过叫化鸡,却已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了,且吃口“干吧”。
常熟还有许多小饭馆,各具特色。北赵弄内有六马路菜館、寺南街口也有一家两层小楼的菜馆,黑色木板门面,名字叫不出了,生意也很兴隆,是一般平民百姓常光顾的地方。
当然,常熟名气最响的是王四酒家了,但它坚持不在城内开店,而设在郊外虞山兴福,旧王四酒家像农家菜馆,两层小楼,木格子窗,方砖地,八仙桌长条櫈,两边木楼梯上楼,木地板,开窗即见蜿蜒的虞山,门前一片大场,有几棵参天古银杏树,周围是农家小屋,尽显乡村古朴。新鲜食料、山珍野味,就近取材,叫化鸡是“王四”最有名的菜品。
虽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但慕名而来的食客络绎不绝,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宋美龄一行专程赶来品尝,轰动了常熟全城。山景园后来在王四酒家旁也开了一个分店。
如今这些大小饭店除王四和山景园外均已不存在了,鸿运楼很早就已拆除,那些小饭店也随着城市的改造不复存在,山景园后来搬到寺前街原慧日寺后门隔壁。
改革开放后,这百年老店扩大了面门,进行了装修,增加了气派,但多次进入,与全国其他许多中华老字号一样,大失所望,几次点招牌油鸡,都离那时的水准甚远,再也吃不到那个时候的味道;鸡笃面筋,更是清水寡汤,还没有自家的鸡汤鲜。
王四酒家仍在原址,但也经过了翻造,尽显“高大上”,然而,去兴福吃过一次,也是一样,实在不敢恭维,且菜价死貴。
这些现状,恐怕除了食材本身的“先天不足”外,如今的许多掌勺者已为外地人所代替,本帮老厨师的传统厨艺已基本失传,但还是挂着这块金字招牌标高价,这恐怕是当今众多老字号被人们唾弃的症结所在。
未完待续……
“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吴文化第一山——常熟虞山
作者介绍:黄仁彬,1940年生,1946年2月-1951年7月在常熟石梅小学读书,1957年7月毕业于江苏省常熟中学,1961年7月在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数学系任教,1980年底调入苏州铁道师范学院数学系任教,先后任数学分析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1988年评为副教授,任教期间主讲了数学分析、复变函数、拓扑学等14门课程,作为主持人之一完成了数学分析课程建设,並荣获江苏省Ⅱ类优秀课程。1993年获首批全国高师院校曾宪梓基金会教学三等奖。多次参加全国性专业会议並大会发言,1993年参加一般拓扑学国际会议並在分会场上作报告,发表多篇论文。曾任苏州市数学会常务理事(高教组负责人)、苏州市教育学会中学数学分会副理事长。2001年退休。现旅居海外。
留言功能现已开通,页面底端可见“写留言”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