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2025年的四月天,晚风轻软,我、老伴和姐姐用过晚饭,照例踱向桃源桥商业街。霓虹灯影里,我驻足凝望柴家墙弄九号的旧址——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如今已杳然无迹。双脚不自觉地丈量着记忆中的格局:卧室、小堂前、厨房、朝北的小道地……而最叫我怅惘的,是母亲手植的那株梨树。
打我记事起,它就立在花坛上,足有两层楼高。早春时节,一树梨花如雪浪扑面,与父亲栽种的茶花争艳。茶花性喜阴凉,父亲深谙其性,故植于朝北的道地,恰成了它们的乐土。于是,春寒未褪时,便见”一树梨花压茶花”的奇景,人在其中,恍如画中游。父亲的书画是小城的一绝,他时常捧着写生本,对着梨花写生,仔细地观察花儿的生长规律。他常说:“写生是创作的不二法门。”他的工笔梨花图,即以家中的梨花为粉本。如今再看他的画,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二三枝,花儿偃仰向背,各呈姿态,一派欣欣向荣景象,永远绽放在咫尺素纸上。待梨花渐谢,花瓣纷飞如雨,簌簌落满石子地,倒应了那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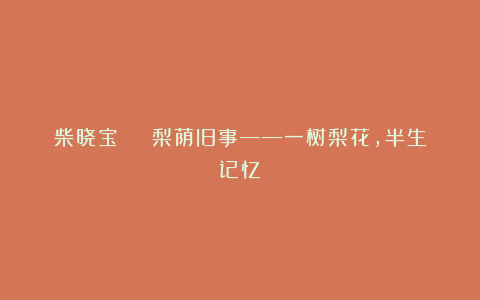
盛夏过后,梨树枝头便缀满胖嘟嘟的果实,秋阳一照,金黄透亮。蜂蝶绕树,雀鸟啄食,树上的毛毛虫难逃母亲的火眼金睛——二米开外,她便一眼锁定,叫那虫子束手就擒。最贪心的当属金龟子,专挑好梨乱啃。不过,它倒成了我们的玩物,捉来在颈部系上细绳,任它上下扑腾,能耍上大半天。“采摘啰!”母亲一声令下,我忙着架梯采摘,不一会儿便盛满竹篮。母亲笑着分给邻里,那清甜的滋味,至今唇齿留香。
梨树不仅结梨,还成了丝瓜的天然藤架。母亲在树根处种了几株瓜秧,蛞蝓(鼻涕虫)是它们的天敌。每到夜晚,蛞蝓猖狂出没,母亲便严阵以待,掌灯夜战,非要赶尽杀绝才肯歇息。几场春雨过后,藤蔓便攀枝而上。母亲日日施肥拔草,忙得不亦乐乎。秋风起时,丝瓜悬垂枝桠间,餐桌上便有了丝瓜蛋汤——丝瓜配上现打的活络蛋,再搭一把手工面条,母亲偶尔滴几滴麻油,鲜香扑鼻,堪称人间至味。
冬日梨树凋零,光秃的枝干却另有用处。朝北的道地少阳光,母亲便在高枝间拉起麻绳,晾晒衣物,万国旗似的在空中飘扬。有一回,她竟爬上竹梯,倚着梨树打盹晒太阳。父亲下课归来,抬头一看,朗声笑道:”香娘登天了!”——因大哥名”谷香”,父母便互称”香娘””香阿叔”。这昵称里,藏着一家子的温情。
老家朝北小道地,是父母精心打造的百花园,给我们带来太多欢乐。夏日午后,我躺在梨荫下的藤椅上,四周围着一群小辈,嘻嘻哈哈地给我扇蒲扇、敲背、捧凉茶。侄囡小燕还只有四岁,她不停地咽着口水,仔细削好梨,又怕弄脏,竟用舌头舔了一遍。我哭笑不得:“这还能吃吗?”那时,我俨如成了“小皇帝”。小家伙们最爱听我讲故事,我便把从父亲那儿听来的笑话添油加醋,海阔天空地发挥,逗得他们前仰后合,连连追问:“下面呢?下面呢?”一个“卖香屁”的故事,成了他们的口头禅,至今还在传讲——小阿叔因放香屁被皇帝召见,荒唐又滑稽。
还有一件趣事。上世纪60年代末,全民挖防空洞,我家也在梨树下挖了一个。我干劲十足,特制了短柄锄头,没几天就挖了二人多深。谁知一场大雨,防空洞成了蓄水池。我正懊恼,母亲却笑着说:“这下梨树和丝瓜浇水的用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