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写深秋,就不能只写深秋。
要写第一阵砭骨的西风,
像古琴师试音的指尖,掠过大地紧绷的丝弦。
要写霜迹,不是薄薄的一层,
而是夜神用狼毫蘸着月华,
在每片草叶的刃口上写下的银白篆书。
要写天空,那被浣洗过无数次的蓝,蓝得如此空旷,
仿佛能听见云雀去年春天留下的啼鸣,
还在那虚无中打着旋儿。
要写树。不能只说落叶纷飞。
要写梧桐最顶梢那片孤悬的叶子,
如何在与风最后的角力中,绷出金石般的筋络。
要写银杏的告别式,千万把金箔小扇同时松开手,
为大地铺一场寂静的、簌簌作响的暴雨。
要写乌桕,它的红不是春花那种喧闹的红,
是生命在告别前,
从骨髓里熬出的最后一抹、带着苦味的酡红。
要写水。不能只说寒潭清冽。
要写荷塘里折戟的枯茎,
像一场盛大战役后遗留的矛戈,
依然保持着冲锋的姿态,
守护着水底沉睡的、洁白的梦。
要写河流慢下来的心跳,水变得如此澄明,
仿佛能看穿时间,
看见卵石亿万年前作为山峰的峥嵘。
要写暮色里,夕光如何像稠密的蜂蜜,
缓缓注入江河的血管,
让冷冽的秋水也暂时温暖、滞重起来。
要写光。要写午后三时,太阳斜射过窗棂,
在旧书页上投下的、比夏天漫长三倍的光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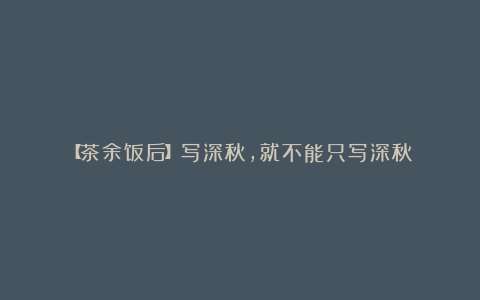
光柱里浮动的微尘,是时间具象的骨血。
要写月色,秋月不是纱,是霜,是磨得飞薄的瓷片,
碰一下,指尖都会生出凉沁沁的回响。
要写气味。是新稻入仓后,
谷仓里丰饶的、让人心安的暖香;
是雨后,腐烂的落叶与湿润的泥土混合成的、
带有酒曲味的芬芳;
是某个深夜,不知从何处潜来的、那一年里最初的、
若有若无的蜡梅的冷香,像一句神秘的预言。
要写声音。不是喧哗,是更大的寂静。
是鞋底踩碎枯叶时,
那一声清脆的、关于逝去的叹息。
是夜读时,窗外唧唧的虫鸣,
一声比一声稀,一声比一声远,
最后彻底融进墨色的夜空里。
是清晨,屋檐下那只最后离去的燕子,
振翅时划破空气的、那一缕微弱的涟漪。
最后,要写人。不能只写愁绪。
要写母亲翻出箱底的毛衣,
在阳光下拍打出的、带着樟木味道的云。
要写晚归的人,
呵出的白气如何在街灯下瞬间成形又瞬间消散,
像一句来不及说出口的独白。要写你自己,
在某个突然安静的片刻,
心头泛起的那阵无边的、清澈的惘然——
不是悲伤,而是忽然听懂了自然更迭的密语,
关于收获后的虚空,凋零前的绚烂,
以及生命在沉静中积蓄的、等待破土的力。
至此,墨尽,纸短。
而深秋,才刚刚开始它的叙述。